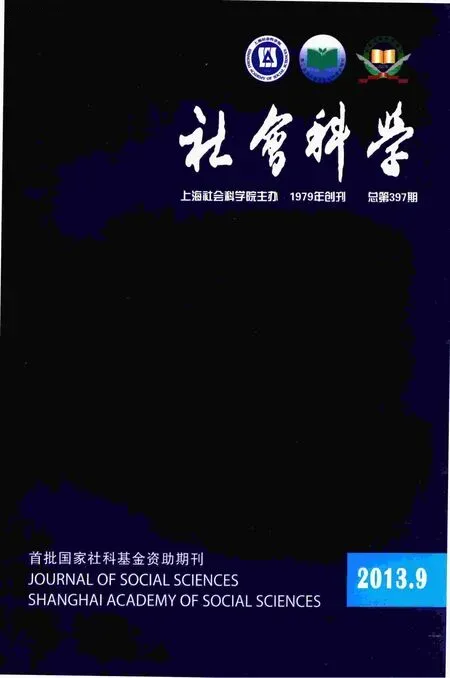元叙述:普遍元意识的几个关键问题
赵毅衡
一、何为“元”?
本文要讨论的题目比较特殊:探讨各种体裁元叙述共同的构成原则。
“元”(meta-)这个前缀,原是希腊文“在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文集最早的编者安德罗尼库斯把哲学卷放在自然科学卷之后,名之为Metaphysics。由于哲学被认为是对自然科学深层规律的思考,因此meta-这个前缀具有了新的含义,指对规律的探研。简单地说,就是说:关于X的X,称为“元X”。例如,语言的控制规律 (语法、词解、语意结构)被称为“元语言”,元语言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
以此类推,“元历史”大致上就是历史哲学,“元逻辑”则是逻辑规律的研究,“元批评”类近于文艺学。港台学者把meta-译为其希腊原意“后设”。但早从康德起我们就知道规律并不出现于现象之后,“后设”这译法不妥。“元”当然是《周易》起开始使用的旧词,《春秋繁露》云:“元者为万物之本”,这译法很能达意。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晚清译为《形而上学》,也极为传神。
此术语虽然源头古老,关于元叙述的理论,却是一个当代问题。20世纪初在科学与哲学界就开始了元理论的讨论。1920年罗素给维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是元语言观念在现代的第一次明确描述,点明层控关系是元语言的根本:“每种语言,对自身的结构不可言说,但是可以有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①Bertrant Russell,“Introduction”,in 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Routledge,1987,p.7.;同年著名法国数学家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提出了“元数学” (metamathematics);1937年逻辑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提出逻辑体系的“元公理”(metatheorum)。由此,元概念成为各学科共同的范畴,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元”成为各学科理论界热衷探寻的范畴。
1979年人工智能专家霍夫斯塔德 (Douglas R Hofstadter)的迷人的“科普”著作《哥德尔、艾歇、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 (Go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获普利策奖,①Douglas R Hofstadter,Go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NewYork:Basic Books,1979.中译本见乐秀成编译《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书用美术和音乐为例,把艰深的逻辑哲学说的极其生动,“元”概念开始普及。此后meta-成为西方大学生喜欢拽的概念:他们会说:“我们来‘元化’一下”(Let's get meta.),大致意思是“让我们深入一层看这个问题”。这可能是西方大量的电影、游戏中的元叙述,激发了青少年的想象。这种普遍元化,也是元叙述脱离了单纯技巧层次,成为一种现代“元意识”的标志。
自从六七十年代元戏剧与元小说的理论开始出现,至今也积累了大量研究文献,但是在学界实践中,对体裁有所偏颇:固然二十世纪后现代元小说的实践,产生了大量典范作品,但是元小说的讨论远远超过其他体裁,以至于至今没有看到综合所有元叙述体裁的讨论。更令人困惑的是:术语“元叙述”已经被用得意义歧出,几乎难以收拾。1979年利奥塔的《后现代条件》一书,②Jean-Francois Lyotard,Introduction: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1979,xxiv-xxv.把“元叙述”(meta-narrative)作为“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同义词,指的是那些类似黑格尔体系的“超越性普世真理”,或“主导意识”(Master Idea),而这种宏大叙述,是后现代主义一心要加以批判质疑的对象。用在这个意义上的“元叙述”,勉强可以说是“关于叙述的叙述”——控制所有其他叙述的叙述,不过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喻用法,利奥塔所用的“元叙述”,意义类近意识形态。
另一些叙述学家则将“元叙述”概念用在小说分析中,例如热奈特用“元叙述”(metadiegetic)指小说叙述分层中的主叙述层。③Genette,Gérard,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 in Metho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王丽亚指出,叙述学家往往只是把元叙述看作元小说手法的一种,也就是说一种小说技巧。④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热奈特还使用了另一个词“元文本”,指的是一个文本产生之后,是此文本生成后被接受之前,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等等,即能对接收产生影响的关于此文本的评论,⑤Gerard Genette,Paratext: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Cambridge: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27.这些当然也是“关于文本的文本”。
上面的两种“元叙述”一词的用法,利奥塔的“意识形态用法”,只能当做一个比喻;而热奈特用于叙述文本形式分析,有其合理性,可能过于细微。本文希望从文本的构造原理上讨论元叙述,找出横跨各种媒介的所有的符号叙述文本“元叙述化”的规律。元叙述化,就是各种叙述文本在层次上扩展的方式。本文首先检查几种主要叙述体裁“元叙述化”的现象,包括各种事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最后从各种体裁的纷纭众相中总结元叙述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利于我们理解这个当代文化的重要概念。
二、什么是当代文化中的“元叙述”?
可以检查各种叙述体裁中的元叙述,包括纪实型叙述的元历史、元新闻、元广告,虚构性叙述的元戏剧、元电影、元小说、元游戏,我们可以看到元叙述几乎无所不在,任何叙述体裁都有元叙述化的变体。尤其是当代的叙述体裁,几乎都可以说成有元叙述成分,其表现多样繁杂,不易总结,是元叙述研究的一个大难点。至今没有人来总结出各种叙述体裁共同的“元叙述化”途径,因此,本文以下的讨论,只能是一种尝试:
首先,元叙述的因素的确在叙述中普遍存在,但只有当元叙述因素成为文本主导,整个文本才能被视为“元叙述文本”。成为主导有几条清晰途径可循。而所有这些“元化”途径,共同特点是“犯框”,即破坏叙述再现的区隔。最后,本文要指出:元叙述除了让文本“陌生化”而显得生动新鲜,利于传达,更重要的是提示并解析叙述的构造,是文本突破有机整体的茧壳。
应当说,没有归成一类的“元叙述”,只有各种体裁的“元叙述化”方式,用以获得有某种相类似“元叙述”的品质。如果我们能总结出各种元叙述的共同点,那么我们就能找到抽象地思考这个问题的可能。
必须指出,程式化是抵消元叙述化效果的最有力手段,如平话小说中常出现“看官有所不知”,实为一个元叙述技巧,但程式化了。而元叙述技巧一旦程式化,就让读者觉得十分自然,“不像”元叙述。因此,没有绝对的元叙述化,也没有绝对的程式化,二者力量消长,引出“元叙述化程度”问题,元叙述化效果达到一定程度后,无法被读者依照文化程式加以“自然化”,就成为元叙述。所以下面说的各种“元叙述化”途径,都只是取得元叙述化效果的相对途径。元叙述因素是无处不在的,元叙述因素被前推,成为文本的主导,才能成就一个元叙述文本。
有些小说“元叙述化”走到一半。王安忆《锦绣谷之恋》中的叙述者,急不可耐地想取得自我意识。叙述者自我取消了客观性,似乎比主人公——一个寻找婚外恋的女人——对情节发展更感兴趣,但是这作品的“元叙述露迹”只是偶一为之,适可而止,因而是一种“中小说”(mid-fiction)。这是艾伦·淮尔德 (Alan Wilde)的用词,据称是“现实主义小说与自反小说的中间地带,其实验性相当强。但主要不靠自反方法”①Alan Wilde,Middle Ground:Studi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8,p.4.。他的这个看法很精彩,指出了元小说没有绝对界限,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元叙述这样的抽象理论问题,有强烈的“文化特殊性”:不仅“元叙述化”的途径因文化而异,而且现代与传统的元叙述大不相同,在一个文化中能体会到的元叙述,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则是再正常不过。下面总结的五条元叙述化方式,呈现一个从内到外的过程:前两条是在文本之内展开,第三条已经跨出文本单层次的范围,而第四、第五两条,则是在文本间进行元叙述化的途径。
第一,“露迹”式:暴露构筑叙述文本的过程,是最明白无误的“关于叙述 (过程)的叙述”。媒介化使叙述得到一个创造独立世界的机会。但是一旦暴露这个制作过程,叙述独立世界的神话就破灭了。元戏剧角色暴露自己是演员,元小说暴露文字是编造,元广告暴露布景是纸糊的,元电影暴露情节是剪辑的,或是摆拍的:任何体裁都有无数暴露自身制作过程的方式。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元叙述化方式,也是所谓“自我意识”的最清晰的表现方式。例如大卫·芬奇的《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把剪辑过程放在制成的电影里;中国学者支宇评论邓贤写的缅甸远征军的报告文学《大国之魂》时,也用“元叙述”一词指作者在文本中的大量的直接评论,诉说自己作为远征军后代长期忍受的政治恐惧,以及他采访这段历史的过程。②支宇:《历史还原、元叙述、文体混杂:邓贤长篇纪实文学研究》,《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正常小说中,叙述者有权做各种干预评论。元小说中,叙述者则有意耍弄自己控制一切的权利。维尔托夫以“电影眼睛论”拍出《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年)等,已经采用“倒卷”(rewinding)制作,例如让肉回到牛的身上,用以让人们看到电影是一种欺骗眼睛的艺术;福尔斯 (John Fowles)《法国中尉的女人》(French Leutenant's Woman),“作者”竟然出来,把表拨慢了一刻钟,情节就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此种“自我暴露”揭示出来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创作过程,有时候被暴露的过程是个更加无稽的虚构,例如巴斯 (John Barth)《顿妮亚扎德传》(Dunyazadiad),写的是《天方夜谭》是如何写成的,山鲁佐德用讲故事迷惑残暴苏丹,原来她有个妹妹顿妮亚扎德,每天从一个叫巴斯的小老头那里取得一个故事告诉姐姐,巴斯当然是从他的现代书房得到这些《天方夜谭》故事。
以拍电影为情节主体的电影。例如戈达尔 (Jean-Luc Godard)的《芳名卡门》 (Prenom Carmen),戈达尔自己作为一个导演出现在电影中,指导剧中人物如何拍摄一个“卡门故事”电影;费里尼的《81/2》中说到导演黔驴技穷,求助于梦境;《阮玲玉》《我与梦露相处的一个星期》这样的电影也应当算元电影;至于《录影带谋杀案》《纸袋头》等,直接就把自身这部电影如何形成的过程作为电影的主要情节,可以称为“自生电影”。
另一种以“叙述中的叙述”为主导方式的叙述,是靠生成别的叙述而形成的叙述。一般的“故事中的故事”并非一定是元叙述,因为叙述分层经常是程式化的叙述手段,例如《十日谈》就不算元叙述,因为没有写出让我们出乎意料的“生成叙述”。但是如果以某种方式有效地突出了叙述中的叙述,元叙述就出现了。小说如塞尔维亚作家帕维茨的《哈扎尔词典》,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电影如希区柯克的《后窗》,主人公拉开窗帘,就等于在电影中看电影。
例如戏中戏放在戏剧和电影中,就很可能效果不显,而小说中的次叙述 (人物说起故事来),大部分都已经很正常。放到广告中,就可能是“元叙述化”的手法。

这是Clear Channel(一家户外广告公司)的广告。一家广告公司做自己的广告,已经是元广告。但是它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自指”方式,屏幕上斗大字说“嗨你!让你看你就看了吧!”,看到这广告的人不禁吓了一跳:“的确我着了招”。然后潜在的客户就会想到:它让每个人不由自主看它要人们看的东西,说明这家公司的广告“到达率”极高。这是一幅“自我生成”广告,是一幅不失幽默,不乏惊奇,而且构思新颖的元广告。
这种叙述中的叙述,还有一种亚型,即多体裁“拼贴”:正常小说中,文体不免有混杂之处,例如中国小说中的“以诗为证”,《红楼梦》中画出了贾宝玉身佩之玉的正面反面图案字样。这种拼贴可以来的更自然,例如鲁迅《高老夫子》中高老夫子接到贤良女校的聘书,作为叙述内容,原可把聘书语句转述出来,但是小说中把聘书格式原样印下,而且民初格式,不用任何标点。美国作家厄普代克 (John Updike)的小说《跑吧,兔子》,其中有一行是这样的:
He drives too fast down Joseph Street,and turn left ig-noring the sign saying STOP.
他快速度驶过约瑟夫街,不顾写着“停车”的牌子就打左转。
就叙述文本的非图像性而言,交通信号的STOP也不应大写,这是印刷文字的图像性能被调动进入叙述。但是偶一用之,读者不会感到是元叙述。只有当叙述者有意把拼贴做过头,元叙述才会出现:例如巴塞尔姆 (Donald Barthelme)《白雪公主》(Snow White)中画了国旗、太极图、卡车、手枪,甚至有读者调查问卷,有点像电影中拼贴动漫镜头。
第二,多叙述合一:同一个文本中有多个叙述展开,可以让读者自行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元叙述性,是因为读者的选择僭越文本构筑过程。爱尔兰作家奥布莱恩 (Flann O'Brien)的《双鸟戏水》(At Swim-Two-Birds)一直是元小说论者喜欢讨论的名著,奥布莱恩解释说“一本好书可以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开端,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仅仅在于都源于作者的预知能力。正因为如此,故事可以有上百种不同的结尾”。另一本“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库佛(Robert Coover)的《保姆》(Babysitter),小说中有14个并列的不同情节 (保姆杀了孩子,保姆自杀,等等)。这些情节在逻辑上不能共存,但是它们偏偏就共存于一本小说。任何一个情节线索单独拉出,是正常的叙述,并存而互相对照,而且强迫读者面临选择,才构成元叙述。
这样的叙述文本,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文本中,几个文本有某种关联地共存,也就是说,是以文本间性为主题的文本。这已经成为当代电影最喜欢用的元叙述方式:从《罗拉快跑》 (Run Lola Run),到《滑门》(Sliding Door),到《源代码》(Source Code),都是这样一个叙述的多重变体共存文本。在纪实性叙述中,这种方式只能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出现,例如说“关于李自成的下落,有几种说法”,而且因为读者与作者一样,没有挑选的可能,实际上不是元叙述。
第三,多层联动式:叙述暴露层次间的控制。戏剧元意识不仅是明确演与被演的关系,即层次控制关系,也不仅是布莱希特所强调的“被演出意识”或“引证意识”,即剧场性,而且是层次替换意识,即二者相互影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正常小说中,叙述者可以打乱情节的顺序,用倒述、预述、伏笔等,目的是把故事说得生动,而元小说“力求一种总体的随意性,以表现当代社会的杂乱无章、疯狂恣肆、冲突横生”①Patricia Waugh,Metafiction:The Theory and Pra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London:Routledge,1984,p.12.。极端的例子如胡里奥.柯达扎 (Julio Cortazar)的《跳房子》(Hopscotch)。
游戏这种特殊的叙述,②关于游戏作为一种叙述,参见赵毅衡《演示性叙述:一个符号学分析》,《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经常可以元叙述化。很多游戏是在别的游戏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依赖于另一层游戏而进行的,是“关于游戏的游戏”。最常见的就是“赌其他游戏的结果”。这种游戏方式与历史一样古老:赌赛马、赌赛狗、读赛蟋蟀、赌赛球等。注意这与观看比赛不同,一般观赛者自己并没有进行另一层游戏,而赌另一层赛事者,自己在进行另一场游戏,只是他们在另一个层次上游戏,两场游戏联动,由此构成“经典的元游戏”③Roger Fisher et al,Getting to Yes: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5.。
元广告也可以做的更加微妙。例如下面这张LV公司的广告,法国名演员卡特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在给LV公司拍广告:道具火车,灯光架子,历历在目,场面很大。看来广告原是拍德纳芙拎LV包箱上火车回家的情景。似乎是LV公司很认真,德纳芙很投入,过程繁复而细致,只能中途休息。此时德纳芙坐在LV箱子上揉脚,松一口气,广告语说“有时候,家只是一种感觉”。这是一幅非常有创意的广告:广告拍做广告,以做广告作为广告,暴露做广告的过程,自嘲工作的辛苦,让法国的第一美女受累了,幸好可以坐在LV箱包上,略有安慰。的确是自曝控制层次的“元叙述式广告”,很有想象力和幽默感。

第四,“寄生”式:依靠已知叙述才成立的文本,即明显地关于另一个或另一批的叙述的叙述,这也是一种“叙述文本共存”。但是这种“后文本”④关于“先后文本”,请参见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是正常的程序化的各种“后传”、“续篇”、“再写”、“归来”,甚至“前传”,这些叙述形式都已经自然化了。
正常小说中,有大量典故,对先前文本的影射,这是无所不在的“文本间性”。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据他自己说“暗指和戏拟了60多位作家”,但是读者多半难以觉察。而元小说中有意戏仿各种体裁。例如布罗提根 (Richard Brautigan)的《在美国钓鳟鱼》(Trout-Fishing in America)戏仿禅宗公案,霍克斯 (John Hawkes)的《菩提枝》 (Lime Twig)戏仿通俗惊险小说,加德纳 (John Gardner)《格伦代尔》(Grendel)颠覆英国史诗《贝尔武甫》(Beowulf)。
大部分电影中这种“尊敬的点头致意”几乎看不出来。例如特鲁福的《日以继夜》中引用了自己的电影《四百击》,其中的一个镜头是人物撕下美国片《公民凯恩》的海报。伍迪·艾伦的《星尘往事》戏仿费里尼的《81/2》,他的《开罗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1985)向巴斯特·基顿 (Buster Keaton)的名作《小福尔摩斯》(Sherlock Jr.,1924)致意。只有明显直接“寄生于”其他作品,才让观众明白不得不如此读才行。如里斯的《藻海无边》那样的小说,如黄哲伦 (David Henry Hwang)的《蝴蝶君》(M.Butterfly)那样的舞台剧或电影,对不了解《简爱》或《蝴蝶夫人》的读者,这些作品的立意无法成立,因为《藻海无边》就是要显示纯洁爱情的《简爱》,有个对照之下令人战栗而读之的前文,而《蝴蝶君》则以东西方文化关系,进入同性恋之复杂冲突为主题。
第五,全媒体承接式:一个叙述文本被许多媒体承接衍生成多种体裁。尽管这种情况在传统文化中不乏先例,小说的故事被改编成戏剧、评书等,一直是常见的事,但这种“全媒体承接”却是当代传媒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元叙述发展的新趋势。当今时代传媒文化的发达,一个媒介中的叙述可以衍生到整个文化:是连环画人物的唐老鸭、超人、变形金刚、黑衣人、蝙蝠侠,原是武侠小说英雄如郭靖,东方不败,几乎都衍生成为“全媒体叙述”:电视连续剧、电影、动漫、游戏、电子游戏、玩偶商品、次生小说,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以至于到最后超人与蝙蝠侠等人物,替代真人,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偶像。1999年,蝙蝠侠“诞生”60周年,不少文化论者为他“庆生”,不少论者对当代大众文化这种永恒的童心,感到迷惑不解。①David Finkelstein and Ross Macfarlane,“Batman's Big birthday”.The Guardian,March 15,1999.http://www.guardian.co.uk/g2/story/0,,314504,00.html.Retrieved June 19,2007.当代传媒的无穷变身所创造的元叙述变身能力,为先前时代所不可思议。
更剧烈的“元广告”是对广告内容做反讽性的评论,或者是相反,用商品来反指与广告图像正相反的意义。这在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中,几乎成了套式,例如王广义的成名作,借广告对比文化革命的大批判之无的放矢,或借大批判来反说今日商业化浪潮,尤其是西方进口货受欢迎之空泛。这是体裁之间的互相衍生互相评论。
三、“犯框”:元叙述对抗区隔
所有以上五种“元叙述化途径”,共同特点是侵犯破坏叙述的框架区隔。区隔在符形、符义、符用三个层次上把纪实叙述经验区隔开来,再把虚构叙述与透明的纪实再现区隔开来,让它成为一个可以不透明的独立的世界。
一度区隔把符号再现与经验区隔开来,这个区隔的特征是媒介化:经验的再现,则必须用一种媒介才能实现,符号必须通过媒介才能被感知。一旦用某种媒介再现,被再现的经验之物已经不在场,媒介形成的符号代替它在场。我们可以称这个一度区隔为“媒介化区隔”,其结果是一个符号文本构成的世界,这种基础叙述文本是“纪实的”。
虚构叙述必须在符号再现的基础上再设置第二层区隔,也就是说,它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为了传达虚构文本,作者的人格中分裂出一个虚构的叙述者人格,而且提醒接收者,他期盼接收者分裂出一个人格接受虚构叙述。这个双层区隔里的再现,与经验世界就出现了“不透明性”,接收者不再期待虚构文本具有指称性。
霍尔对“再现”的区隔作用解释得非常简明清晰:“你把手中的杯子放下走到室外,你仍然能想着这只杯子,尽管它物理上不存在于那里。”①[英]斯特亚特·霍尔:《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页。这就是脑中的再现:意义生产过程,就是用媒介 (在这个例子中是心像)来表达一个不在场的对象或意义。我们可以延伸霍尔给再现举的简单例子:我看到某人摔了一个杯子,这是经验。我转过头去,心里想起这个情景,是心像再现;我画下来,写下来,是用再现构成纪实叙述文本。当我把这情景画进连环画,把这段情景写进诗歌小说,把这段录像剪辑成电影,就可以是虚构叙述的一部分,它可以不再纪实。米切尔在《图像转向》一书中认为元概念 (concept of meta)的基础是“二度再现”,他引用福柯,说这是“再现再现的力量”(to represent its representation)。②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42,p.58.
有一种“元电影”比较特殊,是其他叙述样式所无:从银幕上直接对观众说话。在戏剧里,人物直接向观众说话,是很自然的,就不能算“元戏剧”;广告因为其单向诉求性质,也经常会对观众直接说话,也不能算“元广告”。但是电影的表演性质是被程式化遮掩的,不存在第四堵透明的墙,无法对观众说话。一旦用上,就比较特殊。伍迪.艾伦 (Woody Allan)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他自己出镜扮演的主人公直接对观众说话,问观众对戏中人物的看法,更是翻出一个层次;谢尔 (Charles Shyer)导演的电影《公子阿尔菲》(Alfie)主人公一直向着观众说话。看着某女郎来了,对观众说“对不起,我先要去办点事”,转身进入情节。
不少论者已经谈过框架在叙述文本中的重大作用。苏克尼茨克在1985年的著作中指出元小说的反身指涉目的在于“把读者愿意相信和不愿意相信的同时予以搁置”,因为框架是相信的前提,但是框架在元小说中并没有被全部破坏。③Ronald Sukenick,Form:Digressions on the Act of Ficti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5,p.99.次年,马丁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元小说与框架的关系:“这个框架告诉我们,在解释它里面的一切时,要用不同于外在于它的东西的方式。但是为了建立这一区别,这个框架就必须既是画面的组成部分,又不是它的组成部分。为了陈述画面与墙壁,或显示与虚构之间的规则,人们就必须违反这条规则,正如罗素不得不违反它的规则,以避免在陈述规则是陷入悖论。”④Wa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中译文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最具体直观的框架,莫过于美术的画框与标题,画框把美术世界与周围的墙壁隔开,也就是将再现与经验世界隔开。如果一幅画自己画出画框,那就是自我“元化”。荷兰版画家艾歇(M.C.Escher)的下面这幅画,几乎囊括了本文上面讨论的各种元叙述化途径:它暴露了自身在区隔框架内的构筑方式;它提供了左手画右手与右手画左手两种选择;它提供了立体与平面两个层次;他提示了我们画的“立体感”实际上依赖画框的区隔作用,而这区隔功能是可能被破坏的;它提示了此画的“现实效果”完全依靠媒介——简单的铅笔线条。

因此,“正常的”叙述,满足于在这框架内处理文本。而任何元叙述,其本质是“犯框”,侵犯这个框架,虽然元叙述不一定如这幅画那样完全推翻框架,但是它试探“逗弄”或“暴露”框架的区隔性,有意卖弄这种冒犯,让读者意识到叙述虽然落在区隔框架中,却并不一定要尊重这个区隔框架:“犯框”是所有元叙述的根本特征。
四、“元叙述”与叙述理论
马丁说:一旦叙述冒犯框架,“这位作者就立即成了一位理论家”①Wa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中译文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的确,元叙述的主要意义,就是“用叙述讨论理论”,尽管不是用理论语言讨论理论。元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演出,是叙述者或人物替代批评家理论家,从故事内部批评叙述规则。怀特《Metahistory》一书中译本标题译作《元史学》,没有忠实于原义,却很传神,一旦“元叙述化”,其中的“学”这一层意思就突显了。元游戏指的是对游戏的研究,对游戏规律的探讨。这是教练的工作,运动学的工作领域,也是对运动员的高水平要求,即不仅面对游戏,还要知其所以然。②Barney Pell,Strategy Gener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Meta-Game Playing,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93,p.289.教练的临场指挥换人,直接影响到比赛胜负的可能性。至于元戏剧,霍恩比认为可以有三种取向:
第一,为探究存在问题,“戏中有戏”;
第二,为探究社会问题,“戏中仪式”;
第三,为探究个人问题,“演中有演”。③Richard Hornby,Drama,Metadrama and Perception,London:Associ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83.
这个说法倒是相当条理分明,讨论的却不是戏剧结构,而是戏剧背后的哲理。任何戏剧都有理论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戏不元。元叙述暴露叙述策略,从而解构现实主义的“真实”,消解利用叙述的逼真性以制造意识形态神话的可能,颠覆叙述创造“真实世界”的能力。
把某物“打上引号”,就是使某物成为语言 (或其他艺术表意手段)的操作对象,而不是被语言“反映”的独立于手段之外的客体。当我们说: “小说表现‘生活’”。这完全不同于说:“小说表现生活”。后一个宣称是“自然化”的,生活被当作一个存在于小说之外的实体,保留着它的所有本体实在性;而前一个宣言,生活处于引号之内,它的本体性被否决了,它只存在于“小说表现”的操作之中,在这操作之外它不再具有其独立品质。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充分的现场性。这二个宣称还有更深一层分歧:在“小说表现生活”中,生活与小说处于同一符号表意层次,操作是同层次的水平运动,它的运动轨迹显彰与否是个次要问题;“小说表现‘生活’”,主宾语项是异层次的,而“小说”比“生活”处于高一层次,它居高临下地处理引号内的事项,表现的操作就成了突然层次障碍的关键性行为。
换句话说,在“小说表现‘生活’”这陈述中,与小说这主词有关的,与其说是“生活”的诸本质内容,不如说是小说表达本身,它的构造之自我定义功能:小说成了关于自身的表意行为,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说,成了元小说。
元小说揭示小说虚构性,从而导向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元小说表明符号虚构叙述中,意义很大程度上它是叙述的产物。这样,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也并不比虚构更真实,它也是符号的构筑:世界不过是一个大文本。符号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读者的任务不再是接受一个已完成的充分自我封闭的世界,相反,他必须参与创造,自行发现作品与世界——从而学会创造自己的世界。”
诚然,离心运动是20世纪全世界文学总的趋向,但是如果离心的方向依然是追求对世界的解释方式,那么这是同水平的运动。欲超越当代文学传统,需要对更根本的东西——表现形式与解释方式——进行破坏和再建。先锋小说元意识的产生符合了这个需要。
元意识,是对叙述创造一个小说世界来反映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的根本怀疑,是放弃叙述世界的真理价值;相反,它肯定叙述文本的人造性和假设性,从而把控制叙述的诸种深层规律——叙述程式、前文本、互文性价值体系与释读体系——拉到表层来,暴露之,利用之,把傀儡戏的全套牵线班子都推到前台,对叙述机制来个彻底的露迹。
这样的小说不再再现经验,叙述创造的是文本间关系。读者面对的不再是对已形成的经验的释读,读者必须自己形成释读。当一切元语言——历史的、伦理的、理性的、意识形态的——都被证伪后,解释无法再依靠现成的符码,歧解就不再受文本排斥,甚至不必再受文本鼓励,歧解成为文本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每个读者必须成为批评家。
从这点上说,元游戏实际上是游戏的本质,也是人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的本质。而这种至关重要的能力,要学习的就是触类旁通,拒绝人云亦云的“元意识”。一个叙述文本能被随便“元叙述化”,是它受欢迎的标志,因为它提供了人们延伸创造的共同基础,成为文本典故的锚定点,《蝙蝠侠》或是《西游记》,就是这类让一个文化中各种媒介的各种文本都可以衍生发展的出发文本,可以称之为具有“元叙述化潜力”的文本。
由此可以推进一步说,不让“元叙述化”的文本往往是在文化中被视为经典,视为神圣的文本。像《荷马史诗》那样在文化中被反复引用、背诵、讲述,其叙述方式就固定化了。①Michael Hutter,“The Value of Play”,in(ed)Arjo Klamer,The Value of Culture: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Arts,1996,p.129.越是经典,就越吸引元叙述化,但也越是“改编难”,任何改变都会被认为“不像”,甚至被指责为“亵渎经典”。可以说,神圣性的经典就是不让随便“元叙述化”的文本。这样的经典文本是需要的,因为元叙述化本身具有消解能力,过于广泛地使用会让一个文化的基础性叙述文本消失。
五、元意识与中国思想
一般论者都认为“元意识”是典型的后现代思想。麦卡弗里指出:“元意识正在进化成我们时代的特征意识,是对主体性和我的体系里人工制造物高度自觉后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当代的意识不仅浸透了自我意识,而且是认识到注入游戏,玩耍,虚构,人造,主体性等是让人文明化的核心概念。”②Larry McCaffery,The Metafictional Muse,The Works of Robert Coover,Donald Barthelme,and William H Gass,Pittsburg: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1982,p.225.但是元意识只有在后现代才能产生吗?哪怕过去时代有过痕迹,但是只有在后现代才能成为主导思想吗?
笔者认为,在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文化中,侵犯框架区隔的意识不会很强烈,因为规则只有在合一的框架区隔中才能顺利贯彻。相反,某些超乎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哪怕在前现代都有可能催生元意识。
不奇怪,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元意识由来已久,尤其是在释道这两家非主流思想中,《道德经》强调区分君临于“可道”、“可名”世界之上的“常道”与“常名”;禅宗谕“至佛非佛”和论“迷”,与“悟”。《传灯录》卷二十八说:“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清晰地指出层次控制关系。
奇书《西游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元小说。翻转《西游记》,固然已是戏仿,而书中论及层次观念,妙趣横生,发人深思。第四回孙行者入小月王万镜楼,镜中见故人刘伯钦,慌忙长揖,问:“为何同在这里?”伯钦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这是框架意识的绝妙说明。
控制与被控制,操纵与被操纵,扮演与被扮演,是叙述的最基本原理。本书在先前已经屡有讨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时,首先就是其“三界”,“欲界六重天”等分层观念使中国士人“讶其说以为至怪也”。《酉阳杂俎》重说了《譬喻经》中故事:“昔梵志作术,吐有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吞之,柱杖而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这观念来自《观佛三昧海经》,其中说佛现白毫毛相,“毛内有万亿光,于其光中,现化菩萨,皆修善行”。
其实佛教各宗都把宇宙分层作为色空观的最主要立论方式之一,法华宗所谓“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华严宗大师法藏应武则天召为说佛法,举殿前金狮子塑像为例:“狮子眼、耳、支节,一一毛处,各有金狮子。一一毛处狮子,同时屯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无边狮子,又复一一毛,带此无边狮子,还入一毛中。如此重重无尽,犹天帝网珠,名因陀罗网境界门。”①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这种分层观念在《华严经》中论之甚详:“善男子,我经行时,一念中一切世界皆悉现前,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层次观与定慧观很自然地联结起来。不少佛学史家都同意华严宗是禅宗思想的前驱。就万相分层,诸法实相非无亦无这点而言,的确启导了禅宗在修行之上更翻一层。
层次观念对禅思维方式影响至深,这类公案在禅宗文献中极多。举一个与中国民间神相关的例子:《五灯会元》卷二“破灶堕和尚”,大师用杖击破灶,灶神得以解脱而升天,因此“青衣峨冠”来表示感谢。“少选,侍僧问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诲,灶神得什么径旨便得升天?’师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别也无道理为伊。’”必须“打破”现象世界,才能进入更高层次。受佛理影响的中国诗学,讲“写意”。而写意的前提就是文本之上另有一“意”界,王国维后来归为“境界”说。境界超越艺术媒介之外,也超越观赏文本直接见到的物象之外。
可以不无骄傲地说,中国先贤对元意识比西方古人敏感得多。然而西方现代元意识发源于希腊哲学与数学的推理逻辑之中。如欧几里德几何体系之严密,固然难逃导致千年机械论统治之咎,但一旦发现触动公理,即可创立整个新体系,它就直接引向了元数学。中国当代的元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无法借释道而生,但是中国传统思想之非理性色彩反而有助于元意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