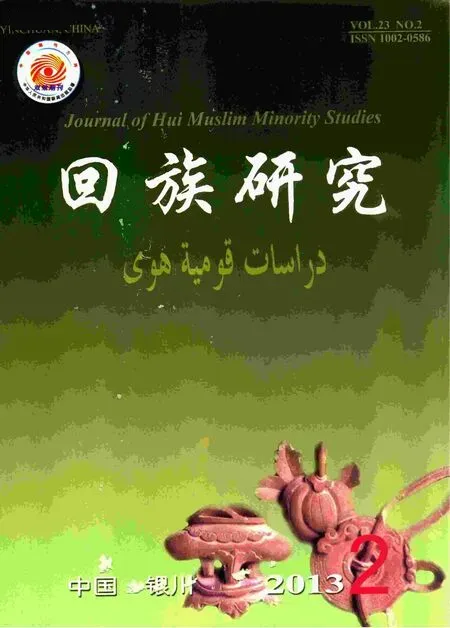传统乡村回族的家族与时代变迁——以红岸村杨氏族人为例
杨文笔
(宁夏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宁夏 固原756000)
费孝通曾以“乡土中国”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自身特质,为学界打开了一扇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特性的窗口。传统中国以宗法伦理构筑具有家国同构特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宗法制成为维系传统乡土社会的纽带。在基层乡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由父系继嗣关系组成的家庭联合,使得乡土社会构建起来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对的基层社会组织——宗族(学界一般认为家族一般是以五服为界,宗族则指同宗同姓同地域的各个家族结成的群体)。这种扩大家族的基层组织构造,在充当中央政权实现民间社会控制中介的同时,不断地实现与高度集权的中央王朝的权力博弈,尤其是在地方社会控制权下移,“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局面呈现中,宗族或“乡族”成为民间社会具有相对自治的符号表征。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此提出了中国汉人社会中的“宗族范式”,并在远离中央统治中心的“边陲地区”(东南地区)最为明显[1]。这种“政治与地方组织”及基层各种关系网络共同组成了乡土社会的“权力文化结”。当然“宗族”并不绝对是以血缘关系而形成,这一点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是有所不同的,学者郑振满和陈忠烈在福建和广州的研究中发现,宗族的构建具有较强的工具性,是超血缘和超地域的人为民间结社的需要。例如郑振满在福建地区发现的“继承式”“依附式”“合同式”三种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中,其中“合同式”就是非血缘关系的异姓人契约结社的宗族类型[2]。我们可以把东南地区视为中国宗族的“文化高峰”,那么对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处于中国宗族的“文化边际”的西北回族地区,这样一个迥异于中国汉人社会的文化空间,“宗族范式”是否普遍存在?其实在西北回族地区,“宗族范式”的显性特征根本就不存在,更多的是体现出宗族的次级形态——家族,在与作为宗教群体“族性”边界的张力中,家族的构建在乡村回族主体的文化拒斥中,及与他群差异的突出中,缺少东南地区宗族的显性特征。中国回族的家族及其家族认同在其族群“板块分布”格局中,具有地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东南、华北等地回族的家族认同呈现方式较为“显性”,西北回族这种显性的家族制度要素则较少。在西北乡村回族社会中,其家族认同的显性表达方式明显缺乏,更多体现在其“隐性”的表达方式上。笔者选择了西海固地区红岸村杨氏族人为研究个案,以此展开对这一话题的分析与思考。
一、村庄早期的家族
红岸村,位于宁夏海原县高崖乡东北部的一个纯回族村庄,处于平原地势,清水河自南向北流经村庄,村庄北邻同心县王团镇,村东有银平公路和中宝铁路干线通过,交通较为便利,是一个发展潜力较好的回族村庄。在杨氏回族人迁入村庄之前,红岸村的历史甚为模糊,据《海原县志》(1999年版)记载,隋朝时期,在今天的高崖乡一带设置了塔楼县。北宋时期,与西夏政权对峙,在红岸村的邻村红古村筑墙建立萧关城[3]。元朝时期,蒙古人灭掉西夏,据西夏故土,红岸村一带也留下了蒙古人的足迹。清光绪年间设堡为管辖单位,红岸村归属于海原县56 堡之一的红古堡。杨氏族人进入村庄,时间不过130 多年,据2009年新修纂的《杨家塘杨氏族谱》中表明,红岸村杨氏族人是清朝同治年间为躲避战乱和迫害从河南和陕西一带迁移而来①,先居固原羊圈堡,再迁同心县的老庄子洼,后其中的杨天虎家不久就搬到了红岸村,成为红岸村杨氏族人的第一代。这一口述历史时间,与海原县正史记载相符,修纂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乾隆盐茶厅志》中看不出红岸村有回族人的影子,但修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光绪海城县志》中,红岸村所属的红古堡就已被注明有回族人居住。若干年后,又有5 家百字辈杨氏族人迁移过来,从《族谱》看出,他们在辈份上低杨天虎一辈,是红岸村杨氏族人的第二代。当时的红岸村,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土地贫瘠,甚为荒凉。仅有的六家人在“我们原为一个先人的根”族源记忆下,维系成红岸村的杨氏家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婚丧嫁娶中始终是以整村的杨氏族人为单位,那时一家有事,全村(族)行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西海固乡村回族穆斯林的家族是一种以父系同姓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群体,受汉族社会家族中“五服”为认同标准的影响,回族家族内血缘认同为曾祖辈为标界,即从曾孙到曾祖五辈以内的所有同姓男系家庭构成一个家族。在当时的杨氏家族中,不可否认的是,村庄中的杨氏族人内部存在着家与家间的亲疏远近,这种家庭间关系的差序化取决于同—族亲的亲疏关系。王铭铭在研究福建村庄中的家族时,将同—族亲细分为堂亲、同房份亲、同房支亲、同家族亲等类型。其中堂亲是四五代之内同族公的族—家亲,族亲是四五代以上的同祖先的家族成员。同—族亲的亲疏关系分如下级类:堂亲—同房份亲—同房支亲—同家族亲。堂亲是其中最小单位,同家族亲是其中的最大单位[4]。西北回族的族亲与汉族社会有着相同的一面,只是在堂亲的认定上其代际更小。由于时间久远,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我们无法考究他们间谁为直系血亲,谁为旁系血亲,谁家与谁家是堂亲,抑或是族亲?其实这并不重要,作为同治年间逃难陕回的幸存者,空间的置换无疑使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党护族类”的观念,聚族而居,互为族亲,这在早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杨氏族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现在杨氏后人的口述来看,当时六家人的团结比较好,尤其是在他们经营的驮运业上,六家人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共同经营驮运事业。他们结合成一个家族整体,共推家族中辈份最高的杨天虎为掌舵人,在村落中,他也是杨氏族人的“掌柜的”(族长),是全村人的“庄主”。赶脚的脚户在家族中选取,如第三代中的杨华,曾经是家族中驼运业的脚户,后因能干成为掌舵人。他武艺高强,能说会道,在保持家族利益,协调与外人矛盾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在后人中还相传着他的故事。随着杨氏家族人口增多,分家中新的家族又开始形成。到了民国初年红岸村的第五代保字辈时,红岸村的多家族现状形成,这时整个红岸村的杨氏家族已以红岸村的第二代百字辈为认同标准,形成了6 个家族,杨氏族人的亲族认同转移到了这6 个新的家族。事实上,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建构实体,红岸村杨氏家族本身也会经历一个“树大分枝”的发展过程,从一姓一族到一姓多族的同根异支。民国年间,正值国家形态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时期,这种时代变革体现在基层乡土社会,则是一个国家权力向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断渗透的过程。诚如王铭铭所说,国家力量在基层社会中的延伸起始于民国时期。当时,新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巩固其自身统治,加强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控制,在中国农村积极推行保甲制度,以户为基本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这种基层政权建设的结果,一方面国家权力渗透到了民间社会,另一方面也为乡土精英的崛起提供契机。这种背景中,杨氏族人第五代中的杨保荣脱颖而出,他当过保长和甲长,后任高崖区区长,在当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谓一手遮天。他在红岸村中辈份并非最高,年纪并非最长,但凭着他的“权”与“威”,却是名副其实的“庄主”,是杨氏族人的“族长”,是清真寺的学董,在这一时期,树大分枝的杨氏族人被空前整合成一个同姓家族整体。民国年间随着伊赫瓦尼在海原县的传播,杨保荣凭借着自身的权威,在杨氏族人的教派归属上,实现了形式上的改宗换新,他发动全村人新建造了村落历史以来的第一个清真大寺,使杨氏族人在村落公共事务中保持高度一致。即使如此,这一时期也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依附式宗族”特性的强宗大族,杨氏族人内部“三代”以内的家族认同更为强化,因为这一时期杨氏族人大多数都达致“五代”,超“三代”的认同明显弱化,家族单位“一本万殊”,即使是保字辈的14 家,家族认同单位已经多元化。他们对自己近缘的族人,称为“党家子”或“一门分”“一门子人”等,在杨氏族人中,这些名词表达家族及其认同的内部方式或特有符号,当人们说我们是“党家子”时,意味着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人。整个杨氏族人只为同祖同宗、同源异流的不同家族。
二、家族再生产与家族认同的“差序特性”
家族是一个具有流动特性的动态变化的实体,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推移,其直接结果便是家族再生产的分家析产,分家析产的结果使多个“兄弟互动性”的核心家庭形成。新的经济独立的家庭形成,它是家庭这种初级社会群体发展的必然,这种树大分枝的动态性家庭分化,消弱和重构着原有的家族认同,体现在随着家庭的扩大代际的增多,使得原有的家族认同在动态演变中弱化,新的家族认同在“近代”内重新得以建构。回族人的家庭结构与汉族人有很大的差异,传统的汉人家庭以四世同堂的联合和扩大家庭为主导,而回族社会中这种家庭类型却很少,分家而生成的核心家庭是回族社会中的主体。这在红岸村的杨氏族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不仅在过去很普遍,现在更为普遍,在杨氏族人看来,在一个家庭中,成家后的儿子分家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有些家庭基本上的做法是一旦儿子结婚,立刻就会分家,这使得红岸村的家户较多。民国9年(1920年)时,红岸村杨氏族人有大小十几家,到1949年时已发展到50 多家,杨氏族人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当然这与这一时期国家对国内人口控制的松弛有关。笔者2010年调查的红岸村人数为1357 人,却有302 户,其中一户或一家人为4.5 人,这个数字是接近现今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其中杨氏族人的人口规模达到800多人,当年的几个家族已演变成了20 多个新的家族。
在红岸村800 多口杨氏族人中,如果从源头追溯,这些现在看来都已经单门立户的小家庭,都是清末迁移到红岸村杨氏六家人的后代,从规模上说,他们已有150 多家,只不过是这六家人历尽百年后形成的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由于回族社会受到汉族“五服”传统的影响,即从曾孙到曾祖的五辈来界分家族。但是在家族中具体执行“五服”传统时,回族人有自己的特色,回族人家族中真正执行的是“四服”(四代),甚至是“三服”(三代),也就是“三服”之内的核心家庭,实为是“一门子人”或“党家子”,他们的“党家子”观念要比“四服”内强烈得多。乡村回族的家族认同感的强弱与代际数(隔代)成反比,也就是说当代际数越大时,即隔代越远,家族认同感相应越弱,认同的边界只在5 代以内,代数越小(隔代越近),越能体现出他们是直系血缘的“党家子”。现在红岸村的杨姓家族中,他们中以红岸村第5 代保字辈为认同标准,形成了20 多个大大小小的家族。人们基本上是以同爷辈的认同来构成同一家族。如笔者调查的杨保心与杨保旺为同胞亲兄弟,他们为红岸村杨氏族人的第五代,杨保心生有10 个儿子,杨保旺生有6 个儿子,各自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十多个家庭。在他们这一辈上,他们是最亲的兄弟,到了他们的儿子辈的十几家时,他们都是杨氏族人中最亲近的“党家子”。但到了他们的孙子辈时,原本的一个家族的认同发生转移,认同感已经明显弱化,他们并没有出“五服”,但是家族观念已经淡化了。他们的家族归属开始转移到了离自己更近更亲的堂族,这种近辈单位是以三代为依据,越近其认同感越强,越远其认同感越弱。当然这并不否认“四服”和“五服”的家庭就不是同族人,这种族人认同也会在不同的情境中演绎出来,只是带有了明显的“差序”特性。也就是说,当“四服”内的族人家庭在与“五服”内的家庭相对时,他们间更认同为“党家子”,以此类推。当整个村数十代的杨姓人与他姓人相对时,他们都会认同自己是杨家人,这种本是同根生的共族观念又强烈起来,2009年几个县的杨氏族人大聚会则是例证。
三、家族认同的内部表达机制
杨氏族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自清末迁至红岸村,毗邻设舍,聚族而居,形成单姓同族村落,随着以后他姓家庭进入村落,这种杨姓同族的认同,在六家人中表现得甚为明显。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家族认同内部的表达方式上,这种表达方式既有着外援的显性,也有异于“他者”族群的内部自我创设,使得回族人家族认同的构建方式上具有着二元属性。
(一)字辈与辈份:杨氏家族认同的显性表达
具有“双轨制”特性的回族人起名包括了“起经名”与“起学名”。回族人的“经名”相似于汉族人的小名,是穆斯林身份的一种内部表达,“学名”或“官名”却寄予着在汉文化语境中回族人家族认同的本土化。回族人起官名时,也仿照汉人的起名规则,制定了一套字辈规则,通用于整个家族内,其目的与汉人社会一样,“行第原为合族定名分而设,使子子孙孙,承承继继,不至于有干涉之嫌”[5]。字辈的功能是明晰无疑的,使用同一字辈的人为同一辈,通过字辈可以看出你在整个家族中的辈份,以及所处的位置。字辈不同,可以表明长幼尊卑的秩序,他不以年龄为标准。作为个体,遵循家族中的字辈,既是一种群体的归属,也是作为家族秩序的显性表征。字辈规则中,包含着一整套家族权利和义务。作为涂尔干所说的外在于个人的“社会事实”,认同中具有一种隐性的群体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来自于乡土社会礼治秩序下的家族伦理,它所塑造的家族认同在代际传承中已超越仪式互动性,家族意识透过字辈则能清晰可见。红岸村杨姓族人字辈的具体制定,时间久远,我们无法详实考证,但这套规则通过家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红岸村杨姓已有九代人,其中前七代人的字辈是这样的:天、百、无字、汉、保、志、文。笔者通过对村庄七代人的名字的考察,所有人的起名上基本上都遵守着这一规则,如表1。据老年人回忆说,在过去的时候,当村里生了下一代人时,族内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着下一代的起名。正是如此,在“无宗族”的红岸村杨氏家族中,早期杨氏家族人的家族观在家族再生产中分化并转移,形成以“己”辈为认同单位的多个家族,杨氏家族的字辈能够完整地保持七辈,在红岸杨氏族人中,他虽不称与自己不属“四服”的同辈人为党家子,但他不会泯灭掉我们是同一个“祖爷”的“根”的观念。事实上“根”既是家族再生产的源泉,也是渐离渐远的杨氏族人在形成新的家族认同时,仍不失为“杨氏族人”的原因,而字辈规则代际相守,使得“差序”的“近代”家族认同具有抚今追昔重构大家族的可能性。2009年杨家塘杨姓族人的纪念杨氏先祖行为,是在动员了杨家塘以外的红岸村等十几个村落的同一祖先的杨氏族人,在那次大聚会中,他们梳理字辈,认祖归根,重新规范树大分枝后家族内部的辈份,使得淡忘已久的大家族观又得以重新强化起来。

表1 红岸村杨氏族人的字辈
(二)家族认同的隐性表达
一般而言,传统回族家族间的互动行为集中体现在婚丧嫁娶中,它是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通过一种互惠式的彼此“礼物交换”,将家族观念展演并强化在几个家庭间的互动行为中,它在异于汉人大型的祭祖仪式中,彰显出了回族人家族认同的构建方式“隐性化”的一面。例如干尔曼里(搭救亡人的尔曼里)、婚嫁中的“吃茶”等民俗中,杨氏族人的家族认同的构建更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1.婚礼宴席中的“吃茶”。“吃茶”是宁夏西海固回族“婚嫁”中传统的家族行为,是新郎的亲族在其结婚当天的“吃筵席”时,设宴款待来送新娘的娘家人。这一山区回族人的民俗行为,以家族为互动单位,有主家(娶媳妇家)、吃茶家、安家三种角色,承担着“吃茶”和“安客”两种职责。笔者曾在另文中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这种吃茶行为,自杨氏族人到红岸村,就传承于杨氏家族内部,家族内部的核心家族是承担吃茶的主体,他们告诉笔者,以前他们同族谁家结婚,都要举行一个婚礼宴席前的家族会,他们谓之曰:“吃汇伙”,以此来明确吃茶的主体。在杨姓族人中,“近亲”家庭间的“吃茶”作为“礼物交换”,正是家族内部间的这种特有的“礼物交换”形式,将杨氏家族中由于分家导致的核心家庭为主导的松散家族连接起来整合为一体。同时家族内部间礼物的对等交换,用杨氏族人的话说就是“骗工”中,也就是你给我“吃茶”,我欠你家一个“工”(表达“人情”的一个单位),以后我再给你还上。这里面包含着一定的功利因素,彼此的互惠才是最实质的目的。在核心家庭占主导的杨氏族人中,“吃茶”有着一套具体的运行规则,作为杨氏族人在婚嫁中的互动行为,主要是在一个爷爷的党家子内部的核心家庭中,“四服”以外就很少见了。总体上说,“吃茶”从根本上体现着回族乡村家族基于血缘关系上的远近亲疏和以己为中心划圈子的“差序格局”特性,也就是说“吃茶”总是在家族血缘间的亲属链上运转,以亲疏远近的“吃茶”与“不吃茶”的群体行为中,家族观念在差序中淡化或在家族间的彼此互动中家族认同得以强化[6]。
2.搭救亡人的尔曼里。学者在论及宗族组织,重视的是“祠堂、族谱及族田”三大要素,郑振满认为迄宋以来的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普遍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不是以上这三大因素,而是各种形式的祭祖活动[7]。不同形式的祭祀形成的一个“祭祀圈”,是宗族内部联系最为密切的凝聚力最强的亲属团体。西北回族社会中也有着祭祀直系父辈的行为,回族人称之为“搭救亡人的尔曼里”。这是一种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举行的“尔曼里”形式,它是最为普及的家庭(族)内部的规模最小的“尔曼里”,每年在亡人的忌日上举行一次。它存在的主要目的在于搭救亡人,客观上它作为一种“集体表象”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是回族社会中家族血缘关系传承和认同的一种符号标志。笔者在红岸村杨氏族人的调查中发现,干这一“尔曼里”的主体,一般都是在同一家族内部的几个核心家庭举行,搭救的对象是同一个爷爷或同一个父亲,或同一个奶奶或同一个母亲。这种行为贯穿于三代人之间,也就是儿女给去世的父母,父母给早逝的儿女,或者孙子给去世的爷爷奶奶干“尔曼里”,超过三代者较少,可以看出乡村回族家族认同的特色。干“尔曼里”的各家为“党家子”或“一门子人”“本家人”,这种“尔曼里”的符号意义在于它是同一家族与其他家族之间的一条边界,只是这种认同随着家族再生产,使这种家族边界富有动态的流动性。但是总是在遵循着三代血缘家庭为“尔曼里”主体的约定俗成。在年复一年的不同主体间的纪念亡人的“尔曼里”中,在动态中构建和强化回族人家族认同的集体记忆,成为乡村回族家族认同的一种特有方式[8]。
四、家族认同的时代变迁
当今时代正处于一个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中,乡土中国在逐渐走出传统,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意志的彰显。使得传统家族秩序受到挑战,随着带来的是家族间世俗矛盾的加剧,家族观念弱化。在红岸村的杨氏族人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原本是“党家子”的家庭间,现在间的关系已大不如以前,过去间的往来较为密切,现在交往渐少了。但家族内部家庭间的矛盾出现,家庭间长期处于互不往来的局面,家族内部的团结较差,“党家子”的观念就更为弱化。同时在传统“长老时代”,家族内部辈份高年纪大的老人,在家族中地位也是最高的,也往往受到整个族人的尊重,他们往往是家族中的族长,甚至是村里的“庄主”,也是清真寺里的学董。现在的杨氏家族已无权威性的族老,在年轻人的权力分配中,老人的权威趋于象征性,清真寺里的学董年轻化,作为家族利益的代表,本身却缺乏传统权威的权力表征和运作机制。
在家族认同的构建方式上,其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均发生了变化,如起名中的字辈和婚嫁中的“吃茶”,等等。首先,在杨氏族人起名上辈份趋于混乱。杨氏人从第一代杨天虎定居红岸村,如今已是繁衍生息了近十代,应该说从第一代到第七代,字辈保持的相对较好,但是到了第七代文字辈后,也就是今天村里杨氏家族的八零后和九零后一代,字辈的恪守已被完全打破。根据笔者的调查,到了这一辈,规则应该是建字辈,但是根据笔者对全村这一辈人的起名考察发现,遵守这一字辈规则者只是很少的几个,大多数都是在这一字辈上随心所欲,大概有20 多种不同。笔者就以村民杨志F 家为例,这家人共有5 个儿子,其中4 个结婚的儿子中,孙子的起名各不相同,老大的儿子名字为杨富×,二儿子的两个儿子为杨×,三儿子的儿子为杨×,四儿子的两个儿子为杨万×,起名上一家人已无法统一了。以至于村里有人感叹:这辈人人还能说清,到了下几代人,辈份就彻底乱了。这种忧思并不是一种杞人忧天,也是一种即将面对的事实。今同心县五丰台杨氏族人从源头追溯,也为羊圈堡杨氏族人的分支,如今也面临着字辈混乱,辈份无序的现实,2009年其族人新修的《五丰台杨氏宗谱》中就写道:“上述字辈谱(发、达、德、福、生、百)自百字辈(6 世)开始,离经叛道,如脱缰之马;汪洋恣肆,如泛滥洪水。三代重名,四世同讳,已无辈份可言,令人堪忧。”[9]其次,作为家族认同隐性方式的“吃茶”走向历史终结。自2000年以来,“吃茶”在红岸村的杨氏族人中逐渐成为过去式,笔者在红岸村中亲身感受到这一点。传统的同一家庭内部血缘亲属“吃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某一核心家庭为单位所操办的筵席,昔日同族几家“吃茶”成为了红岸村杨氏族人的历史记忆。改革后的“吃筵席”,简单快捷,由新郎一家来置办,整个婚礼程序中“吃筵席”的时间大大缩短,娶家动灶,亲族只上礼。据笔者调查,从2008年11月到2012年3月间,红岸村杨姓人共有32 家子出嫁女儿和娶媳妇,其中无一家再有“吃茶”和“安客”的行为,婚礼的筵席基本上都是由一家人全部完成,“吃茶”的家族性特征明显减弱。与此同时,在干尔曼里上,杨氏族人原本是以同父的兄弟家庭一起来过,随着“党家子”间矛盾的滋生,有些家庭也选择单另独家干尔曼里。
2007年以来,杨氏族人中出现家族复兴的势头,由同心县杨家塘杨氏族人中的几位退休老干部发起一场认祖归根活动。在他们的倡导和组织下,召集了海原县红岸村和贺堡村、同心县杨家塘、固原市原州区羊圈堡村等各地的杨姓族人,齐集百年前杨氏老祖先居住过的老庄子哇,立碑标记,并以集体干尔曼里的形式纪念和缅怀先祖。在此活动中,他们萌生了修族谱的想法。在历来认为修家谱是汉人行为的西海固回族人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一次,当然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为杨氏族人清朝同治年间迁移至此,如今已繁衍生息至十代,已有5000 多人,树大分枝,分布在宁夏、甘肃、新疆3 省10 多个县几十个村,其调查的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杨氏族人几年的努力,终于在2009年修成了《杨家塘杨氏族谱》。应该说,整个活动从发动到举行,家族认同的强烈情绪被调动起来。在认祖归根后,活动并没有达到其预定的目的,在整个过程中,主导和参与者都为虎夫耶(老教)的杨姓族人,伊赫瓦尼(新教)族人很少参与进来,使得这样一次家族认同的构建实践,从眼前来看,似乎很成功,从长远来看,意义不大。《杨家塘杨氏族谱》中对字辈加以规范和制定杨氏族规等,其实这只是发起者的一厢情愿,在今天这样一个家族观念日益淡化的时代,难以被普遍遵守。
五、西北乡村回族社会的“无宗族”特性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西海固乡村回族家族的自身特征。不管是在其起名的字辈,还是在婚嫁中的吃茶和搭救亡人的尔曼里,以及在当今这样一个介于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中,家族认同逐渐弱化的趋势,无可辩驳地彰显出在西北乡村回族社会中鲜明的无宗族特性。笔者这里是以汉文化语境的“宗族范式”和乡村为单位而得出的结论,如果超越乡村用另一种视界来看西北回族社会,宗族不仅存在,却彰显出另一种存在范式,笔者另文中会具体论述。也有学者认为西北乡村回族社会存在着宗族现象,如张同基在《纳家户透析:回族农村宗族与家族发展态势》一文中,从宗族是拥有共同祖先的同姓亲属群体的定义出发,认为宁夏永宁纳家户历史上存在着纳氏和其他姓氏的宗族势力,伴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以及具有现代民主性质的基层权力机制的建立,使纳家户的宗族势力走向终结[10]。笔者认为,张文中提及的纳家户“宗族势力”,并不具备汉人宗族组织的基本特性,一般而言,学者论及宋明以来的宗族组织,是“用祠堂,族谱与族田这三件东西联结起来”作为符号表征[11]。纳家户呈现给人们更多的是一个纳姓占主导的大家族回族村落。以研究西北回族穆斯林见长的犹太学者李普曼(Jonathan N·Lipman),在其专著《熟悉的陌生人:西北中国的穆斯林史》(Familiar Stran-gers: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中,把西北穆斯林社会描述为中国边缘的具有二元特征的社会,这既是一个缺乏伊斯兰社会调节机制的穆斯林社会,又是一个缺乏东部“中国”社会调节机制,尤其是士绅阶层的中国社会[12]。李普曼以客位视角看到了西北回族穆斯林作为亚文化群体,在与大传统互动历史中的边缘境遇形成了具有“熟悉的陌生人”的尴尬,尤其是他认为回族穆斯林社会缺乏中国东南的“宗族范式”,此观点甚为客观,西北乡村回族社会的无宗族现象有其深层原因。
第一,穆斯林独一信仰与宗族组织间的无法调和性,集中体现在回族人独特的祭祀模式上。汉人构建宗族组织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敬祖祭祀,祭祀祖先是一个重要的宗族内部仪式,这个客观上具有家族认同功能的仪式行为,其背后有着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回族人的祭祀仪式,如搭救亡人的尔曼里,其目的在于活着的人通过善举的行为祈求真主饶恕亡人的罪过,祭祀在主观上是对亡人的搭救,这与汉族人祭祀的价值观上截然相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族人不可能发展出如汉族人的敬祖祭祀的宗族文化。相反的是东南地区的回族人的宗族组织,其之所以能够生成,在于这些回族人已彻底汉化,放弃伊斯兰信仰,如福建泉州的丁氏回族人和陈埭的蒲姓回族人。他们的祭祖行为,已无西北回族人尔曼里的对己父辈亡人的搭救属性,除了纪念和缅怀,“远以追水源木本之义,近以报属毛离裹之恩也”[13]。更具有祖先崇拜的汉族人的祭祖行为。西北回族人严格恪守宗教信条,但也敬祖尊亲,其祭祀的尔曼里以三代人为主。这种祖先祭祀的空白随着苏非门宦的出现而弥补,也就是西北苏非门宦内部的给逝去教主干尔曼里,这种尔曼里形式上等同于汉族的祖先祭祀,但是祭祀与被祭祀者并无血缘性,更多的是对逝去教主的缅怀和纪念。可以看出,回族人从血缘上,无法生发出“继承式宗族”,从宗教的维系上,又能建构出具有“继承式宗族”特性的门宦内部纪念道祖或教主的尔曼里。总之,回族人的独一信仰和杜绝以物配主的信念,使回族人群体的建构具有超血缘的特性,这就不可能发展出宗族产生的关键因素,也就是祭祖行为,也不可能构建出共有的“祭祀圈”,使得宗族产生缺少长链条的血缘纽带环节。
第二,穆斯林的“乌玛”精神共同体的信仰认同与归属,使得回族人在保持血缘纽带的家族认同中,更容易将群体认同和归属集中到“乌玛”凝聚的哲玛提上。回族先民进入中国便以“蕃坊”的形式定居下来,这种“蕃坊”既是中华“文野之别”的符号边界,也是伊斯兰“乌玛”在异质文化空间的生根发芽。“乌玛”或“稳麦”(Umma),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后,穆罕默德在打破阿拉伯人以血缘家族、肤色、地域等人群整合要素的过程中,在伊斯兰信仰的号召下,建立的信仰共同体。“稳麦的基础是信仰,伊斯兰只承认共同敬畏真主,服从穆圣,遵循伊斯兰法制的人,都在稳麦中”[14]。“乌玛”理念直接促成了回族人的哲玛提居住格局,成为哲玛提形成的“精神原点”。哲玛提正是“稳麦”这个精神原型在中国社会中的复制与投射,并成为“稳麦”的实体性社会结构和文化操演、传承的社会空间[15]。因此,哲玛提对于回族穆斯林而言,是他们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中,在同而不化的本土化中的至高认同,它形成于伊斯兰信仰,同时又固化伊斯兰信仰为目的,是回族人多元认同中最有凝聚力的第一认同,这种认同也只能形成于穆斯林信仰群体中。体现在回族村落中,同一血缘基础上形成家族群体,并具有着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这种认同最终又落附到哲玛提的认同之上。我们看到的是回族人更多地把精力放到哲玛提之中,不是家族中。在汉族社会中,宗族有不同的规模,可以一个村落有一个宗族,也可能有几个宗族,还可能多个村落构成一个家族。但在回族社会中,一个村落中可能因为群分类别而形成几个哲玛提,或者几个村落共同归属一个哲玛提。哲玛提既是同族人构建的结果,同一家族也会被分割在不同的哲玛提中。
第三,特殊的遗产继承制度。郑振满在论述到他在福建农村中总结出的三种宗族组织形式之一的继承式宗族的形成时,其主要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继承有关,也是不完全分家析产的结果。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遗产继承制度,是以分割继承为特征的。但在实际上,民间为了缓和分家析产对于传统家庭的冲击,往往采取分家不分祭,分家不分户或分家不析产的方式,对宗祠、户籍及某些财产实行共同继承,使分家后的族人可以继续保持协作关系,从而促成了从家族到宗族组成的演变[2]。回族人在遗产继承上,是典型的分割继承为特征的。如上所述,红岸村回族人有1357 口人,却又分为302 户,家庭结构特征几乎接近核心家庭。分家在回族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红岸村中就有很多多子家庭大多都是婚后分家后老人单过的“空巢家庭”。对于回族人而言,分家就是分产,经济上的独立,意味着单门立户,在干尔曼里(搭救亡人)中,时间是同步的,之间又有协作的关系,但干的单位却是一家一户。总之,这种完全迥异于汉人社会的遗产继承制度,是回族家庭不能实现向宗族演变的关键因素。
注释:
①关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有待商榷,杨家塘和红岸村的杨氏族人确系同源,但并非是同治年间从陕西或河南逃难而来,这种说法实为杨氏族人对同治西北回民起义历史记忆的一种主观表述;笔者这里更倾向的是,杨氏族人本为固原三营镇羊圈堡的杨氏老户,羊圈堡杨姓回族人是明朝老户,只是清朝后期,随着族人规模壮大,树大分枝,一部分杨氏族人外迁谋生。根据笔者对红岸村杨氏族人杨志元老人(现年78 岁)的调查,根据他们的回忆,杨氏族人的第三辈人在口音上跟现在是一样的。既然是从河南或陕西迁来,那么他们的口音肯定还是有着陕西或河南的口音。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口音总是跟父母或家人直接相关,况且乡音难改,不可能到了一个人际罕见的地方,乡音就整体性地改变了。事实上,今天,红岸村杨氏族人的口音与羊圈堡杨氏族人一致,只是杨家塘人随同心人的口音罢了。
[1][英]里弗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
[2]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47-78.
[3]刘华.海原县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1,3.
[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68.
[5]太原郡王式族谱[EB/OL].www.chineseroots.com.
[6]杨文笔.宁南山区回族“吃茶”的人类学观察——红岸村田野调查研究[J].民间文化论坛,2010(1).
[7]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03.
[8]杨文笔,马泽梅.回族穆斯林“尔曼里”文化解析[J].世界宗教研究,2010(2).
[9]杨少清.宁夏·同心五丰台杨氏宗谱[M].内部资料,2009:8.
[10]张同基.纳家户透析:回族农村宗族与家族发展态势[J].回族研究,1998(3).
[11]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4).
[12]周传斌.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J].西北民族研究,2005(1).
[13]马建钊.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62.
[14]易斯玛伊·法鲁克.认主学:在思想和生活中的涵义[M].阿立·蒋敬,译.民间版本,2004:144-145.
[15]杨文炯.回族形成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民族研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