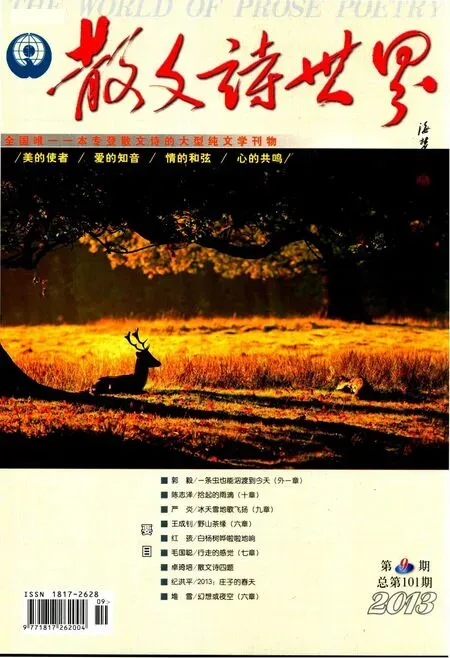拾起的雨滴(十章)
陈志泽
锯——听阿炳奏二胡曲《二泉映月》
瞎子阿炳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
老百姓阿炳处身在苦难生活的茫茫黑暗之中。
双倍的黑暗压着他。民间艺人的阿炳就用他粗糙的手拉动他音乐的锯子锯这黑暗。
阿炳的手在颤抖。锯这无边的黑暗得使尽全身的力气。
他锯出黑暗的汁,点点滴滴,抑或细流……
似断非断,有种如剜如割的锐利与深重。
他锯开了黑暗的缝隙放飞了心中的倾诉——如闪烁的游丝、转瞬即逝的流星、隐约的渔火、金黄色的灯盏;如扬着沙尘的风、泣血的雨,有冷的泪的迸溅和热的血的涌流……
他锯出了星星点点的光明,锯出了比泉更清澈、更欢跃,比月更明亮、更纯洁的白光,在黑暗中蜿蜒流淌,起伏穿行——直到他的锯子又被黑暗紧紧咬住……
听 石
一种隆隆之声从地下上升到天空的尽处,这是从石山的内心释放出来的。而一些直插云霄的“石笋”发出的是拔节的声响。还有对于风的鞭打发出的抗议,陨石撞击的感叹、流星嘹唳的悲鸣……以及空谷的回声。
在我抬眼望山时,山石发出的巨响震撼了我——渐渐地,巨响里流淌出了七彩的、轻音乐似的柔美!
待到我想听个明白,石就屏住了呼吸,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勋 章
石山耸立在夜的暗影里。夜色渐渐隐去,浓雾又来纠缠。天光刚刚透出,雨就急急赶来扑灭……
石山在煎熬中自有一种亮色晃晃悠悠。
石山显得更陡峭了——为了把进犯它的漆黑、阴霾和骚扰统统泻到脚下……
石山耸立到新的高度,太阳就出来了。
太阳是宇宙授给石山的一枚勋章,此刻灿烂辉煌挂在了山的胸前!
鹿之角
鹿举起水灵灵的两根树枝,在山林中跳跃着,时隐时现。
树枝日渐茂盛,不曾想某一刻成为剑戟——争夺爱情而格斗的武器,碰击之声传于四野。
突然,一声枪响,一阵血的迸溅。
树枝被砍伐。中药铺里,气血贯铸的鹿茸一直充足。一盒盒玲珑剔透的薄片等待着“壮阳”的验证……
有些事情是刻在骨头上的
有些事情刻在身体的什么地方都留不下痕迹。
有些事情刻在骨头上——一字字都溅出火星,发出浊重的声音。
有些事情是重复着刻下的,重重叠叠乱如麻。
我时常割开血肉,为了阅读,为了不忘,为了不再有那样的事情刻在骨头上。可割开的血肉很快又愈合了,重复刻下的事情又被掩埋,只有在灵魂刮风下雨时骨头疼痛,内心的闪电才照亮上面刻下的每一个字……
被覆盖的根
树浮出地面的根被斩断,树周围的土地被打磨光亮的大石板覆盖了。大石板密密地铺排过去的时候,树不做声,根不做声。
孤零零的树干竖立着。谁也没有留意树的郁闷、树的痛苦,更没有留意根的重压、根的窒息。
树不肯死去。
根用自己的坚忍医治伤痛。坚忍是无形的,却能贯通气脉,什么障碍都能穿透。
根没有腐烂,它延伸着、奋力地延伸着。
有一天,人们发现根周遭的地面拱了起来,再后来,地面上那些覆盖的大石板七零八落了……
翅 膀
行走在路上,忽遇蝴蝶紧跟着在身旁翻飞。蝴蝶的两片一样大小的花裙裾拍打着,将春的图案一次次相互印染,绚丽斑斓就愈是浓郁。
抬眼,苍鹰正好在头顶上游。它在风云里浮动着,沉思着,张开的两张席样的大翅,纹丝不动……
我走着,一左一右两条腿,一前一后协调迈进,这也是一双对称的翅膀,将我送到期盼的远方。
掀动书页
一阵微风。犁耙走过的土地,痕迹的香飘起。目光漂洗的一颗颗种子撒入,潜进肥沃的希望深处。
掀动书页,就有雷声从心灵的田野上滚过,而细雨在风中若隐若现,寂静无声。
手指轻轻的触碰,这是农人在掀动季节的门帘,召唤丰收的临近……
喧闹的静夜
城市酣睡着。呼吸的气息,摩挲着静夜的肌肤。
120救护车载着急病的亲人,在城市的胸上划过,悄无声息地停泊在医院急救室门口。
医生、护士的询问很轻、很轻。他们之间的简短对话甚至只用手势示意。
手术开始了,无影灯照出月光的静谧与安详。
城市的夜,静极。
可此刻,我神经脆弱,经不起任何微小声响的惊吓。围屏遮不住手术器具偶尔的碰击声,如同钢铁的铿锵;输液的点滴,一滴滴降落在我的心上,却如同一枚枚炸弹,震天动地轰炸……
我的心跳,掀起阵阵血液的巨澜……
漫长的夜,延伸着万籁俱寂的空旷——行进的脚步声却在无眠人的心中震荡。
亲人终于睁开了紧闭的双眼,清晰的话音绽放在唇边——这是静夜里一曲生命的凯歌!
权力的缸——为某贪官画像
雄狮的雕刻。发亮的釉。张着大口,挺着大肚。
如此大缸,威严矗立,装什么用的?
美味佳肴、高档商品、情妇二奶、“红包”礼券……特大的缸,容量大着呢!就连各色桂冠也频频叠放,我所管辖,要取便取——高雅志趣嘛,与腐败无关。(殊不知“专家”的头衔也能换来财富,名书法家点墨成金……)
能盛接天空的雨露与云霞,能收集离奇的梦想,能吞食庞然大物,能吸纳过眼的云烟、飞鸟的影踪、必经行人的足音……
权力的缸,能容多而又多的难容之物。
权力的缸,洗刷得干净,小心盖紧,可还是常露出缝来。
权力的缸,终究要爆满(或被敲破),成为一地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