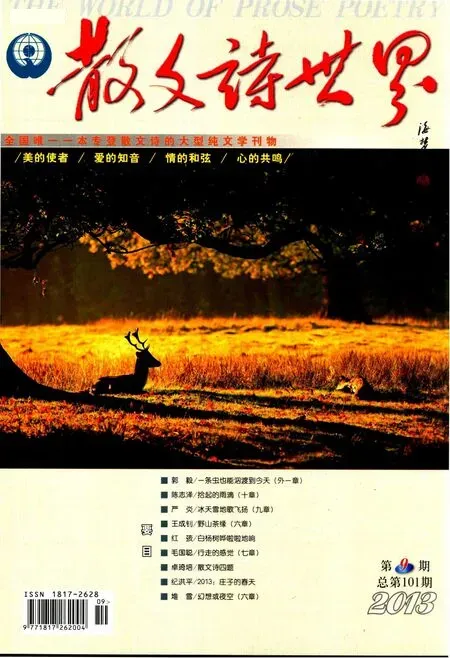一条虫也能泅渡到今天(外一章)
郭 毅
一
化蝶之前,我躲过的风雪,一直在吹。
家园里的树木、花草,是长路上的灯盏,照着的黑和白。
我所在的故乡,不同凡响,居住着蝉和青虫……这些友好的邻居,天天把歌谣传唱。
蚯蚓的地下,有潦草的碎骨闪动着磷光,在蚂蚁的脊背上运渡另外的桥梁。
萤火虫的夜晚,我把心放在半坡上,静看尘世的天空,漂浮着月光和星辰,以及更远处温馨的火。
过去的已经过去。路途上,那些颂歌和辉煌,我实在无心去打点,无力去述说。
我已腾出我的位置,交出了众人羡慕的殿堂。
那个觊觎者如愿已偿,在显要的地方指手画脚。
事实再也清楚不过,任何努力也无法将它改变。
没有鲜花。没有酒祀。我在远离了虚假的赞美和祝词中,一天天调整过来。
孤独的,是我默默地爬行,让敬畏和尊崇,在我赖以生存的植物之上。
那圣洁的光,从未有过的热情,从归途的天空闪来,显得格外明晰。
二
地火焚过的原野,卵的中央居住着金贵的黄胆。
稼禾的青黄移居的粮仓,飘着蜜蜂和更多蝶的翅膀。
我现今的巢,简陋如散落的枯枝,隐居在腐朽的树梢,被春天的叶子拥抱。
翠绿的是我的心,最先领略这世间的朝露。
有些清凉是必须的,才能驱散过剩的心火。
我憋屈的肢体,在这世间的教堂,因为单纯,而一次次弯曲,像蛇一样在大地上蜿蜒前行。
一次次脱皮,一次次新生,我都在炙热中飞翔。
天空淡远。云的颜色实在是太高了,它的飘逸在我的仰望中,遥不可及。
而我的卵,别先急于破壳,我还想靠着这温馨,美美地睡上一觉。
守护着的是这金贵的黄胆,一翻身,梦就飘散,落在油菜和稻谷的花上。
我俯首是瞻,把过多的晨露播放成语言。
三
时光缝隙里飘飞的叶子,是不是我的床?
我梦的入口和出口,罩着透明的帷帐,感恩茫茫尘世赐予我难得的清静,而不被拜访打扰。
我的魂走过的路途,丢弃的疤痕,已在躯壳上镶嵌了岁月的光。
多余的行走,在比腰脊劳损的折射里,深感不适。
彻夜的辗转,让心跳得厉害。
我打开一扇窗,请清风进来扑灭余火丛生的胆汁。
一地绿的波光,驱赶着旷野上的热和凉。
许多层次的家园,古典再现的前辈,也在这片叶子上。
它们咀嚼,让生活在忙碌里回味。
过多的梦在碎裂的骨架间,闪动着智慧和敏捷。
影子的故乡,一闪一闪。我拾起怀念,捂紧受凉的胸膛。
梦依然在叶子的飘飞里,和炊烟一同上升。
在神秘的天国,有我恬静舒适的床。
四
我的江湖不见得多么深广。我的爬行游荡出来的天空,也不见得有多么敞亮。
脚趾轻盈的部分,扣紧的是险峰,是深渊里不见刀子的急流。
那透明的,是浮于尘世的虚华和荣耀,在感叹中衰老、下坠。
走过的路,并不见陡。丢在身后的高山、峡谷……是快慰里吹起的一阵凉风。
同行者的羽毛,沾满命运的欢乐和悲苦。我在它们中间泅渡,用舌尖舔砥那深水,那俊美。
血脉切割刀子,斩碎了原野的光芒。流经我胸膛的经脉,脆弱到比花瓣还轻。
我依然在飘,披挂着半生的镣铐,从前世的河面驾一叶扁舟,渡向今生这岸。
对岸,有更多的蝶影,在花丛的上空旋舞。我知道,那种轻盈和飘逸,是卸壳之后的一种趋势,需要历练和超脱。
五
我的前世是什么样的物种,要把今生演化为虫?
也许我的前世是一头虎或豹,欠下了过多的生灵,要在今生赎回自己的血腥,要把威武、猛烈、强悍演变为零,在此生不再张扬。
其实,为虫不耐。既渺小,又蚀大器。
从我嘴里吞进的树叶、菜根……比我自身的形象高大。
那些委屈的沙砾,也在我修炼的大厅,呈现尖锐的光滑。
不食油荤,在素食主义的理念中,保留着原始的肤色。
有时,我在自然中迎合着潜在的法则,与更多的颜色融为一体。
为了生存,我不得不从俗如流,把翅膀,慢慢张开。
尘世辽远,天地深邃,因为我的小,我才脱一层皮又脱一层皮,把骨骼裹得这么坚强。
待修的空间,定有更大的风雪,在脉管里长鸣。
而我临近的秋天,已渐渐黯淡。
六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爬行,又算得了什么。
我贫弱的呼吸,摇不动一叶苍绿。这是我的睿智,而不被灵性的异族掠夺。
我不会站立,所以看不远更高的山岭、更宽的河流。
我的所见是寸光之内的风景,活得惬意而自在。那内里的颜色,灯盏遍地,厘清更多的灵魂。
靠着的美女,嘴里念叨着家事,已在这个精神缺失的时代颓废下去。
褶皱里的春天,需要一阵微风,才能吹散渐融的雪。
我出行的早晨,听见冰在远处叫喊。那撕裂的疼痛软化了我僵硬的躯体。
我伸展开去的胳膊,用拥抱的方式,紧紧地托着这个世界。
从北向南,只是理想的飞翔。我腰间的刀子,披挂执著和热情,等待秋风闪伤远处的山腰。
七
静静地,是我归隐后一贯的心情。
我收紧我骨殖疏松的脚步,把那些急促、激动放在合适的位置,蹒跚向前。
我谦卑地面对一棵草、一片叶和每条经过的同类。
甚至一丝细微的风,我都要去感激,去微笑。
我用真诚的心供养周围的诸神,请更多的敬畏接触我的清高。
风吹的方向,不是张开的翠绿,就是卷来的雪雨、刮进的尘土。
我迎头的地方,就在风口,讲述一地蓬勃和喧哗。
此刻,成都的大街上,秋风掀动的轮胎一地尘烟。
我趋向的地段,在急促的刹车声里,擦伤了平原的肤色。
卵的中央居住着金贵的黄胆,分泌出绿的苦汁,颐养我蜗牛似爬行的脚印,把此生的轨迹描绘得愈加清晰。
我是欢乐的,我在笑。
笑我的渺小,我的爬行,在这个世上几个简单的词,居然也能到达今天,居然还将行走下去。
外面,风雪在秋风的手势里,还将吹起更多的尘土。
在化蝶之前,我躲过的风雪,依然在吹。
萤火虫
有光芒,就会有梦想,在夜的天堂闪亮。
提着灯笼走路的虫子,一定不会碰到黑暗的墙壁。
它被自己的火焰照着,在夜的穹窿挥舞迷幻的影子。
始料不及的树,伸长峨冠黝黑的华盖,也在萤火虫的天空,欣然接受这神圣的庆典。
我看见众多的飞翔,携带着梦境里丰富的产物,在树冠环绕,跳荡着柔曼、舒缓,以及层次里更远的深长。
多美的场景,适合搁置圣洁的诗句。然而,我笔下的光芒,总在梦的边沿,粘满乡村的阳光和露水,显得那么慌张。
失重的灯盏,忽略了我的近视。我只能远望更多提灯的虫子,拨响琴弦,弹奏逝世的爱情,更多是怀念和饥荒。
弥漫夜空的萤火,圣诗一般高贵的教堂,总在虫子的背上,袅袅升腾,教会我的仰望。
我看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在光的黑暗中逐渐拉长。
那白的部分,是不是我不光彩的照耀,要被胸膛的那点光抹去?
我不语,并不代表我认可的世界就很辉煌。在夜的深处,依然有爬行的蛇潜伏在阴影里,等待光的火焰,驱逐周身的雾重与冰凉。
萤火虫的灯依旧亮着,像是什么事情的发生和结束,都与它没有关系一样。
而梦的故乡,闪过的河流,早已度过干旱的季节。
我在光的饥饿中慢慢萎缩,黑夜自然会来提升我。沉没的尘土掩盖了我的头颅,我的浑浊的眼里发着迷人的微光。
我愿意这样,从诞生开始,一直在世间的旅途,提着这盏不熄的灯笼,绕着梦的境地照耀。
这,现在是,将来也是。即使骨肉碎裂,灯也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