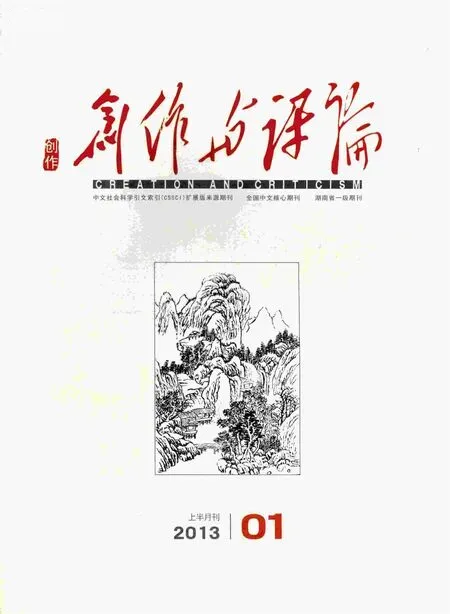雕镂时代的心灵——甫跃辉小说论
○ 杨荣昌
一代人的文学审美范式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同构关系。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他们没有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但成长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均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由此引发的社会阵痛为文学书写开掘出巨大的表现空间。这代写作者在转型时期成长并伴随社会浪潮的涌动走上文学舞台,他们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父兄辈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普遍以个人的成长史为隐形线索,深度挖掘转型时期的人心嬗变,以个体的成长体验折射具有普适性特征的生命流程。
一、个体经验观照下的代际特征
1984年出生的甫跃辉,在云南的乡下生活了十余年,滇西乡村的神怪传奇和巫风迷离的边缘景观,为他提供了最初的写作资源。年长后求学于上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染,深切感知城乡二元模式对峙所带来的冲突,由此开始了他对时代与人性的思考。他塑造了一系列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青年男女形象,他们强烈地向往城市生活,倔强地想以求学来改变命运处境,即使升学无望也要进城打工,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诀别。进城后的青年男女们,面对欲望化都市生活的诱惑,往往招架不及而被欲望俘虏,最终向现实投诚。变节总是从爱情开始,女青年抛弃一路走来的乡下男友选择另觅新枝,男青年在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挫折之下一蹶不振。时代显露出它极其脆弱的一面。
《巨象》中的李生,《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的李绳,《晚宴》中的顾零洲,都是被爱情抛弃、被城市遗忘的“多余人”,他们从乡下来到城市,原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城里寻得一块立足之地。深情的女性给他们提供了最初的精神动力,可现实总是袒露出它的残酷性,经济问题、门第问题、文化观念问题随着生活的日复一日成为恋人之间矛盾的根源,结局无一例外地是分手。男主人公的身上聚集了“外省青年”的种种特点,他们奋斗的历程让人感佩,经历的遭遇让人同情,但他们也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敏感自卑、颓废堕落,一遇到挫折就自甘沉沦,心理扭曲连带身体自渎,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如李生被城里女友抛弃后,骗取了同样来自乡下的女孩小彦的信任和好感,把她作为身体泄欲的对象,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报复”城市的目的。经历了一段对他而言没有付出真爱的恋情之后又始乱终弃,选择与自己的同学结婚,毫不顾及小彦的真实感受。李绳在遭遇城里女友抛弃之后与初中同学曹英偶然相遇,勾起了对往昔美好生活的回忆,两人产生若有若无的精神之恋。但没多久他得知曹英已有了男友,而且是个猥琐之徒时,竟不惜铤而走险杀了他,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顾零洲”是甫跃辉小说中常用的男主人公名字,有着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性格特征,或可视为作者为当代文学长廊创作的文学典型。《动物园》中的顾零洲和虞丽是一对恋人,蜗居在动物园附近的一间出租房内,虞丽不习惯那儿散发出的特殊气味,于是两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对抗”,焦点集中在开窗——关窗上。在坚持自我与尊重对方之间,进行着充满弹性与张力的“战斗”。最后即使某一方已为爱情作出让步,阴霾即将被风驱散,恋人却已擦肩而过,生活展示了它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
甫跃辉笔下的青年男女是被现代生活裹挟的一代人,他们在陌生的城市艰难打拼,承受着常人难以体会的生活压力,常以孤独者的形象漫游于寄身的城市,看着别人的灯红酒绿,为自己不可捉摸的前程黯然神伤。作者对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胆汁质的情绪特点和莽撞、冲动的性格有着敏锐的观察,尤其是对矛盾、犹疑和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把握得极为细致。他以细腻的笔触揭示当代青年在重压之下的精神迷惘与心理挣扎,对虽有真实所想却又不便明说的尴尬、自尊和试探心理的刻画,显示出很强的写实功力。小说人物的聪慧、勤奋、隐忍和无伤大碍的狡黠,合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处境,既有作者的个体记忆,又是对一代人集体形象的表征。他写出了一种值得信赖的生活现实,在人心的踏勘方面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高度,从中可窥视出这代人最具生命质感的生存方式,有力地拓展了“80后”文学的艺术边界。
二、切开人性的横断面
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文学最重要的现实作用应是对人类情感的不断丰富,对人性尊严的执着呵护,换言之,对人性光辉与善良质地的坚守,是重铸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甫跃辉小说中的人物尽管身处逆境,遭遇艰难,却大都保持着基本的做人底线,常给我们带来温暖和感动。《骤风》讲述了一位母亲陪同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到康复中心,一路上她絮絮叨叨,诉说生活对她的不公,抱怨儿子的痴傻,焦心家庭的困顿。种种情状,将一位母亲的无助与辛酸推向极致。此时骤风突起,天空仿佛一个巨大的胃囊,将“杂草、果皮、水桶、糟木板、破衣烂衫”,包括路上的行人等全部吞下。此时,一直被母亲数落的儿子突然“哇呀一声喊,就扑倒母亲,压在了身下,四肢摊开,烙大饼似的,严丝合缝地裹住了母亲。母亲抓住了儿子的一只手,嚷叫着,要翻过身来护住儿子。儿子只是死死压着”。儿子患有精神疾病,他处于本能护母,人性深处存留着善良。母亲尽管抱怨儿子是“孽障”,关键时刻却要翻过身来保护他。母子之间的血脉亲情,在危难之中转化成了人性的迸发。《白雪红灯笼》中的六指为了讨要血汗钱,从一个懦弱的打工者变成杀人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老正年轻时失手杀了人,大半辈子在惊惶与忏悔中度过,对有着特殊遭遇的六指的妻女自然怀着一份异样的感情。六指的妻女没有因老正是杀人犯而害怕或看不起他,反而认定了他是好人,默默地为他圆梦。小说展示了底层民众的辛酸,凸显了人性残存的温情,那漫天白雪中的一对红灯笼,犹如一团烈火,照亮了人性幽暗的夜空。《滚石河》中亮子、亮子父和未正面出场的亮子母都极见性格,人物关系也处理得极为妥帖,结发夫妻的爱情,母子之间的亲情,深藏于心却拙于表达,或者屈从于某种俗世的道德评价而羞于启齿。他的人物有一个普遍特点,即使身负屈辱也要尽量保持自尊,表现了底层人的坚韧个性。
甫跃辉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自有其发展的轨道,他们在喧嚣的物质世界中迷失自我,其贪欲自私的品格和对爱情的背叛,细究之下发觉都合乎时代特征和性格发展的自身逻辑。他们的所思所想,言语行为,包括出格的举动,都有值得人同情和谅解的地方。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弱点,但没有对其进行声色俱厉的道德谴责,而是任由人物按自身的命运轨道出场,自己隐入文本后面,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精细的刻画者,将评判的权力和任务交给读者。这种不忙于对时代下结论,不忙于对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体现出作者匠心独运的叙事技巧,是作家所应恪守的写作规范。它比那种急于跳出文本指手画脚、生怕读者没有判断能力的写作要可敬得多。
优秀的作家注定不会漠视这个时代的伤痛与浮躁,揭露社会病态,雕镂世道人心,是其介入当下现场、对现存秩序发问的方式之一。在今天,文学已很能再承载拯救民族苦难的大任,但对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探究,依然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甫跃辉不遗余力地探索人性的复杂性,甚至以出离常态的狂乱场景来表现人性的疯狂与贪婪。《苏州夜》深刻揭露了现代人在欲望冲击之下,残存的廉耻和尊严被一丝一丝地剥去,人最终蜕变为纯粹的肉体,由此指向了城市文明的畸形与虚假。《鱼王》和《鹰王》是两部中篇,都设置了人性善恶的对比,展示出边缘地带的迷乱景象。前文中,人们为了捕捉传说中的鱼王,狂乱地倾巢而出下湖捕鱼,对当地人口耳相传了若干年,某种程度上已被赋予神灵色彩的鱼王没有丝毫的敬畏和爱惜。《鹰王》刻画了一群人近乎发疯的虐待狂心理,他们对鹰王的偷盗捕杀,与解救鹰王于困境的余顺来相比,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利益驱使人走向疯狂之路。作者以锋锐的批判精神表达鲜明的人文价值立场,对人类信仰的失范和灵魂的污染,倾泻了一名青年作家的愤火。两部中篇在深层隐喻上有所差别,作者借鱼王死亡之后鱼骨被取走,表达出一种骨鲠在喉的痛感。鹰王面对几近疯狂的捕捉者,最终一改连日的慵懒消沉之病态,展翅冲天,飞向云霄,寄予了作者对新生的希冀。
三、叙写成长的忧伤与疼痛
甫跃辉小说主人公以青年男女或少年儿童居多,这是他目前把握得最好的两类人物形象。他把人物放置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检视其命运流程,以成长的视角回顾过往时光,深刻揭示人物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对话或对抗关系。成长注定是一个充满欢愉和痛楚的过程,成长的代价在所难免。《初岁》中的兰建成年少时对猪充满感情,但这份温情终不敌成人世界的冷酷与漠然,在理智而实用的成人眼里,“猪”只是满足食欲的牺牲。兰建成走向杀猪场的过程,抹去了少年时代的最后一丝童真,在二十一岁的前夕完成了向成人世界的最终转变。“杀猪”的仪式就成了对他而言具有特殊含义的“成人礼”。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在侄女小微的身上,兰建成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但是谁又能保证,十年、二十年之后的小微,不会变成今天的自己呢?《雀跃》中的金氏姐妹,《街市》中的车云飞,都成长于温情缺失的环境,这影响了他们后来几乎全部的人生价值取向。《老街》中的“我”曾对泰国女青年“阿三”怀着一份特殊的好感,这种眷恋贯穿了整个的少年时代,若干年后,当“我”得知那些曾触及内心最柔软记忆的人物都四处飘零、鸿飞冥冥时,心头顿然产生一种幻灭之感。甫跃辉写出了成长的疼痛,它没有撕心裂肺般的巨痛,却足以让过去的自己面目全非。在长篇小说《刻舟记》中,作者以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为线索,通过回顾成长中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逐一复活岁月给人留下的真实记忆。学校正常教育的缺失,家庭温暖的匮乏,造成了主人公乖戾而暴躁的性格,亲人们的一个个离去,更是给童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作者明知时间流逝再也无法追回,但仍以文字雕刻光阴之舟,叙写成长的记忆,借以祭奠逝去的青春,在极具个人化的经验表述中,指向了人类共同的童年记忆。
文学发展到今天,那些迷恋个人身体经验、仅写一己之私欲的作品显然很难满足读者的胃口。读者所关注的,是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信息元素,从阅读中可以透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情感迷局。这要求我们的作家要有建立文学与当下世界相联系的能力,文字要能直指人心,写出世道苍凉、人心向背。甫跃辉在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方面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维度,体现出对心理刻画的卓越才华,如《静夜思》中“我”对历史的冥想,《守候》中的东来在广袤无垠的郊野中,面对死一般的静夜以回想往事抵拒恐惧的侵袭等等,都极为深刻地触摸到人物的内心。他的小说构思奇特精巧,一些重要人物不直接出场,如《白雪红灯笼》中的六指,《滚石河》中的亮子的母亲,他们的形象是通过别人的转述来完成建构的,但依然栩栩如生。在结局的设置上,也常令人回味无穷,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作者充分调动语言词汇的功能,营造气氛,铺排环境,渲染心理,借以传达一种孤独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小说散发着哀而不伤的美学气质。
甫跃辉是一名有着精神之根的写作者,云南生活对于他的意义,是生命之根,文学之魂,是心灵栖息的地方,他在这里怀想天真的童年,舒展想象的翅膀。小说中的云南元素经由他的文学处理,都演化为人物精神成长的重要背景。在苍茫人海中前行,他不断回望来路,以锋利的语言之刀切开人性的横断面,雕刻出一幅幅乱相纷纭的人世图景,刻写出一代人的灵魂挣扎与现实伤痛。这种年轻生命践履中表现出的聪慧与早熟,以及将人生体验转化为文学表达的艺术自觉,必将助他不断抵达人性深度,攀越至文学的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