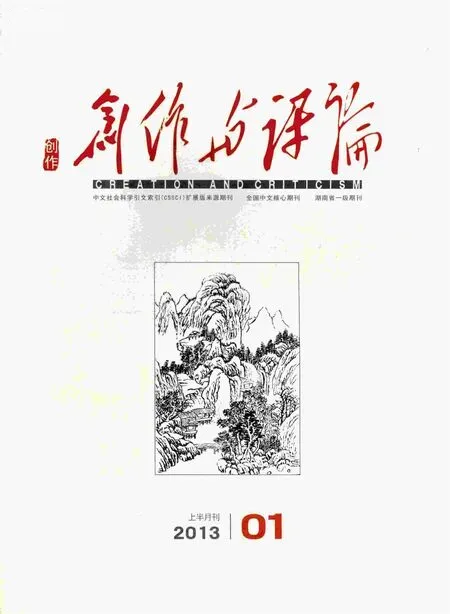文学之惑
○ 韩少功
文字的长与短
影视产品挤压文字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还原如真,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
没错,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挡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优秀的文学实外有虚,实中寓虚,虚实相济,虚实相生,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大意)。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或者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圈、插头?
画不出来,就是拍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美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出缺略、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追踪。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抽象化。钱先生未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辨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然而“白马”可入图,“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抽象,精神高蹈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图景,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动物化、白痴化?屏幕前“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式的恶嘲岂不会一语成谶?
一条是文字的感觉承担,一条是文字的抽象负载,均是影视镜头所短。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基因,互为隐形源代码,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两种大变局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
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秉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象、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想象一种批评
当代最好的文学,也许是批评——这当然是指广义的批评,包括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思想批评等各种文字。
这种揣测可能过于大胆。
如此揣测的理由,是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已经告别信息稀缺的时代,进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拐点之前,没有网络、电视、广播以及发达的报业,文学家是生活情状的主要报告人;文学作品享受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优势,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特质,成为效率最高和广受欢迎的信息工具,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与人生。但在拐点之后,如果不是对文学鉴赏有特别的训练与爱好,通过波德莱尔去了解法国,通过托尔斯泰去了解俄国,通过鲁迅和沈从文去了解中国人,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已很不够用,至少是不太方便。现在的情况是:细节与叙事不再是文学的专利,段子、微博、博客、视频、报刊、电视剧等都充满细节并争相叙事。每天揣着手机和敲击鼠标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于信息太多、太繁、太乱,以至自己的大脑形同不设防的喧嚣广场,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处于茫然无绪和无所适从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不饿,而是暴饮暴食之际需要一个好胃,来消化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
文学当然还能继续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看家本领,成为全球信息产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广大受众更迫切、更重要、更广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这个世界再增加几本小说或诗歌,而是获得一种消化信息的能力,关系到信息真伪的辨别,信息关系的梳理,信息内涵的破译和读解——这不正是批评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学本身而言,当文学日益接近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虚肿,一种富有活力的批评,一种凝聚着智慧和美的监测机制,难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药?
把批评总是视为文学的寄生物,既不聪明也不公正。体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元曲,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从来不会消亡,但会出现演变,包括体裁高峰形态的位移。那么,在一个正被大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批评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为的创新空间?批评——那种呼啦啦释放出足够智慧与美的批评,那种内容与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评,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天无韵的唐诗和宋词?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一点勇敢甚至猖狂的想象。
我不是批评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批评写作的学习者。我的部分文章,与其说是与读者对话,不如说首先是与自己对话,是帮助自己消化繁杂信息的一点尝试,以协调感性与理性、实践与书本,防止消化不良之后的病入膏肓。作为中华文化的传薪者,大家共同努力于批评的写作和阅读,顺应当下这个万花筒似的文化大变局,以继续精神的发育成长,也许不失为与时俱进之举。
重新生活
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
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不一样,可以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可以让时间停止和倒回,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孤独者重历友爱,智巧者重历幼稚,消沉者重历豪迈。
因为有了小说,过去的时光还可以提速或者缓行,变成回忆者眼里的匆匆掠过或者留连往返;往日的身影和场景还可以微缩或者放大,在回忆者心里忽略不计或者纤毫毕现。从这一点上来说,重新生活也是修改生活和再造生活,是回忆者们不甘于生命的一次性,不甘于人生草图即人生定案的可恶规则,一心违抗命运的草草从事,力图在生活已经结束以后,再造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像拿着已经用过的一张废车票,在始发站再一次混进车厢里始发。
捏着废车票再一次获准登车旅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废车票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多次生效——这就是小说写作及其阅读的特权。
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是我在重新生活时不得不多看两眼和多呆一刻的驿地。这里只有一些凡人小事,在这个浮嚣的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我在这里补上一些端详或者一些远眺,添入一些聆听或者一些触摸,我的第二生命就已经上路。哪怕是一条隐没在大山里的羊肠小路,也可能在这里焕然一新和别有风光,其陌生的光彩和气味让自己吓一大跳。
小说于我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比方说小说能够果腹和暖身吗?能够取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以及新闻吗?恐怕不能,恐怕很难。但小说至少能弥补过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说,至少能洞开一种新的过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于心的发现,增收一种更加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对此已感激不尽。如果读者们能从中分享到一丝微笑或一声叹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浑身有戏
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文学老师。他来自话剧团,在表演方面有经验也有兴趣,所以对我辈青年多了一条苛求:经常让我们做表演小品。比方说,让我们表演一下小偷溜进了主人房间时的形态,或者表演一下突然遇到往日情人时各种可能的神色。
我不擅表演,屡屡失败,自觉笨拙无比。但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了演员的不易。一个好演员,应该说浑身是功夫,浑身都有戏,从腰身到眉宇,甚至从脚尖到发梢,几乎都有活泼意味的随时闪耀。在很多时候,他完全不需要威武雄壮的大动作,不需要慷慨激昂的大台词,一出场,就能吸引观众眼球。哪怕只给他几秒钟的时间,哪怕不给他重要的台词和位置,他也能举手投足之间风生云起,流目顾盼之际气象万千,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把别人的戏都给抢了。这样的好演员,也从来都“吃”得住或“含”得住戏,在没有动作的地方同样有行为,在没有台词的地方同样有语言,独自扛上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的静场,也能让观众觉得目不暇接和满台生辉。俄国和法国的有些演员还特别愿意拿这种静场戏来斗狠,在每一道视线和每一个体态上,稳稳地下功夫。
可惜,现在的好演员不是很多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看得也太少,以我偏侠而肤浅的观感而言,以前的金山和赵丹的段位不低,但都已经去逝。当代的中国影视演员里,以前有过斯琴高娃、陈道明、焦晃、孙海英等,这些年来强手越来越多,但惨不忍睹的三流演员似乎也越来越多,比如男的大多只有个衣架子,女的大多徒有个好脸蛋,充其量是些漂亮的纸人和瓷人——这些台词机器实在顶不住了,就来点挤眉弄眼或者冲进冲出的多动症。你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如何往下演毫无主意,一出场就“慌”和“飘”,胡乱凑点形体套路,把出场时间填满就行。奇怪的是,这样的台词机器有时还被流行舆论捧红!
小说也是一种演出,不过是文字的演出而已。如果一个小说家文路很窄,笔力很浅,没有火爆的折腾就只能呆头呆脑,甚至没有暴力戏和色情戏便有气无力碌碌无为,那么这个作家基本上就已经作废。这样的作家太依赖极端的感官刺激,就像瘾君子太依赖可卡因和摇头丸,已丧失了感觉能力。这种人对日常生活没感觉,对人们的性格、习俗、情感以及文化特征没感觉,对植物、动物、阳光、土地等等当然更不会有感觉,那还叫小说吗?还叫小说的文字吗?诚然,爱与死是小说的主题(至少是主题的一部分吧),小说家也没有远离色情与暴力的洁癖。但爱不是藏春阁影集,死不是太平间日志,恰恰相反,爱与死如果是动人的话,如果是有价值份量的话,恰好是因为爱与死不过是作者笔下全部人生过程的水到渠成。换句话说,爱与死是山颠而不是山,是刀锋而不是刀。即便是要表达爱与死,功夫首先得在爱与死之外。
正因为如此,好小说家不回避刺激,但决不依赖和滥用刺激——只有末流演员,只有斯瓦辛格那种超级肌肉符号,才会傻傻地依赖那些看似很“爆”的情节和场面。好小说家常常是沉静的,因为自信而从容不迫。他们是一些兴致勃勃的观察家和品尝家,对日常生活百态时时充满感受和表达的冲动,因此一棵草,一条街巷,一个普通老人,一次言不及义的寒暄,都会在他们的笔下生龙活虎和变化多端。这倒不是饶舌者的喋喋不休。凭着对生活细节的精微体察和独特感受,这些高手们下笔就“吃”得住或“含”得住叙述,下笔便有戏,便有味,便有生活质感和感觉深度,便有审美和思想的丰足信息含量,便有文字的磁吸力、粘附力、繁殖力以及牵引力,哪怕是落笔在最普通的吃饭睡觉,哪怕落笔在最容易乏味的一个过渡性段落,他们也常常能给读者以惊讶,营造出文字本身的悬念——就像每一个细节里都隐藏着惊天命案,读者在滚滚而来的发现中不由自主地跟进,甚至能把某一段黄昏描写读得提心吊胆气喘吁吁。
文学是干什么的呢?文学就是把生活不断重新感觉和重新发现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全部生活不断重新侦破的历险,不仅是折腾在藏春阁和太平间。在这一过程中,爱与死不一定表现为情节和场面,倒是常常成为一种精神氤氲,弥漫和震颤在字里行间,是一种无形的文字紧张。
这当然是指一种较高的境界。
眼下先锋派有先锋派的套路,市场派有市场派的套路。先锋与市场其实都无罪,只是一旦成为套路,共通的毛病就是感觉的消褪,就是叙事的僵硬,就是缺乏生活汁液的文字大面积枯萎——这一切都掩盖在夸张和矫饰的刺激之下。你在这些套路面前可以看到预设的时兴观念(比如反腐或改革),或者常用的高新技术(比如荒诞化或魔幻化),但你唯独看不到现实生活本身的汹涌,看不到作者在一个个生活瞬间面的怦然心动和刻骨难忘,当然更看不到观念与技术在生活中的原创性酿制。所谓戏不够,鬼来凑,这不过是一具具华丽伟岸的木乃伊,在冒充人与生活。在这里,我愿意重提“生活”,愿意重提“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观察”、“生活是文学之源”等似乎过时的词语。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写作技巧、文学观念、知识配置、出版空间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都不存在重大障碍之时,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对生活的感受)不幸成为我们很多写作人的瘸腿。
在这时候,想一想我们在荧屏前的欣喜和失望,想一想优秀演员与末流演员的高下之分,有关文学的常识也许不言自明。
所谓文学经典是一个模糊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脱颖而出和影响长在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以及基石的意义。
这些作品大多留有中等阶级的物权印痕,切合读书人的总体利益需求和心理趋向——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编撰,以及向其它社会群体传导文学的职能。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则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官方文件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以后,一度强势的迷信与文件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经典却有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以抗打击、耐磨损、保值增值的超强功能,一次次重返书架和书桌。
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患自闭症,有的是同性恋……更重要的是,有的读书人依傍权贵,有的读书人亲近贫民,也是常有的事,生发出不同的文学风尚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包括约定对经典的模糊理解。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流行;但在另一方面,《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西厢记》或《红楼梦》,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或苦或甜的精英闷骚,或明或暗的愤世纠结,却可能进入广泛而持久的记忆——即便它们与太多底层群体几无相关,与乞丐、巫汉、乡村老太那里的文学活动几无相关。
这应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不过,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着了人们的某种痒痒肉,也有不胫而走甚至呼风唤雨一时之效,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权力、资本、士林清议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的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会折腾,面对一桶阴沟水,恐怕还是无能为力。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味、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或长尾猴,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而绝对的人性之道,或者说人类较广泛、较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和垃圾逐渐淘汰出去。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创造和开发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作为“资源大户”,分别富含了佛教和道教的文化资源,一如《三国演义》(帝王文化资源)与《水浒》(江湖文化资源),也会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相比之下,大仲马不过是浅水池里的好水手,张恨水不过是卖水货的旺铺面,大量探案、黑幕、艳情之类即便热销,却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不难看出,“经典化”诚然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底线和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性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在更大范围同时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前者有相对性,后者有绝对性;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前者是势之所成,后者则是质之所限与命之所定。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均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作用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至少需等待下一本文学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