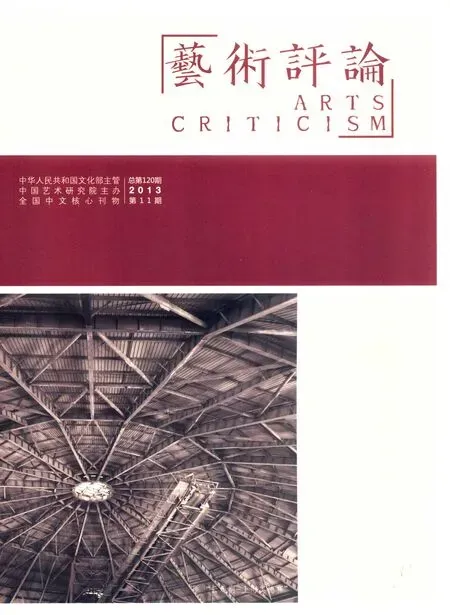人格尊严的悲歌
——李龙云和他的“小井”
郭启宏
剧院近日重排重演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我于看戏前后重读了文学剧本,感慨良多。这部作品被已故戏剧大家王季思先生称作“中国当代十大正剧”之一(见王季思主编《中国当代十大正剧集》前言),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时期中国话剧的一部代表作,《小井胡同》(以下简称《小井》)当之无愧;眼下面对导演杨立新的舞台呈现(演出应该是更完整的解读),我忽焉沉思,这部作品更是超越年代的经典,因为人性永远没有过时,我甚至很想请教季思师,这部作品的“戏骨”应该是悲剧的啊,它把尘世间人性的美好生生地撕碎给我们看,尽管它也给我们一个光明的预示。
李龙云在首演当年写道:“乡土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它铸就我一种特有的自尊,为我幼年的心灵涂上了第一层底色。它告诉我:什么是善良美好,什么是正直倔强,什么是底层人民的尊严……”底层人民的尊严,说得多么好!天上人间最值得赞颂的就是这一种尊严!
在剧中,我们看到这四九城里贬称“南贫”的小井,住着各种各色的草根,电车工人、面铺掌柜、小业主、旧警察、国民党兵、从良妓女……无论兵荒马乱,抑或狗跳鸡飞,小井人似乎都在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中生活,于不逾矩中示人以尊严。小井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一个南贫的贫字便否定了“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小井也不是《镜花缘》里的“君子国”,熙来攘往者固非“葛天氏之民”;然而,小井在低水准的生活形态中犹然呈现出邻里之乐,“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洩洩”。令人深思的是,在小井的世界里,若混混儿小环子者,馋,懒,不要脸,终其一生难脱人渣的“徽号”,却也撼动不了小井人道德的底线;而那位从乡下嫁到小井的小媳妇,却能够挺着“左派”的身板,借着“运动”的缤幡,呼风唤雨,所向披靡,把个小井搅得人仰马翻,而小井人顺着风直往前轱辘,差点把人性扭曲了。更令人深思的是,小环子只是“小巫”,小井人对他可以劝阻,可以斥责,可以摆弄水仨儿的“金钩马”,可以抡开春喜的恨巴掌,便是无奈也还可以摇摇头叹息一番;小媳妇才是“大巫”,面对小媳妇,小井人显然没了底气,敢怒不敢言,虽说她没有三头六臂,她却有着强大得叫人望而生畏的背景,那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那是“战无不胜”的思想体系。直到小环子故意诬陷小媳妇的男人“搞破鞋”,以“没影的事”让小媳妇当众出丑,一巷草根才得以拍手称快。深恨小媳妇的“阶级感情”使草根们人同此心,大家首肯了小环子的坏招儿,连刘家祥也略无恶意地调侃着小环子,“你小子合着逮谁咬谁!”直到后来,石掌柜更出高招儿,让大牛子串通火葬场的铁哥们,愣是开来汽车,生生地把小媳妇往火葬场送,小井一时间开锅了,乐得吴七对许六夸说,“小井真出了高人啦!”(当年饰演小环子的任宝贤、饰演小媳妇的吕中,其演技几臻极致,至今印象深刻)小井人对于小媳妇的小小的胜利,看似无足轻重的一两次小玩闹,实则是小井人彰显人格尊严的凯歌,受众在开心大笑之际,当会滴下苦涩的泪。《小井》内涵的深刻性正在于此!
蓦然想起鲁迅!他认为人性应该偏向于强悍,他所要呼唤的,是“精神界之战士”。当代文学理论家何西来也在呼唤“文化战士”,他在《文格和人格——邵燕祥杂文论片》中提出“胆识”的概念,认为胆识是“文化战士的最可贵的品格。他的理性,他的真诚,他的人格,都集中地通过胆识表现出来。”我想,真正的编剧应该是“文化战士”,是“精神界之战士”。重读《小井》,我很钦佩李龙云作为一个剧作家的艺术良心和艺术勇气,即所谓胆识!试想,那是“文革”硝烟刚过的时节,能做到言必己出,不攀附,毋依傍,不唯书,毋唯上,而且敢于公开宣讲出来,便是有胆识!西来兄举邵燕祥为是,我意李龙云亦然。放眼当代剧坛,阿谀奉承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庸俗搞笑者有之,自欺欺人者有之,抄袭剽窃者亦有之,而孤独于“闹热局”之外的思想者却不多见!兴思及此,教我忆起龙云与我的一件往事。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某一时段,有一天,龙云告诉我,他想写竹林七贤,问我该找哪些资料?我不假思索,脱口便说《世说新语》。他想了想,没有再问,我补充说,魏晋时期的笔记小说也可以看看。龙云是个含蓄的人,仿佛闲聊,烟云过眼。直到龙云仓促辞世,我忽然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我在说废话嘛,他能不知道《世说新语》?回忆起他当时神情,肯定是十分失望,我自诩藏书颇丰,为什么不能替他翻找?如今想来,反省之际又多了一层思考,他何以想写竹林七贤?是有感于嵇康的绝调《广陵散》、阮籍的猖狂哭途穷,还是偶然触及“软肋”,或读《与山巨源绝交书》,或读《思旧赋》,而心有与焉?我隐隐想到“闹热局”外孤独的思想者……
李龙云是个极具天赋的剧作家,从《小井》呈现出来的,除了最可贵的品格——胆识,还有他过人的艺术感觉。比如语言,这种艺术感觉让他从众多的“京油子”堆里脱颖而出,他把“老北京”的方言、俗语、俏皮话,甚至流转于“胡同串子”嘴皮上的鄙俚词汇,经过艺术加工,雅化(而非脏化)而成老舍式的文学语言,凡庸的“京片子”哪里来得!又比如技巧,这种艺术感觉尤其表现在话剧的情节的编织上。想来似乎很有些日子了,身为编剧的人并不重视(或竟是不懂吧)编剧技巧,似乎认得字便写得戏,写出戏来,居然是个大外行!老兄台,你可以高唱思想,什么“时代主旋律”,你可以大话生活,什么“深入工农兵”,但倘若没有编剧技巧,何必定要写戏?《小井》第二幕,身为党员、记者的七十儿抗美援朝归来被打成“右派”,蒙在鼓里的是以儿子为荣的老爸马德清,一旦父子相见该是何等叫人心酸的难堪的场面!戏剧流程应在“误会”之中。此时,若角色与观众皆一头雾水,则效果大亏欠;若舞台上下一目了然,效果也会减半。看作家如何巧妙运笔:他让七十儿预先向刘大叔(刘家祥)交了底,亦即将带来的感情纠葛扩大了范围,刘大叔得以古道热肠,因势利导,观众自然也就成了知情人,静观其变。看看,马德清还未上场,舞台已经厚积蓄势,于是,后面的戏怎么演怎么感人。受众诸君略识戏剧的主儿自可以“误会法”的技巧律之,却又未必谙熟这“误会法”的底蕴,这不是一般的技巧,不是人人学得用得的技巧,这是必得诉诸高尚动机与操守的技巧!试想,设若刘大叔不具爱心,是小媳妇或小环子,肯定要“荒诞”出另一番景象,演者不知其然,观者则颇受愚弄,哪来戏剧?由此看来,舞台上没有离得开思想和生活的“纯技巧”的玩艺儿,所谓技巧无一不是高尚道德的浸淫、崭新思维的展现。《小井》一剧,如斯不落斧凿痕的技巧比比皆是。反顾适才所说的“胆识”,唐人刘知几早就提出“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
中国剧坛能如李龙云者究竟有多少?我曾在公开场合信口开河,冒说了一个量化参照值——不超过二十名,不料好友伯益公大加驳斥:“充其量,十人耳!”中国这么大,人杰这么少,天注定李龙云毕生孤独,我从他想写竹林七贤推知,也从他留下的大量文字见得。
我与龙云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相知于毕生,而相忘于江湖,期间自然少不了同行笔会的雅集,也就有了把臂出游,樽俎交欢,而素常居京则很少串门,堪称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我每每推己及人,惋叹龙云的遭际。他离开人艺后写出的各类作品,我大多读过,却没有看到演出。我曾经既主观且武断地说过,国话和上海演出他的剧本不大可能比人艺更好,我其实没有门户之见,我只是觉得作家与剧院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互动,说句糙话,绣球配牡丹,瘸驴配破磨,非关好与不好,搭配终须得当。当初于是之他们把龙云调入人艺,都说合适;后来龙云离开人艺,都为之惋惜。我是少数支持龙云调动的人,不仅仅为“树挪死、人挪活”,更为龙云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此次从《小井》说明书上看到他当年说过的那段话:“(乡土)铸就我一种特有的自尊。”恰好为我昔日今朝的率尔立说做了注脚。曾记否?当初我对龙云说过一句颇有些沧桑的话:“我快到退休年龄了,也没有剧院团会要我……”我不能不说到人艺!人艺今天为李龙云重排《小井》,不但于艺术大有裨益,也做了一件大大功德事!艺术家与剧院的关系,即便从消极意义上讲,至少也应做到“两不负”:艺术家不负剧院,剧院同样不负艺术家;若从艺术行为上讲,创作与出品本是甲方乙方,而非雇佣关系,若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雇佣关系可以打造商业大片,似还有几分可信;若说可以“炮制”出真正艺术品,甚至经典,则近乎梦呓!呜呼!值此杰作上演之际,我祝演出延续辉煌,我想上苍当会开眼,让我可以仿李龙云句式,告慰好友:
“叫我一声剧作家,我会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