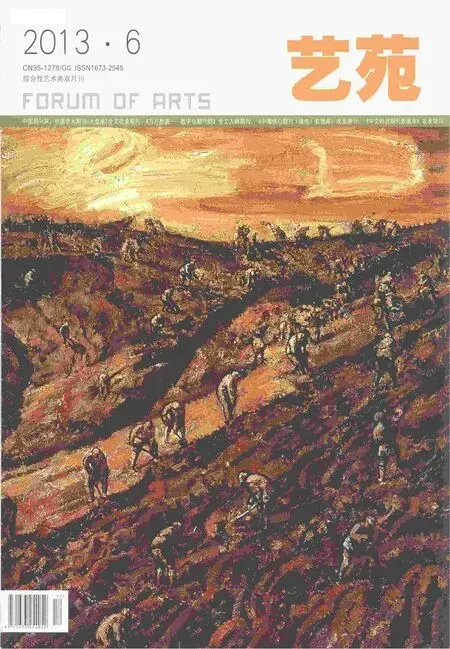进入情境,直感本体——戏剧教学方法新探索
文‖汪余礼
戏剧教学是我国实施生态艺术教育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培育新型生态人格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国高校现行的一些戏剧教学理念与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材里,当前一些高校的戏剧教学还深受陈旧的戏剧观、艺术观的影响,不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心灵,亦无助于新型人格的培养。经过数年教学实践的探索与反思,笔者认为,戏剧教学的重心不在于分析戏剧冲突、社会矛盾,而在于“进入情境觅珍宝,直感本体悟灵韵”;其旨归不在于认识社会生活及其矛盾冲突,而在于重铸人格与族魂。
长期以来,我国戏剧教育在“反映论”艺术观和“冲突论”戏剧观影响下,比较注重分析戏剧作品所反映的矛盾冲突或社会问题。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们仿佛增进了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内在矛盾的认识,或者知晓了某时某地发生过的严重冲突或存在的严峻问题,但只是增加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而已,那些矛盾、冲突、问题本身对其心灵几乎发生不了什么影响。因为,能进入大学课堂的剧作多半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品,它们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多半已随风飘逝,或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对于今人认识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转变观念,不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待作品,不把戏剧作品看作是“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的反映”,而是从审美的视角,把戏剧作品看作是“人的生命体验的陌生化、情境化、浓缩化显现形式”,并以此新观念引领戏剧教学的全过程,那么戏剧(尤其是那些经典剧作)对于我们的鲜活的、切己的意义将逐步显示出来。
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剧作,即便它们在表层上描写了社会生活,或触及某些社会问题,但在深层次上,其探索、表现的重心往往在于人的内在生命运动或人性的深层冲突。正是对人心、人性之发展变化的高度敏感与深邃体验,促使作家拿起笔来捕捉个中幽微与灵光,进而创化为作品。而戏剧形式的特殊性,在于时空的限制带来其表现生命体验的情境化、浓缩化特征;再加上艺术形式本身的反常性、陌生化特点,因此,可以说戏剧是“人的生命体验的陌生化、情境化、浓缩化显现形式”。在此观念引领下,我们对经典剧作的讲解,就不是要说明它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生活、矛盾冲突,而是要体会、阐释作家设置了怎样的戏剧情境,表现了怎样的生命运动,传达了怎样的生命体验。这里,进入情境以及情境中的生命运动过程,是踏上审美之旅的关键。
进入情境的过程,就是直感戏剧艺术本体的过程,也就是戏剧审美的过程。所谓“审美”,指的是直观作品感性形象并逐步领略其内在情感意蕴,同时也逐渐与艺术家心灵产生共鸣的活动。对于戏剧来说,其本体在于情境,进入情境才能实现审美。这里所谓“情境”,特指戏剧作品中由人物处境、人物动机、人物动作与反动作等要素所构成的情势、氛围与境况;它具有主客交融、虚实相映、不断流动、集中饱满的特点,是戏剧中最具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其中,人物处境通常由时空环境、特定事件、人物关系三要素构成,它是人物产生动机、发出动作的前提条件,也潜伏着戏剧悬念;人物动机是人物的情感、意志、欲望、潜意识等整个内在生命活动的总和,它是戏剧动作的内在动力,是戏剧悬念的重要指向,也是戏剧性的源泉;人物的动作与反动作包括角色/演员的独白、旁白、对白、静默以及神态、肢体动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包蕴着戏剧冲突,显示着戏剧悬念,推动着戏剧情节的发展。据此界定,“情境”是由“情”、“境”合成的,既有客观成分,也有主观成分。人物处境是戏剧情境的客观要素,是戏剧情境中随人物关系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基质性、域限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戏剧人物的命运;人物动机与人物动作则是戏剧情境中最富有活力和流动性、最富于主体性、也最重要的实体内容。质言之,“情境”既是人物展开其生命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人物实现其人格与命运的具体形式。在此意义上,“所谓戏剧的本体,就是情境中的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而“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作为“情境”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隐示着作品的形而上学质。罗曼·英伽登说:“形而上学质是一种特殊的气氛;这种气氛深入到一切,用自己的光辉照亮了一切。……形而上学质的显示,构成了我们生命的顶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生命和所有一切存在的东西中最深邃的东西。……它们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要显示的时候,可以让人们心醉神迷地看到。而且也只有我们首先而且干脆生活在那个情境下,或者感到和某个生活在那类情境中的人完全合为一体,它们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靠近、最活跃和最富于个性的。”可见,“形而上学质”是“情境”中最深层次的存在,是作品中特别吸引人但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某种“灵韵”;它隐示着作品最深层次的智慧,但需要欣赏者充分进入情境才可能领略到。由此观之,情境作为戏剧本体,乃是一个由人物处境、人物外在动作、人物内在生命运动、形而上学质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综合体。而进入情境作为直感本体的审美过程,关键是要进入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内在生命运动,并进而领略其形而上学质。下面试以《雷雨》的教学为例详论之。
《雷雨》是曹禺写的一首诗,是他出于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不可言状的憧憬”所写的一首戏剧诗。但在大学课堂上,这个作品经常被讲得面目全非。有的教授讲,“《雷雨》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揭示了它所依存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发展趋势”;有的学者说,“《雷雨》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表明了资产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有的老师讲,“《雷雨》反映了五四前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它彻底地否定了那个人吃人的社会,昂扬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亮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每看到这类观点,笔者心里总是疑窦丛生:如果《雷雨》真是旨在反映、暴露那些罪恶,它还有什么现代性或当代意义?当今的学生既不生活在封建家庭,也不是资产阶级,并且早已越过了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雷雨》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以反映论视角讲解《雷雨》,想必学生们会产生这类疑问。但是《雷雨》,就其根底而言,乃是可以影响人一生的伟大作品,对每一个现代人都有着切己的、重要的启示意义。
笔者曾多次对本科生、研究生讲解《雷雨》。我不会直接告诉学生,该剧反映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而通常采取一种曲折的方式,先是抛给学生一些疑问(比如《雷雨》中的第九个角色是谁?为什么说《雷雨》是一首诗?),以引发学生深入了解《雷雨》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一点点、一层层进入《雷雨》的情境中去。先从戏剧情境的营构、发展,讲到戏剧情境的翻转、中止,让学生领略该剧情境运动的全过程;然后仔细从剧中人物的处境,分析其各自的动机与动作,再阐发主要人物的内心流程,让学生如临其境地感受主人公的内在生命运动。走完这个过程,回过头来看,会发现《雷雨》实质上是通过设置一种危机四伏、愈显逼窄的戏剧情境,高度浓缩地展现了周朴园一生的三个阶段(从一个满怀理想的留学生,蜕变到残忍冷血的资本家兼冷酷专制的家庭暴君,再转变为沉静忧郁的忏悔者),并着重表现了周朴园在此三个阶段的内心伤痛、悲哀与反省、忏悔。第四幕有一场戏特别关键,它仿佛是该剧的“枢纽”,也透露了该剧之“天机”。在这场戏,周朴园深夜独坐客厅,回想起白天里侍萍的出现与控诉、蘩漪的蔑视与反抗、大海的仇恨与诅咒,内心里开始感到虚弱,感到不安。他开始感到“人间的事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作人不容易,太不容易”。尤其是侍萍的再次到来,让他感受到冥冥中命运的打击。原先“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周朴园,现在再也没有以前的信心和底气了。面对不可知的、隐隐让人感到恐惧的命运,他开始“退缩”:从恶胆退向良心,从魔性退到人性。最后两个儿子死去、两位妻子变疯的残酷结局,更是让他感到命运的神秘力量与自身的累累罪行。他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忏悔者?为什么要把周公馆捐献给教会做医院?是要表明他还良心未泯吗?从剧作整体来看,曹禺如此安排,是要探索人性与人的命运,并为自己并通过自己为每一个人思考:人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才能活出意义来?
周朴园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是特别发人深省的。他并非本性很坏的人,他的蜕变几乎是合情合理、而且颇具普遍性的,正是这一点触目惊心。当初,周朴园从德国留学回来,满脑子自由、平等的观念,大胆地撇开当时的等级偏见,勇敢地与仆人侍萍相爱了。他当时所遭受的社会压力、家庭压力可能远远大于30年后周冲所遭受的压力,但他比周冲坚强多了,即便家人反对他还是要跟侍萍相爱,不止相爱还要同居,不止生第一个儿子还要生第二个儿子。在1895年前后,敢于那样做的男人是极少的。于此可见周朴园的真诚与坚强。但在一个现实社会(而非心造的理想社会)中,人性究竟可能是什么?有多少人能始终保持灵魂的纯洁与高贵,从不堕落、从不蜕变?只要脑子清醒一点,对此是没法乐观的。那个时候,曹禺已清楚地看到,人性虽不见得本恶,但多数时候是比较软弱的,容易被现实所改变;现实就像一个大染缸,每一个充满理想的人落在里面,几乎很少不经由幻灭、悲哀而逐渐变色、变质,染上大大小小、性质不一的污点。总之,身处现实中,“作人不容易”,第一步似乎就必须经历“人性的异化”(走向人性的反面,走向兽性或魔性)。于是,理想幻灭后的周朴园在痛苦的淬炼中蜕变了,他开始通过不断作恶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是经历过那种内心伤痛后,周朴园不惮于故意淹死2200个小工,通过克扣小工的抚恤金来攫取他的第一桶金;也正是经历过那次蜕变后,周朴园不惮于让警察直接向大群罢工者开枪,而且打死了人不给抚恤金。然而,作恶不但无法持久(总会不断遭人反对、反抗),而且始终令人恐惧不安。周朴园一度似乎“毫无顾忌,敢做坏事”,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忘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天命;因此他作恶于前,忏悔于后,用道德面孔把自己包装起来。但这样仍然不能逃脱天命的惩罚,毁灭性的打击还是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最后周朴园子亡妻疯,真个是落得“绝子绝孙”的结局。至此,周朴园所代表的人性发展路线走到了死胡同。反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可以说,这一人性发展路线是相当普遍的,至今仍有不少人在那上面走着。但其实,这一路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早在1933年曹禺就以艺术形式彻底否定了它。
曹禺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们,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在剧中,周朴园可谓是最精明的人物,但也正是他,不知不觉中做着断子绝孙的愚蠢事。他的悲剧性结局,不仅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挥之不去的“命运感”,更启示人们去思考: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种无形的秩序或制约人类命运的天人之道?人究竟怎样才能不做愚蠢事,从而超拔于“可怜的动物”之上呢?人类有可能永续发展吗?这种思考,会逐渐把学生带向作品的形而上学质,带向生态智慧的领悟,最终带向生态人格的建构。
当年巴金看了《雷雨》之后,他的感受就不是该剧暴露了什么罪恶,也不觉得该剧的故事“很混乱”,而是想到自己该怎么做人。在《怀念曹禺》一文中,巴金说:“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巴金确实是真正进入了《雷雨》的情境,真正读懂、读通了《雷雨》,并且领悟到了它的形而上学质;正是这种充分的感受与领悟,使得他真正敏感到该剧的终极关注,敏感到艺术家的灵魂之光,这样他才会与曹禺产生深深的共鸣——否弃周朴园所代表的人性发展路线,而寻求更能持续发展的、利人利己的人生道路。
这个从形式进入作品内质、人物内心与作家心灵的过程,就是“披文以入情,沿波而讨源”的过程,也就是“审美”的过程;而审美过程中的深层共鸣、感通,则可以说是一种发现珍宝、感受灵韵的过程。在巴金看来,曹禺是一个心灵中深藏很多宝贝的人;他那些宝贝,是他关于社会人生思考的结晶,是高级智慧的结晶。能否从作品中看到深处的光源,敏悟到其中深隐的高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美以及讲解的成败。以笔者的体会,这个过程讲解得越细致,带给学生的感悟越多,教学效果往往越好。在此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给学生一些理性认知的结论,而是让学生层层深入地进入戏剧情境,注意戏剧场面中那些感性的生活细节,由此逐步进入人物的内心,特别是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最后通观全剧,领悟其深层次的意味与灵韵。只要学生在这种由外而内的审美过程中能够“入情入心”、“动情动心”,那么他(她)的心灵就会逐渐受到感化,就会开始独立思考一些关乎自我、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如此一来,学生的精神就会逐渐成长,人格就会逐渐完善;如果青年学生的内在精神能朝此方向不断成长、完善,那么新的民族精神就有望形成。以审美代宗教,以艺术铸族魂,亦将未必为虚言。
如果说“艺术表现的和谐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不仅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一种最高的智慧,因而也是文化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关键。能够经常窥见艺术这种可持续发展过程的人,也就是窥见到宇宙中最高级的智慧和获得真正的和谐状态之机会的人”,那么,充分进入情境、直感戏剧本体、领悟其形上灵韵,正是窥见宇宙高级智慧、建构和谐生态人格、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准备,一种方式。我们的戏剧教学,任重而道远;如果改进理念与方法,确实还是大有可为的。
[1]谭霈生.戏剧本体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2]罗曼·英伽登.论文学作品[M].张振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3]巴金.巴金散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
[4]滕守尧.回归生态的艺术教育[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