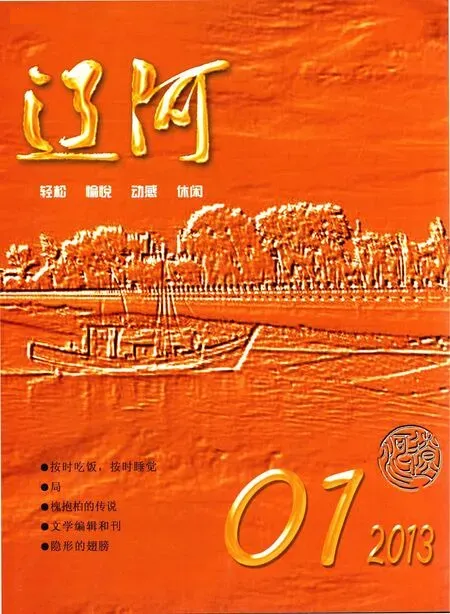帮助爷爷去天堂
河北/刘志波
带着爷爷的亲笔信,我去寻找一个叫仵龙堂的地方。
据爷爷说,仵龙堂在中国河北地界。按图索骥,我从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小村庄。查了一下行车路线,需从北京坐火车到沧州,再倒去盐山的汽车,过了东关镇,下站就是仵龙堂了。提起东关镇,我一点也不陌生,爷爷多次讲过,那是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当年东关镇马路边有个据点,里面住着一个叫小泉一郎的年轻人,就是我爷爷。爷爷说他来中国时可幸福了,鸡鸭鱼肉,柴米油盐,缺啥就去百姓家“拿”,像探囊取物一样简单。若生理上有想法了,提着枪到村里找个女人就把难题解决掉。爷爷说有次他们据点里抓来一汽车女人,个个水水灵灵,嫩得水葱似的,那一回,把爷爷尿眼子累得尿不出尿来。
当然,这一切都是爷爷过去常在众人面前显摆的。当年爷爷就爱说在中国那些事,好像那是爷爷一生的荣耀似的。那时我还小,常缠着爷爷讲故事。爷爷就讲他在中国的历史,说起来喋喋不休,像讲武侠小说。爷爷说他那年来中国只有十八岁,长得干瘪瘦小,还不够枪高。第一次看杀人,还尿了裤子。那次是抓了两个土八路,长官本意是拿这两个家伙让爷爷练手,就命令这两个八路跪下。一个八路乜长官一眼,高傲地昂着头,就是不跪。长官来气了,抽出马刀,刷地砍掉他一只手臂。那八路皱一下眉头,依然不跪,还啐了长官一脸唾沫。长官抹一下瘦脸,猛地吸溜一口气,便朝那八路的脖子抡圆了马刀。一股鲜血从断裂的脖颈处喷涌而出,溅了爷爷一身。爷爷吓得一屁股坐地上,裤裆立刻湿了一片。随即被长官一皮鞋从地上踢了起来。长官骂了爷爷一句,命他去杀另一个八路。爷爷提着刀,走近八路跟前,战战兢兢犹犹豫豫就是下不了手。长官上来又踢了爷爷一脚。无奈,爷爷就紧紧地闭上眼睛,一咬牙,也朝那八路的脖颈抡圆了马刀……
后来爷爷杀人就不眨眼了。
爷爷说这些时,那神气劲儿,就像刚刚御敌凯旋的勇士,从心底漾出一股豪气,衬着脸上的红晕,闪出熠熠的光泽。他并没觉出杀人是件多么可耻而又恐怖的事,对他来说,却像为民除害,助人为乐一样愉悦。可悲的是,我当时幼稚懵懂,不辨是非,竟把爷爷崇敬为英雄。爷爷那时还真就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家里不论来了什么客人,他都要把话题扯到中国去,顺便夸赞一番自己当年在中国的壮举。客人们也往往投其所好,顺坡下驴地说他了不起。听到夸奖,爷爷就更加得意,讲到动情处,眉飞色舞,嘴角上直冒白沫,像螃蟹吐得一样。
每次听爷爷讲,几乎都会听到他夸耀自己的枪法。爷爷说他打枪可百步穿杨,空中吊一枚铜钱,子弹能从钱眼儿里穿过去。我头次听了惊得差点把眼珠子瞪掉,好家伙,这么远的距离,算是子弹长了眼还有眨巴的时候呢,就不偏不歪地从钱眼儿穿过去,真是太神奇了。忙问他这么好的枪法是如何练的?爷爷摸摸下巴,笑眯眯说,这可是我独有绝技,功劳吗,当归那些中国人,若不是他们为我当靶子,我怎会练成神枪手呢。
爷爷说他的枪法都是在巡逻途中练就的。爷爷的东关据点和李家铺据点相距有二十多里路,一条石子铺就的公路,像条脐带将两个据点连在一起。为防八路骚扰,据点间每天都要沿公路巡逻。爷爷坐卡车上咣当当咣当当觉得无聊,就把枪架在车帮上练瞄准。瞄准的目标大都是路边地里耕作的农夫,有时手痒了,就勾搂一下扳机,子弹就闭着眼瞎飞,反正也打不中目标。开始,农夫们听到枪声,还惊恐地回头看,后来知道伤不着人,就闻而不惊了。练瞄准练了多久,爷爷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一次他冲着一个农夫勾动扳机后,那个农夫吧唧就栽倒地上。哇塞!爷爷很有成就感地立刻举起枪大声欢呼。汽车并未因他的呼叫而停下,依然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一个颠簸,差点将爷爷甩出车外。
后来,爷爷射击的命中率越来越高,他瞄向哪个农夫,子弹就乖乖地去亲近那个农夫。闹得公路边耕作的农夫们,见了日本巡逻车,赶紧趴地上,再不敢直身站立。
没想到,爷爷的射击,惹起了祸端。肯定是农夫们将这事状告给八路军。一天傍晚,当巡逻车从李家铺据点返回中途路过仵龙堂的时候,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枪声噼噼啪啪,爆豆似的,汽车被打爆胎,趴了窝。车上的人叽里呱啦跳下车,无处可逃,便钻进路边一间废弃的茅屋躲避。八路们穷追不舍,将茅屋围住,然后从汽车上倒来汽油泼茅屋上,点着了火。滚滚浓烟中,浮荡着鬼哭狼嚎的惨叫,几乎顷刻间,茅屋化为一堆焦土。屋内人无一幸免,被火神送上了天。幸亏那天爷爷因犯痔疮未去巡逻,才幸免于难。否则,后来也就不会再有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当然,更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日本宪兵此前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鸠山队长闻听此讯,勃然大怒,奶奶的,八格牙路,统统死了死了地!当夜亲自率领驻扎在盐山县城的宪兵队,倾巢出动;并调集东关、李家铺两据点里宪兵,合围仵龙堂。我爷爷那晚忍着屁眼儿疼痛,为了给死去的同胞报仇雪恨,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那次行动。爷爷说那天晚上没有星星,有轻柔的风,树上有猫头鹰咯咯咯地笑。悄悄将村子包围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能听到男人们轻微的鼾声。我爷爷他们将汽油轻轻地泼在每家房后的屋檐上。鸠山队长“烧”字的命令一下,我爷爷一马当先,点燃火烧仵龙堂的第一把火,抢了个头功。
当爷爷的火种触燃汽油的霎那,腾地一下,火舌漫过屋顶,在风的作用下,将火种播向每家每户。一时间,火烧连营,整个村子已是一片火海。火光映照着夜空,亮如白昼。一声声绝望的惨叫,浮荡在村子上空;空气中弥漫着股股焦尸的味道。从火中逃出的人们,赤臂裸膀,惶恐地奔向村外。听到嗒嗒嗒机关枪响,又掉头而返。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赤条条一丝不挂,怀抱一个物件,从火堆里钻出,正好和我爷爷撞个满怀。爷爷当时生理上没任何邪念,只想那女人怀里的物件肯定是个值钱的宝贝,上去就夺。女人抖着身子,抱得越发地紧。爷爷抢不过,抡起枪托,朝女人的脸捣去。火光映照下,女人的面孔立刻扭曲变了形,她踉跄一下,定定神,呸地一口,将满嘴的牙齿和鲜血兜头喷在爷爷脸上。鲜血染红了爷爷的眼睛。爷爷被激怒了。爷爷端起刺刀,向前一用力,扑哧一声,戳进了女人心窝。掰开女人手一看那宝贝,娘的,竟是个被火烧去一角的祖宗牌位。爷爷说他真弄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就这么傻,死到临头了,豁出命来保护的,竟是个分文不值上面写有祖宗名号的木牌牌。
上面的故事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爷爷讲给我听的,记得很清,我十三岁以后,爷爷再也没有给我讲过他过去的事情。这或许与我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的那次不幸有关。
那次事情发生的非常蹊跷,至今也没有谁弄明白那场灾难的起因。当时家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两个姑姑在木屋里睡午觉。之所以建木屋,是为了应对多发的地震,一旦垮塌,轻质的木板不致伤人过重。那天既没打雷,也没下雨,既没云彩,也没刮风,晴天丽日,一片祥和宁静。奇怪的是,这样的好天气,我们家的木屋无缘无故地着起火来。当人们发现时,火舌已吞噬了屋顶。木屋的燃烧,像燃放的炮仗,噼噼啪啪,势如破竹,眨眼间就烧落了架,将两个正熟睡的姑姑活活埋在里面。当爷爷发疯似地将姑姑从废墟中扒出来,已如两个烧焦的家雀儿。悲伤的爷爷只说了句“报应啊”,就再也没说话。
事后我判断,当时爷爷一定想起了仵龙堂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想起了那个被自己刺杀的怀抱祖宗牌位誓死捍卫祖宗的女人;想起了从火海中逃出沿街奔跑的人们;想两个姑姑要是像那些人一样能逃出火海就好了,哪怕有失体面地裸着身子。但,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能。
从此,爷爷沉默了,沉默得像块石头。姑姑的离去,给他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那可是他视若明珠的两个双胞胎宝贝啊,正值豆蔻年华,说没就没了,且没得不明不白,莫名其妙。这让曾经过杀人放火历练的爷爷一下子萎蔫了,魂魄好似游离了躯体,整日如霜打的茄子,蔫头耷拉耳的,什么也不想做。惟一想做的就是烧香拜佛,神明面前,长跪不起,嘴里叨叨咕咕,喃喃自语,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清。
爷爷变了,变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爷爷了。我想爷爷一定是中了什么邪,魔怔了。
直到我来北京留学,也从未再听爷爷讲过他当年在中国的只言片语。
放暑假了。我并未打算回日本,想利用假期在北京餐馆里打工,一来可挣些钱贴补生活,二来可加深了解民情民风,感受中国文化。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但父亲来电话说,你还是回来吧,你爷爷常念叨你,我看你爷爷状态不是太好。爷爷怎么个不好,父亲并没说,可我从父亲低沉暗哑的嗓音里能感受出些什么。
第二天,我就买了回日本的机票。
进了家门,我走向爷爷的房间。躺在床上的爷爷已无力坐起身子,见了我,只抬抬瘦如柴棒的胳膊,眼眸虽混浊不清,却依然掩不住喜悦的光芒。爷爷拉着我的手说,可把你盼回来了。盼你回来是想让你帮爷爷办件事。我立刻向爷爷保证,无论什么事,一定会帮爷爷办好。爷爷突然高兴的像个孩子,说,让你帮我去天堂。
我一时愣怔了,大惑不解:爷爷定是糊涂了,我怎么可以帮他去天堂呢?
父亲伸手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爷爷神经已经不正常了,他天天说些着三不着两的话。说他一闭眼,就有许多厉鬼绑他下地狱。还让人看他身上的绳痕。绳痕自然看不到,都知他这是臆想,但他还是说得有鼻子有眼。夜里动不动又喊又叫,声音怪怪的,吓人!
不曾想,父亲的话,晚上就得到应验。
夜里,正睡得香甜的我,被一声尖细的怪叫搅了美梦,那声音就像游荡的幽灵钻进我的耳朵,扣开了我涩重的眼帘。我立刻意识到什么,一骨碌爬起床,趿着鞋冲进爷爷房间。爷爷身子缩作一团,像只受惊的猫,浑身抖得如筛糠一般。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爷爷不停地自语。他一定是做了噩梦,蜡黄的脸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我俯下身,抚摸着爷爷,安慰着说,莫怕,莫怕,有我呢。爷爷见了我,如见了救星,一把抓住我,像沉溺水中的落难者,抓到一棵救命的草。说有你在就好了,他们又来绑我下地狱,我不去,我死也不去!我要去天堂!你帮帮我,一定帮帮我!
直到我启程回中国向爷爷道别,才知道爷爷要我帮他做的是什么。他颤抖着手,从枕下摸出一封信递给我,空洞的眼神里充满期待。他咳一声,清清嗓子,似乎想多说些什么,但已无力表白,只喃喃道,你到那个叫仵龙堂的村庄,帮爷爷把这封信烧掉……按理说,我该亲自去的,可我……爷爷没再说下去,喉结蠕动了一下,枯井似的眼眶里,涌出一滴老泪。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叫仵龙堂的村庄。
下得车来,已是夜色浓浓。天上没有星星,有轻柔的风,树上的猫头鹰咯咯咯地笑。村庄安谧地静卧在缁幕下,乖顺恬静得像个婴儿。村口散蹲着三三两两的人,他们在地上烧着纸钱。火光映照着他们凝重而悲伤的泪脸,有人发出嘤嘤抽泣。突然,一个汉子大喊,要勿忘国耻啊!铿锵之声,仿如隆隆滚雷,久久在耳畔回响。
我抬腕看了看手表上的日历:八月二十七日。这是爷爷让我赶到的日子,也是仵龙堂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吧。虽然爷爷没说,但我断定,就是几十年前的今天,爷爷的一把火,将这个村庄烧了个精光。
此时,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竟浮现出姑姑那烧焦的惨影,同时还有那位怀抱祖宗牌位、誓死捍卫祖宗的女人。心揪了一下,两腿无力地软下来。我跪在地上,拣块砖头,学中国人的样子在地上画个圈。然后,从怀里掏出爷爷的信。启封。我打着火机,借着光亮,见轻薄的纸上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是火烧仵龙堂屠杀中国人的侩子手小泉一郎,特向仁慈而宽厚的中国人谢罪来了!我对不起中国人,为在这里犯下的累累罪行深表忏悔!作为一个行将就木之人,我已无力做什么了,只愿死后能去天堂,为那些逝于我屠刀下的中国人效犬马之劳,以补偿曾给他们带来的苦痛之万一……
字是爷爷用中文写的,是怕天堂里的中国人看不懂日文吧?可见爷爷用心良苦。这一刻,我能感知爷爷当时写信时的复杂心情:是反思;是忏悔;是对过往历史的修正;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表白。我也真正理解了爷爷让我来的用意,同时,也为爷爷的真诚与释然而高兴。
信,化作一缕青烟,袅袅的,袅袅的,随气流飘向深邃的夜空。若有灵,爷爷定会感知得到吧。此时,我虔诚地伏下身,向着仵龙堂村,代表我爷爷,不,代表日本人,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这时,从烧纸的人堆里走来一位拿电筒的小伙子,晃动的光影,停留在我的脸上,许是看我陌生吧,他好奇地问,你祭奠的是哪位先人?
中国人!
我的回答令他讶异。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脸上的疑云才消散,扭曲了的面容也恢复原有的形态。电筒的光晕中,我能看清他犀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我的眼睛,然后他以一种近乎宣示的口吻,郑重地对我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绝不会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当然我们也不想延续仇恨,冤冤相报何时了,大度的中国人,会原谅每一个像你爷爷这样,给我们带来过灾难但真诚忏悔的人。”说着,他友好地向我伸出手。
一束电光划向夜空,黑黢黢的天宇,现出一道光明。
我的手机响起来,是父亲打来的越洋电话。一阵沉默后,他沉重地告诉我说,孩子,你爷爷走了,他去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