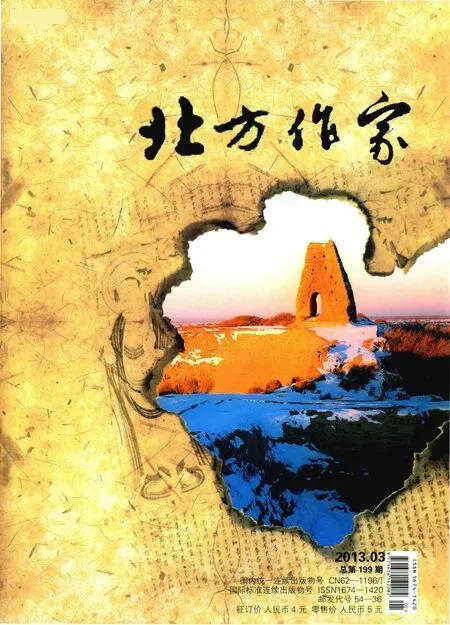敦煌有个高山(外一章)
甘肃敦煌 刘学智
敦煌有个高山(外一章)
甘肃敦煌 刘学智
记忆高山,话有些漫长。
我曾一直笑谈,敦煌这地盘被三股势力分割着。其一是本土敦煌,他们是土著,世代相衍,根须繁茂,虬根盘错繁衍大地的农业文明;其二是艺术敦煌,即敦煌研究院,固守莫高窟,甘肃省直辖,以莫高窟为生存对象,弘扬艺术文化;其三是寄居敦煌,七里镇一帮石油人,吸纳党河风雨,却是青海户籍,血液里鼓噪着工业文明。不大一块绿洲,十几万人相濡以沫,些许异别世界观或价值观,苟和谐且融融,演绎烟火人间,自是有些意思。
不知道敦煌研究院那帮艺术分子与敦煌土著交割深浅与否,按理说,他们在敦煌有近七八十年的历史,怎么说也有三代人的遗传史,是斩不断理还乱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的石油人大规模入迁敦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有二三十年以上的临时户籍。但我总觉得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固有着矛盾,工业文明是冷色的,农业文明是温情的。年少时节,我就两三次与敦煌的劣顽之子们展开过砖头巷战。在砖头瓦块的呼啸声中领略了“血雨腥风”,也自小就体会够了什么是“寄人篱下”。
我真正进入敦煌圈子还是在前几年。敦煌广播电台一个好写名人传记的记者骑着摩托车找到了我,说受北京某杂志之托写我一篇稿子。很奇怪,偏隅敦煌,我也居然被名人了。于是,礼貌地迎来送往几次,就再难以划清文明的种属了。这个圈子里有记者、诗人、画家、官员,有男也有女,有老也有少,都是些食得人间烟火的,喝得了酒,聊得了天,跳得了舞,也做得了梦。有如此一些人类共性,如今就是算得朋友了。
其中敦煌土著诗人健荣说起画家朋友高山,那语气是不一样的庄重。我知道健荣的个性,虽然在政府机关里办理了十几年案牍,但骨子里很诗人,向来很少这般。于是,我记忆住了“高山”这个名字。为此他还特别告诫我,“高山”者“高山”,非“高峰”也。但知原委,原来敦煌研究院高山、王峰、牛玉生三位画家,从生存条件绝对优越的研究院辞职下海做了自由画家,圈地创建了“三元画室”,开始职业画家生涯。特别高、王二人在敦煌画界屈指可点,于是有人盗“高山”之“高”为姓,盗“王峰”之“峰”为名,组合谓之“高峰”,混迹敦煌画市,窃取蒙生银两。这就是盗版的威力,由此我也不得不记住了“高峰”这斯。其实“高峰”乃研究院一沙弥,专司扫沙的一勤杂工,余话后表。
最初与高山的见面犹如遭遇春天那白色绵软的柳絮,一不小心就挂在眉梢。
偶一日,朋邀食聚,席间邂逅高、王二画家。那是最初的“三种文明”直接碰撞。农耕与工业,在艺术面前都显得笨拙、粗糙。两位艺术家中王峰固有一身江湖豪气,俗谚俚语,荤素搭配,淋漓昭然。高山则气骨仙灵,外秀内惠,超然于物,洒脱于世。我等鱼肉酒徒,泾渭分明。现在搜索最初的记忆,高山一则貌美,二则仙惠,三则禁荤。席间人人尊他“高老师”,且绝非貌似尊重。我想,我得叫他“高山先生”。高山言语简略近无,饮祁连雪水,食菜叶生疏,但不排斥别人尽情人间烟火,能聆听饮食男女的七情六欲。聆听,是美德,是宗教况味,是以净纳浊,以静制动,是至美。初次记忆不多,但感觉不错。后来也听说,高山在陌生人面前难有三句以上言辞的。
第二次相聚在青海省格尔木。高山带领他画室一帮女弟子,越野西藏高原写生,过格市小憩。到了石油的地盘我做主。我和油田一官员朋友在市里定下一硕大餐桌,够二十人围绕大快朵颐。高山驱越野车队绝尘杀将而至,长发滞尘。这是一次工业文明与艺术文明双向对撞。工业文明们都醉倒在幻化青稞老酒的禾苗、土地、阳光、收割和汗滴的自然诗篇里。高山禁荤之道“蛋白质,每日三粒黄豆足矣,多则浪费”。趁酒道自然,我简约问讯高山,比如他出家为道、东瀛求学等经历,略以印证。我笑谈“今生出家是我终极目标,只可惜时光累积,凡债沉重,不像你,先出世再入世,不需要华丽转身”。高山莞尔一笑。无语。我自觉混迹青藏高原多年,身上也挟裹了几分粗旷之气,但与高山那种仗剑走天涯,越野虚无境的智侠相比,汗颜。后来,我在高山的博客上也见证了屡次越野青藏的记录。其实,你很难将眼前的书生气、惠侠气的高山与一些“激越”之词搭配的。由此我想,高山是把“非常道”的精髓演绎得博大精深了。
之后一两载,我在柴达木盆地继续着“我为祖国献石油”,高山则在敦煌继续画室躬耕,彼此凡缘,点到为止,高山如仙气倏逝,相册尘封。但朋友健荣对筛选后的情谊执著近乎顽固。他常有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饮食活动或者文化活动。对敦煌文化和敦煌文化人他颇有针砭,曾当众人面铿锵一出书人“你今后就不要再出这样的工作手册了”,而他也有意无意顽固地再续我对高山的记忆。他觉得高山是敦煌画界难得的力量和榜样。而健荣也一再强调,高山道德至高,俗话人品好。我坚信健荣这般固执是有道理的,凡历经人间沧桑,魂语自是真理。我不得不一再打开那尘封的相册。
就在这个貌似春天的下午,我奉命拜见高山。“三元画室”已三迁,如今新画室在敦煌市去鸣沙山老路的一片梨园里。梨树棵棵年老苍劲,都带着智慧的气息和佛道的表情,绝对是心情修炼的佳境。高山也刚好把自己的画室命曰“菩提园”。敦煌市父母官计划在此打造敦煌画家村,想媲美北京、天津、深圳的画家村。这想法很改革开放。敦煌文化名片虽然大气,但市场决定生存,后况难以定论。在高山那设计独特类似莫高洞窟藻井的画室里,他说采访就不需要了,拍照也不需要,我请你们吃饭吧。我借用逆光给他拍摄了几张照片,他身后是巨大的落地玻窗,窗外是梨园里粗大梨树的枝杆,还有几枝写意画般的突兀伸拢的枝条,菩提之味自然自在。
在敦煌宾馆一个小包间里,我第一次领略高山那超然、惠美外表后滔滔言辞的力量,针砭时弊,观点锋利,思想闪电,洞开了我等混迹凡尘者已经死亡的窗户。我和健荣几乎无法言语对接。我在想,是我们真正已经死亡了还是早已习以为常?是,也许不是。或许,佛为什么一直是微笑着的就是因为他站立在凡尘之外、云团之上吧。期间,高山饶有兴趣提起当时敦煌画界发生的一件“博文事件”,一个隐身人发表了一篇《敦煌鄙人和弊画》的网络战斗檄文,其内容顾名思义不用累述。这篇揭露敦煌画界丑陋的文章顿时搅起画坛三尺浪,敦煌画家们的“人”“鬼”表情在博文的“顶文”里显露无遗。这是历史以来敦煌画家们朝自家园子投照无影灯,影子无处躲藏。高山平静一笑,叫我回去搜他博客,什么都有了。
我把自己关进办公室,第一次使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拜阅了高山的博客以及他诸多朋友的链接博客,并下载了他全部画作及个人影册,打理成包,收藏在活动硬盘。阅读,我理解了健荣的顽固坚持,也更加熟悉了高山。
高山,一九六二年生于甘肃兰州。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之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院工作。一九八八年出家为道,系道教全真龙门派二十四代传人,法名诚林,号“了然子”。在榆林窟、莫高窟临摹壁画,并创作油画,先后在中国香港、日本、美国举办个人画展,并在东京艺术大学进修三年。一九九六年回国任段文杰院长秘书。二000年后辞职创办“三元画室”,开始职业画家生涯。其作品宗教况味浓厚,画风飘逸洒脱,是目前敦煌画坛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有很多记叙高山的美文,也有很多析剖他画作的评论,都很好,有深度,有高度,有美感,我不再貂尾续狗。高山他自己对艺术的思考很有些意思,他在一篇《用易经算艺术》博文里曾这样彷徨而又清醒地说:这几年来因为画画成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所以越来越贴近了社会,贴近了现实。而那个很久以来的崇高追求——伟大的艺术,也随着这种贴近越来越看不见了目标。于是我忍不住又起了一卦。结论是:我将成为残余势力被遗弃。后三百年是审丑时代。谁要是能提前画出三百年后的审美的画来,他就是下一个传统的祖师爷。
对绘画我不专业,虽然年少时也曾心倾之,这不是我记叙的主题。我得记叙高山先生两件事。一是他父亲。对于他的绘画及艺术追求,我认为他父亲即著名诗人高平老先生很关切,经常可以见到在高山博文出来后,高平老先生是第一个阅读者和评论者。对于“风格”一篇博文,老先生就如此点评“人格就是艺术创作的风格。人格已经固定,风格自然呈现。人格越是超然,风格越显高雅。人格越是奇特,风格随之怪异。人格如果庸俗,风格岂能出众”。“宁为美尾,不为丑头”。而且,我在高山新画室见到高平老先生的亲笔勉词“戒才多忽略识寡,忌好善不能择人”。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浓浓的情感和艺术要求。我曾在敦煌一次文化活动上见到他们父子这么一幕相见图:高山带着羞涩和儿子的本分前与远道兰州而来的父亲打招呼,老先生那诗人犀利的目光猛然遭遇了牧羊女鞭子轻轻抽打一样温绵。这是父子两代人互为尊敬的表情。我为那一幕时时暖却自己的记忆。由此也记得顾城死后顾工的一篇回忆文章,他总感觉孩子随时会用那把旧钥匙敲着小巷里那厚厚的墙,然后用钥匙找到家门的锁孔,通篇没有一个责怪的词语,那也是我对那父子两代人互为尊敬的至高记忆。
二是高山的宗教感。他有过厌世、出世,再入世的比较复杂的思想斗争轨迹,这是思想者正常的行走轨迹。可以说,是宗教意识奠定了高山的人品和画风。他入教的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道教不极端也不排他,宽容,包容。道教讲一个字“悟”,参悟,超然,无为而为。道教还讲究一个字“净”。把凡尘思绪洗濯干净,独守清静,静虚。而高山的超然宁静既在生活中,也在他的画作里淋漓展现。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他的那幅“大戈壁”的油画,或许也可以叫“黑戈壁”,我在他第二代、第三代画室里都领略过其神韵,那是宁静、宗教的至高表现。猛然见画,抽思固体,有令人遁世之感。但在高山看来依然“表实感真情总无限,画良辰美景亦无常”。或者借用高山的诗来讲就是“西山影暗夜将来,凡心欲灭道心开。遥看四极尽空旷,霞光月色共徘徊。”那是静虚大境界。
经验永远是个人独有的,无法被借用,也无法被分享。在敦煌,高山是为幸。正如高山所言“当我完成绘画技法和表现形式后,我要朝思想的领地出发了”。
敦煌这座城
敦煌人不习惯久居城中,因而保存下来的城是没有的,甚至连完整的城墙都没有。明代的敦煌城是蒙古人修筑的。蒙古人无修筑居所的习惯,勉强修了,只知道遂水而居,不想被党河无情冲刷,而今只剩下—个旧城墩,连着几节矮城墙,叫它:“敦煌故城”也实属勉强。我曾在散文《旧城墩》里写到过它:“多少次了,我都要去看这古老的墩子。墩子的石碑上刻着‘敦煌故城’四个大字。除此之外,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曾耸立着明朝经营西域的重镇——沙州卫的卫所,它曾是流离失所的蒙古人暂以憩身的家园,也是古丝绸之路由盛入衰的历史见证。”清朝的也修过城,修得气象森然,“云峦叠翠层楼外,城廓烟环四望中”。修好之后确也繁荣了地方经齐并将城的观念扩大并渗透到了乡村。现在人们说的进城去,其实就是去进这座清代的城。而现实的城又在什么地方呢?完整的城墙又在哪里呢?和邻近的地区相比,敦煌闭塞而开放,破四旧”时人们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干劲十足,几日内就又将城墙搬得干净,最后连市中心的鼓楼也难以幸免。
现在的城市越修越像一堆水泥,敦煌城也有这种发展趋势。楼房空间狭小不说,连孩子玩的草坪、花坛都没有。你就别指望搞什么城市绿化了。孩子们不知道历史是可以谅解的,可他们竟然把现在唯存的清朝敦煌城的惟一一段城墙叫做“高台子,并且可以在墙下撒尿、泼污水,在墙上刻同伴的大人名讳等。清代的敦煌城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堆坚硬的黄土,就像历史上的一块砖,恰如其分地继承下来,又被抛弃到城市的某个角落。这就是历史上敦煌城的缩影。
对于过去,我们已无话可说,而现在的敦煌城,发展更快,越过党河向西发展,有与青海石油城相接之势。但人们仍把河东岸的地方称为城。住在城西的人也常说“进城去”的话。前些年,乡里的女子恋爱是非逛城不可的,说不到河东的城里走一趟,就要寻死觅活,河东的旧城是占尽了地气,敦煌城是不是正应了那句“紫气东来向西去”的古话呢?
城的概念已在敦煌人的头脑中形成,可大可小,全随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想象的城门里进进出出,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
这样的城造就的人也不—样,男子平平常常,女子却个个生得俊美。早些年,日本男子多到敦煌寻根,不少都以敦煌女子为妻。这在别的地方,容忍须有个过程,但在敦煌就行。说是百年的城墙都会倒,这算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