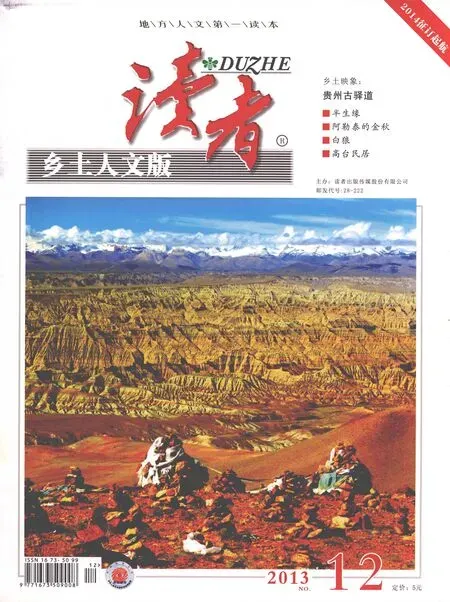饥荒年代的尊严
文/梁文道
饥荒年代的尊严
文/梁文道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里一个叫高吉义的人,有一天和八个伙伴偷到一袋重达一百六十斤的洋芋。几个人饿得太久,什么后果都不顾了,将一袋洋芋煮掉吃光。
这是超出人类身体极限的荒谬举动,更何况饿久的饥民。可是,长期的饥饿让人放下了生理的本能,一直吃,最后变成了心理上的渴欲。
果然,他们九人吃到了腹痛难当的地步,坐在车上稍一晃动,喉底就会掉出一块还没嚼好、更没消化的洋芋。
当天晚上,其中一人终于撑破了胃,不到午夜就断气了。高吉义则倒在炕上翻来覆去,又哭又喊,吐也吐不出,拉也拉不出。好在有一个一直很照顾他的“老右派”牛天德,整夜伺候他,帮他揉肚皮。揉着揉着,高吉义果然吐了,而且上吐下泻。牛天德是工程师,斯文儒雅,这时却用一个盆帮他接上所有的秽物,吐一回倒一回,拉一回倒一回,整晚出出入入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高吉义醒了过来,出门走动,舒活手脚,发现有人架了一副梯子上了房顶,就好奇地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牛天德,他趴在房顶,用一块布晾晒着一层黏稠的东西。
“黏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疙瘩物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显绿色的混合色。”再走近一点,高吉义发现,牛天德“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黏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黏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这是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里写的骇人“大餐”。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回母亲的河北老家,问亲人们是怎么挨过那三年“困难时期”的,他们都吃过树皮吗?
二爷爷与大舅舅都点头,表情淡然,话也不多,只是说:“连草地都给啃成荒滩了,树皮又怎能不吃呢?那时候如果有一碗白面,就已经活得比神仙还好了。”他们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往事已远,不必再提。
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吃草与树皮意味着什么。你肚子是填饱了,却没有营养,所以你会浑身乏力,坐下去就怕站不起来。当年有许多人都试过站着拉屎,任由排泄物沿着裤管流到地上,因为蹲下去的后果可能是再也起不来。假如是在荒郊,瘫坐到晚上会有被狼吃掉的危险。说到拉屎,大多数人肚中没有油水,老吃那些纤维过多的东西就会造成腹胀,肚子里一团团草蛋拉不出来,最后能把人活活胀死,嘴缝溢出一丝黑血。于是大家就自制一种很像耳掏的木勺,互相从对方的肛门里掏挖粪团,常常弄得人痛苦难当,血污四处。
直到二爷爷去世,我没再和他聊起那三年的事。因为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永远不要去问一个挨过灾荒的人是如何熬过来的,人总该保住他最后的一点尊严。
(吴一冉摘自群言出版社《味道之人民公社》一书)
(张甫卿摘自吾喜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