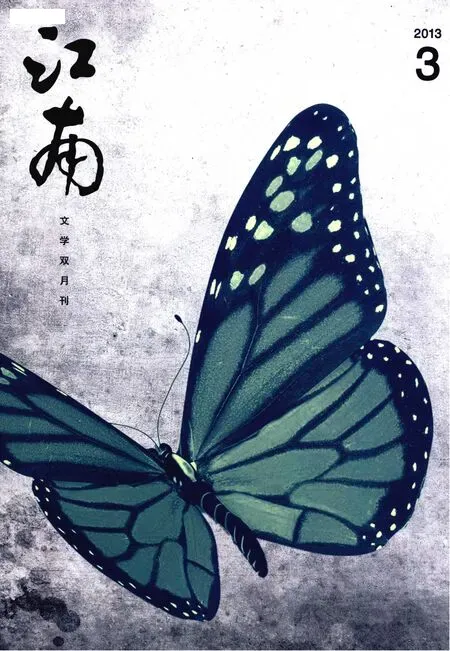革命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对峙与碰撞——评胡发云长篇小说《迷冬》
王春林
阅读《迷冬》,首要一个问题,就是胡发云究竟采取怎样一种形式从怎样一个节点切入对于“文革”那段历史的艺术表现。这一方面,一个很大的观念误区,就是只有对于“文革”苦难一种血淋淋的真切展示,方才算得上是对于“文革”的一种直面表现。倘若从这种观念出发去构建胡发云这部关注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那么,小说的主人公似乎就应该是其中的羊子或者梁宁凯。道理非常简单,与多多、夏小布他们相比较,他们两位更深更直接地介入到了“文革”的矛盾争斗之中。以他们为主人公,显然有利于对“文革”苦难程度的直击渲染。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关乎人性、关乎人类精神的艺术。因此,尽管我们强调作家们在“文革”的苦难面前不能够背过脸去,应该直面“文革”的苦难,但也得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所真正比拼的,并不是对于苦难渲染到怎样一种血淋淋的程度,而是这种苦难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人性世界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点,胡发云的《迷冬》就做得相当好。比如,既然要书写“文革”,武斗就肯定是无法回避的一种社会事实,但胡发云却并没有过多地渲染表现那种尸横遍地的惨酷场景,他更注重于通过主人公多多的主观精神感受来书写武斗的极端负面影响。“从上午一见到那阵势开始,多多就进入一种虚脱的状态,外表看起来没事人一样,但内里的五脏六腑肌肉筋骨都在颤动,像打摆子。见到火,见到血,直至最后见到了尸体,他觉得自己也差不多了,一身虚汗,轻飘飘羽毛一样,恶心,想吐,不管是奔跑还是走动,都像鬼影一般没有了重量。”相对于羊子、梁宁凯他们对于武斗的直接介入,多多只是一位旁观者的位置。从一个精神异常敏感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表现武斗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强烈刺激,较之于直接描写渲染武斗的惨烈场景,不仅切入了人性世界,而且也明显地更加具有艺术性。
很显然,胡发云的《迷冬》并没有采用那种正面展示苦难的艺术表现方式,他实际上是从一种个人记忆的方式切入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与表现的。虽然对于胡发云的个人经历不太了解,但依据我阅读小说的感觉来判断,其中男主人公多多身上,明显存有胡发云自己某种“文革”经历的投影。而这,显然也就意味着胡发云在《迷冬》的书写过程中,充分地调动了个人的“文革”生存经验。从个人记忆的角度来说,《迷冬》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成长小说。对于“文革”开始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的多多而言,他所经历着的这个“文革”进程,实际上也正是自己由初通人事到最后终于成熟起来的一个关键过程。尽管从本质上说,《迷冬》的确是一部旨在关注反思“文革”浩劫历史的社会世情小说,但这却并不妨碍胡发云借助于一种成长小说的模式来架构整部长篇小说。又或者,由于成长小说框架的运用,由于对于自己一种真切“文革”生存经验的充分调动,胡发云《迷冬》之对于“文革”的书写,方才拥有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感,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说到成长小说,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迷冬》中处于文本核心地位的成长者,实际上并不只是多多一人。多多之外,作为女主人公形象出现的他的恋人夏小布,也如同多多一样,正处于成长的关键阶段。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胡发云的《迷冬》通过一种成长小说的框架切入到了“文革”历史的深层,关键还在于牵涉到了一个小说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文革”属于一个涉及到了总体中国人的重大公共历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发云的《迷冬》自然也就少不了公共性的一面。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注重于公共性的传达,那么,小说文本就很可能变得空洞乏味。很大程度上,只有实现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完美融合,方才可能有效避免此种空洞乏味情形的出现。在我看来,胡发云这样一种充分彰显个人历史记忆的成长小说架构,恰如其分地弥补了那样一种公共性的缺陷,很好地实现了个人性与公共性的艺术对接。
必须注意到,多多与夏小布这两位处于成长过程中的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能够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既介入又疏离于“文革”这一历史现场,从根本上说,端赖于胡发云关于那个名叫“独立寒秋”的文艺宣传队的特别的设定。具体来说,在《迷冬》中,胡发云所集中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并不处于时代中心地带的音乐团体。通过对于实际上处于时代边缘位置的一个文艺宣传队的描写而切入那个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胡发云一种艺术构思上的别具匠心与别出心裁。关键还在于,这个“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的人员身份构成是非常特别的。在“文革”那样一个血统论笼罩一切特别盛行的时代,“独立寒秋”却非常勇敢地打破了血统论思想的禁忌,在招生广告中大张旗鼓地强调:“我们热情欢迎那些虽然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是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战友们。”有了这样一个主张,自然就会招来很多“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正如秦珊珊所感觉到的那样:“数月来,‘狗崽子’、‘王八蛋’、‘孝子贤孙’、‘美女蛇’一类最恶毒的咒语,已经让她变得失去了羞耻感,如今却有人预先就将‘战友’的称呼留给她。”之所以会有如此一种特别的感觉形成,是因为秦珊珊因为家庭出身曾经遭受过简直无法承受的凌辱。尤其让秦珊珊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对秦珊珊施加凌辱者,都是她平时特别亲热的好朋友。这里,借助于秦珊珊这个个案的不堪遭遇,胡发云一方面写出了“文革”惨无人道的状况,另一方面却也凸显出“独立寒秋”所拥有的一种独特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为,为如同秦珊珊这样的“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提供了一个能够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奇特避难所。
应该看到,除了一些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者之外,这个文艺宣传队中包括多多与夏小布(尽管夏小布的身份后来曾经数度改变)在内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当时被打入另册的年轻人。就以上这样一种艺术处理方式来说,胡发云的这部小说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那部曾经产生过极大影响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由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所真实再现的,是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11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某种意义上,由羊子与多多、夏小布他们策划创办的这个“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极其类似于奥斯卡·辛德勒创办的那个旨在收容保护犹太人的搪瓷厂。当然,《迷冬》中的这个“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与奥斯卡·辛德勒的搪瓷厂之间,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倘若说《辛德勒的名单》的奥斯卡·辛德勒是以一种他者的身份对处于极端困境中的犹太人施以援手的话,那么,《迷冬》中的“独立寒秋”就属于一种自我拯救,是这些被当时的“革命”打入另册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子女们的一种自救行为。但是,从一种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多多夏小布他们的“独立寒秋”也罢,奥斯卡·辛德勒的搪瓷厂也罢,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圣经》那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很显然,胡发云之所以要以如此一种方式思考表现“文革”,就是要在充分展示“文革”苦难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历史救赎与精神救赎的可能。说到这里,一个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文艺宣传队究竟为什么会被命名为“独立寒秋”?一方面,这样一个来自于毛泽东诗词名句的名称,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必然产物。在当时,许多群众组织都用毛泽东的诗词为自己起名。但在另一方面,出自于多多的如此一种命名行为,显然也还寄托着胡发云另一种深刻的象征内涵。假若把那个惨酷的“文革”时代理解为“寒秋”的话,那么,“独立寒秋”这个名称显然也就具有了一种独立于“文革”时代之外的强烈感觉。正如同多多既在时代现场之中但却又总是游离于“文革”之外一样,这个诺亚方舟式的“独立寒秋”组织,与“文革”所保持的实际上也就是如此一种既在场而又有所游离的关系,保持了某种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品格。
说到“独立寒秋”这个组织,其引人注目处,除了勇于打破“血统论”理念,大量吸收家庭出身存在问题的所谓“非劳动人民”子女之外,另外一个不容忽略处,在于这是一个文艺宣传队,是一个音乐的社会组织。阅读胡发云的这部《迷冬》,关键词除了“文革”之外,就应该是音乐了。对于一种特定时代境遇下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的描写展示,或者也可以说,对于一种殊为迷人的音乐世界极具魅力的形象呈现,乃是《迷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构成部分。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除了自己有着一种强烈的音乐兴趣之外,胡发云为什么非得把“独立寒秋”设定为一个音乐表演团体?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多多没想到宫克对音乐也有如此深厚的修养,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音乐是保存这个世界真善美的最后一块园地,因为它的语言有它自身的逻辑。像你们演的那首《沁园春·长沙》,虽然说歌词在说谁主沉浮,浪遏飞舟,但是旋律在说悲怆和忧伤,不管作曲的是否承认,但是音乐说出了他心底真实的东西。好派也会完蛋,屁派也会完蛋,我们这些人也会完蛋,但是,好的音乐,好的文学艺术,还会流传下去,就像我们今天还记得诗经、楚辞,谁还记得两千多年前那些个王侯将相呢?便是记得一点,也是从司马迁的《史记》里读来的……”某种意义上,这段话语,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作家胡发云自己的一种夫子自道。我以为,胡发云借助于宫克的口吻,实际上给出的,正是他自己之所以要在这部《迷冬》中对于音乐大写特写的根本原因所在。
某种意义上,音乐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存在形式。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宫克所谓“音乐是保存这个世界真善美的最后一块园地”的论断。非常明显,《迷冬》中的“独立寒秋”这样一个以音乐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守护或者说体现人性的堡垒。与“独立寒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所集中审视表现的以灭绝人性为突出特征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关于“文革”所具灭绝人性的特质,胡发云在《迷冬》中有着非常充分的描写展示。“这场无需冒险与牺牲,无需苦难与流血,既没有彷徨与痛苦,也没有离别和忧伤,只需要等级和出身、粗暴和野蛮、狂热与冷酷的革命,让他渐渐成为一个反革命者。他痛苦地抵牾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连同它催生的那些语言、图画、音乐、舞蹈……都让他厌恶至极。”借助于多多的角度,胡发云在这里所尖锐揭示的“等级和出身、粗暴和野蛮、狂热与冷酷”,正是“文革”的一种真实本质。具体来说,无论是武斗的惨酷景象(我们应该注意到胡发云对于武斗的一种理性界定:“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1949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日常生活中本来可以和谐相处的国人之间,仅仅因为一些政治理念上的差异而大打出手,而付出巨大惨烈的生命代价,自然只能够被看做是对于人性的一种灭绝行为),还是那些因为自身的问题(典型如多多的父亲,如林老师)或者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典型如秦珊珊,如黄为仪,如曾经一度的夏小布)而遭受的种种非人折磨,抑或是对于正常人性的强制性扭曲(典型如夏小布的母亲,夏小布的母亲之所以要揭发她父亲的所谓作风问题,显然是受到时代风气一种扭曲性影响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独立寒秋”这个音乐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比如被迫集体加入湖城师院红司,比如被迫远走新疆),以上所有这些,凸显出的都是“文革”的非人本质。与“文革”的惨无人道酷烈无比形成鲜明对照的,除了打破血统论观念大量收留那些“非劳动人民”子女之外,还有音乐所具备的一种人性本质。“她们用自己的某种体验,让这样一首红色儿歌生出了一种能够揉碎人心的痛楚。那天,多多将一段慢板处理得极微弱极缓慢,似乎生命的血液正在一滴滴凝固成火红的冰珠,两个对生活还充满梦想与渴望的小姑娘相互间给予着对方最后一丝丝温暖,她们用这种柔弱的方式反抗着厄运的到来。”在这里,胡发云用充满诗意的文字所写出的,实际上正是音乐本身具有着的那样一种呵护人性的美好品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所体现着的,是一种灭绝人性的革命伦理,而音乐的本质,则是一种呵护人性的生命伦理。本文标题所谓革命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对峙与碰撞,其具体所指,正是“文革”与音乐之间的一种尖锐对立本质。
对于一系列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是胡发云《迷冬》思想艺术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秦珊珊、羊子、黄为仪、宫克、舅舅、陶叶屏、舒叶、舒惠、苏导演、沈婕、葛木生、梁宁凯、李北、何其亮、傅海、钱氏兄弟等等,都令读者过目难忘。当然,胡发云在《迷冬》中刻画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还是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多多与夏小布。返归到“文革”的历史现场,夏小布应该被划入“红五类”的行列之中。问题在于,夏小布尽管身为“红五类”,但她的父亲却因为妻子的“揭发”而在“文革”初期被打入了另册:“罪名一大堆,黑帮,叛徒,三反分子,资产阶级代理人。”明明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资格很老,级别很高”,却在突然之间被当做了革命的对象。如此一种严重的误解,对于夏小布的父亲可谓致命一击。无法理解接受这一切的夏父,终于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关键在于,父亲的被打入另册以及最后的自杀,对于拥有强烈自尊心的夏小布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假若不是在那艘登陆舰上意外地邂逅了自己的恋人多多,夏小布早就以自杀的方式步父亲的后尘了。“夏小布望着他,似乎又穿透了他望着后面的什么地方,那眼神有些怕人,瞳孔放大,灰暗,空空的,像已经死去一样。”这样的文字,极其传神地描摹传达出了夏小布那样一种绝望至极的心理状态。但是,相比较而言,《迷冬》中关于夏小布精神世界更加值得注意的描写,却表现为她在一种反常心态下对于林老师的主动“揭发”。夏小布的“揭发”让多多大吃一惊:“多多几乎不相信这些话是夏小布说的,他回头望了夏小布一眼,是的,还是那个人,那个与自己相处甚深的人,私下里给自己唱过《外国名歌200首》中的许多歌曲的人,他曾经从她的声音与眼神中看到过陶醉与激情。她也亲口对他说过,这是一些不朽的歌。”必须注意到,歌曲或者说音乐在这部《迷冬》中的强烈象征意味。这段叙事话语中,叙述者之所以强调夏小布曾经唱过许多外国名歌,并且强调这些名歌都是一些不朽的歌,其实就是在强调夏小布曾经拥有过美好的人性,是一位单纯善良的女孩子。这样一位女孩子突然变脸,转而大肆“揭发”自己的老师,“揭发”作为恋人、作为精神同道存在的多多自己,当然就让多多大惑不解了。那么,夏小布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呢?只有在登陆舰上再度邂逅之后,夏小布才向多多揭开了真正的谜底所在:“夏小布说,那些天,是我父亲处境最危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那样反常过……”非常明显,正是因为父亲的遭遇对于夏小布形成了强烈刺激,所以夏小布才一度陷入了一种精神严重变形的状态之中。而且,这里也还隐隐约约地存在着一种夏小布的自保心态:“多多似乎明白了夏小布在以攻为守,她怕被人洞悉他俩的某种暧昧关系。”实际上,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胡发云才强有力地写出了夏小布的某种精神深度。
与夏小布相比较,《迷冬》中最不容忽略的一位人物形象,就是多多。在对多多的精神世界展开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就小说的叙事过程而言,多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视点作用。尽管从总体上说,胡发云在《迷冬》中采用了一种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但这种全知叙事方式却更多的是依赖于视点性人物多多的观察眼光才得以完成的。而且,正如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多多是位居《迷冬》文本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小说的那样一种“迷冬”主题,乃是依托于多多的存在才得以相对完满地传达出来的。“多多读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并不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间,他当然没有了自作多情的豪迈和激越,只有许多的失落和怅惘。紧接下来的那些日子,他内心深处又生出许多痛苦、孤傲、厌恶与恐惧。”从这段叙事话语中,即可明确判断出,所谓“迷冬”云云,其实指的正是一种生命的迷惘、迷失状态。对于当时还只是一个年轻中学生的多多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带有鲜明粗暴与野蛮性质的“文革”怪兽,绝对是无法理解的,非常明显地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既然无法理解,那么,一种精神的生命的迷惘,就是必然的事情。胡发云之所以要把自己这部透视反思“文革”的小说不仅命名为“迷冬”,而且还特别设定为一种成长小说的妙处,到这里方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根本上说,多多是一位游离于时代之外的边缘人形象。这一点,似乎是他的天性,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多多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毛病,从幼儿园起,他就不喜欢做群体性动作……此后,所有群体性节目,阿姨就像没他这个人一样,他也像没有那些节目一样,自己在一个角落里专心专意地玩自己的。”既然是如此一位置身于时代思潮之外的边缘人,那么,出现在叙述者话语中的多多,就一定是这样一种形象了:“他的脸色苍白,神情忧郁,与周边环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外形上的不合时宜,更加关键的是,多多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也同样充满着危险性。所谓多多与“文革”的疏离,所谓多多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毛泽东诗词的理解上:“其实,最要命的是多多自己的问题,那就是他对伟大领袖的腹诽。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这是一个掉脑袋的问题。”正如同叙述者已经明确指出的,如同多多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诗词的腹诽,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掉脑袋的事情。尽管叙述者强调多多不懂政治,唯其不懂政治,他才会产生以上这些大逆不道的思想。问题在于,一旦形成了这些大逆不道的思想,多多想远离政治都不可能了。实际上,在“文革”那样一个政治席卷笼罩一切的时代,任是谁恐怕都无法真正地远离政治。即使你想离政治远一点,政治终究也会自己来找上你。
然而,尽管说作为边缘人的多多看起来似乎比其他同伴稍微清醒一些,但从根本上说,多多也还是无法摆脱时代政治的影响。胡发云《迷冬》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对于多多这个自传性形象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种不无严酷的批判性描写。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林老师自杀之后多多的一种自我追问:“事后,多多常常不无后怕地想,当时要是没有那个英语老师的跳楼,自己怕是扛不过去了。他不害怕孤立,也不太在乎批判,他害怕凌辱,怕剪头发怕抹大花脸,更害怕挨打,那个张小平的铜头皮带,比所有的批判都让他恐惧。这样的时候,你连充当个舌战群儒的英雄都不可得。自己会说些什么,是竹筒倒豆子甚至添油加醋,还是顾左右而言他避重就轻?不管是哪一种,他都会觉得林老师之死与自己有关。但是,侥幸逃脱了对林老师刺出最后一刀,自己就清白无辜了吗?自己对林老师的厌恶与冷漠,难道不也是那风刀雨剑中的一部分?”“多多知道,那位英语老师和林老师的死,免却了自己一次最大的耻辱。他对他们的死,一直充满了负罪感。”必须意识到胡发云这种描写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多多这一人物的精神深度,正是依赖于这种批判性描写,才获得了一种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多多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自传性色彩。在中国这样一种向来匮乏罪感意识和自我忏悔精神的文化传统的笼罩之下,胡发云能够通过多多这一人物形象,对于作家自我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一种特别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迷冬》之所以能够相对完美地传达出革命伦理与生命伦理对峙与碰撞的精神内涵,与胡发云对于小说结构的精心设定存在着紧密联系。依照我的理解,《迷冬》中存在着三条结构线索。第一条就是“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的成立以及成立之后的整体发展过程。这条线索很显然是小说的结构主线。第二条是男女主人公多多与夏小布之间的爱情线索。第三条,则是与“独立寒秋”的那些年轻人有着种种血缘关系的成人世界的故事。这其中,多多的父母、舅舅以及与舅舅有着感情纠葛的陶叶屏、苏导演,宫小华的父亲宫克,钱氏兄弟的母亲钱妈妈等一些成人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较为难忘的印象。当然,这三条结构线索,尤其是前两条线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渐次向前推进发展的。三条结构线索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胡发云对于叙事段落的一种节奏处理。具体来说,整部小说除了最后一节“不是尾声”之外,一共由120节组成。根据故事的发展状况,这全部的120节又可以被切割为五个部分。其中,第1节到第5节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讲述多多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的大串联情形;第6节到第17节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的故事由多多一个人而扩展为多多和夏小布两个人,主要发生在那艘从上海航行五天五夜之后抵达故事主要发生地湖城的登陆舰上;第18节到第44节是第三部分,故事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讲述“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的酝酿及成立过程;第45节到第98节是第四部分,主要讲述“独立寒秋”成立后的演出情况,一直到被迫远走新疆为止;第99节到第120节是第五部分,主要讲述“独立寒秋”远赴新疆以及抵达新疆之后的故事。从第一部分到第五部分,不仅描写范围渐次扩大,而且人物与“独立寒秋”的命运也越来越坎坷曲折。尤其不容忽略的是,作为一部以音乐为主体的小说,这五个部分的发展变化非常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多声部合奏的交响乐。
与很多严格回到历史现场描写表现“文革”的作品不同,在《迷冬》中,胡发云采用了一种现在返顾式的写作方式。所谓现在返顾式,就是说作家是站在许多年之后的现在的视角上运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完成小说叙述的。在我看来,胡发云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回望历史的方式,其根本意图在于,可以在一种历史的巨大反差中为读者理解认识“文革”的本质提供充分的可能性。有了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纵深透视,那样一种诡异历史命运的沧桑感,自然也就能够较为完美地传达出来。比如:“只是这一派驻也够长的,一直到十二年之后的1978年,小姨夫妇平反获释,这姐妹俩才重新相聚……此时,小姨夫妇已在漫长的监禁中变得拘谨又木讷,似乎还没有习惯自由的生活,眼里总有一种慌乱卑怯的神色闪过。”在小姨夫妇精神世界被扭曲的状况中,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命运的一种乖谬无情。再比如:“整整十年之后,当多多在一次全市批斗大会上,看见苍老又猥琐的张林站在台上作为‘四人帮’在湖城的骨干分子被控诉被批判的时候,怅惘不已,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幕,有一种深深的荒谬感。不知是一个时代的荒谬,还是一个人的荒谬,感到命运弄人。”确实是所谓的造化弄人,张林这个曾经在湖城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目的人生浮沉,端的是只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命运的乖谬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