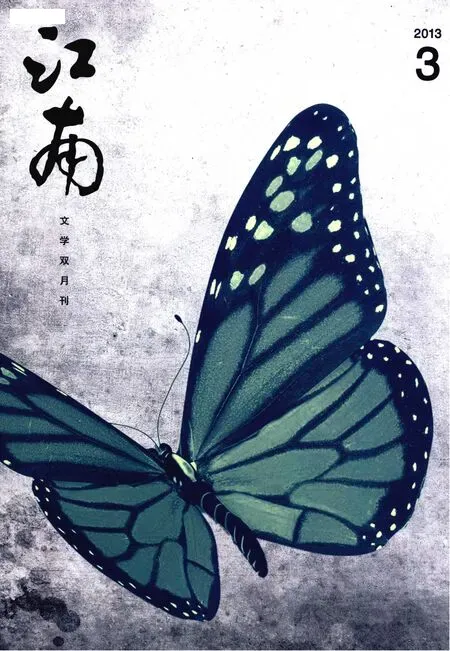虚静恬淡子如水
沙 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语今注今译》,注释者毛子水先生。许是料想我对毛先生一无所知,所以朋友用极为恭敬的语气将他为我做了一番介绍,称他是“研究《论语》第一人”,在台湾学术界被尊称为“通人”“通儒”。何以称“通”?朋友解释说,这是在研究科学的人中,毛先生的国学根基最好;而在研究国学的人中,毛先生的科学根基最深;他的读书之多,甚至他的老师胡适也称赞他是“东南图书馆”……
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年,当年的小伙子成了如今的老头子。但也是有缘,那日与衢州作家柴薪闲聊,柴薪不无炫耀地说起他的故乡江山,说江山石门镇的清漾村,是江南毛氏的聚居地,村子虽小,却人才辈出,历代出过8位尚书,83位进士;清漾毛氏的著作,有五部十七卷被收入《永乐大典》,六部二十七卷被收入《四库全书》;而最近的一位,是早年去了台湾、被称之为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又说,凡是清漾要出人才,毛氏祖宅前的池塘就会冒起香泉,毛子水出生时,馥郁奇异的香气,据说足足弥漫了三天……
听了柴薪这番话,我便怂恿他从故乡的角度,写一篇介绍毛先生的文章;所以如此,并不是他这带有传奇色彩的述说,倒是基于我对毛先生的钦佩。因为我觉得,毛先生是一个真正“读书破万卷”的人,他的读书的目的、读书的取向和读书的理念,都足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而当下,热衷上网的人越来越多,潜心钻研者则日见稀疏;低劣的网络语言更是甚嚣尘上:什么“木油”就是“没有”、什么“杯具”就是“悲剧”、什么“果酱”就是“过奖”……浅薄当时髦,油滑当幽默。真难以想象,要是“稀饭”就是“喜欢”,那“干饭”是什么?要是“鸭梨”即是“压力”,那“睡觉”岂非成了“水饺”?严肃的汉字如此失范,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记得那一年,我粗略读了一遍先生的《论语今注今译》,便真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比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向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这是孔子在提倡“愚民”,其意是:“对于老百姓,指使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必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一是认为这是孔子在倡导“民权”,因为这句话应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其意是:“对于老百姓,如果他可以,就让他去做;如果不可以,就教他该怎么做。”
囿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基本认同的是“愚民”说,而不认可“民权”说——谁能相信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竟有那么高的现代民主意识?但读了《论语今注今译》,我即为毛先生的注释所折服,因为先生将这句话中的“可”字当作“能”字解,此说也便成了:“老百姓能知道该怎么去做,却不能明白为何要这么去做。”于是,这就不是在提倡“愚民”,也不是在倡导“民权”,而是在叹惜民愚了?也就是说,这是孔子对凡事“只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叹息。而这,不就既与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相连贯、也有孔子的“惟上知下愚不移”可印证吗?!
由此,我若有所悟地觉得,先生所以被称之为“通儒”,还在于他对学问的“触类旁通”,以致他能从原本互不相关的枝节中找到血脉相通之处,一通百通地给《论语》以崭新的内容。而他将自己的注释本取名为“今注今译”,其实也意味着一种穿越历史之“通”:无论是注或者是释,立足点都在一个“今”字;而正是这种立足于“今”的注释,便使得注释者与古汉语之间有了一种别人所没有的通达!
不怕见笑,当时我甚至竟还忽地觉得,“读书破万卷”之说所指的,应当绝非是书读得多,而是书读得透;故而其中这一“破”字,也应当是“破解”之破,而非“破损”之破也。
……柴薪很快就拿出了初稿,于是,壬辰年十二月的一天,我便在他和蔡恭先生的带领下,有了一次清漾之行。而这次清漾之行,真是见我未见之见,闻我未闻之闻,让我对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首先,清漾所蕴含的文气,当说是先生的根基。在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历史的毛氏“清漾祖宅”,我看到历代毛氏先贤与当时名人的往来书柬,诸如宋代的苏东坡、陆游、寇准、朱熹,明代的李攀龙、王世贞、杨继盛……“祖宅”正门前的一副楹联就是苏东坡所写,上联曰:“天辟画图,星斗文章并灿。”下联曰:“地呈灵秀,山川人物同奇。”而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能不与他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既袭先人的文脉、又得先人文气息息相关?再是,虽然毛氏先贤入朝为官者不少(且为后人引以为荣),但先生一生的志愿,却仅是想做一个“明事理的普通读书人”;何以如此?我想恐怕与先生自幼的养正环境不无关系——纵然如今看来,先生这座建于清末的故居,显得低矮陈旧灰暗,但悬挂在墙上的那一幅先生亲笔手书的“虚静恬淡”,那按原样摆放在桌上的纸笔、墨砚,却在温柔细腻的线条里,散发着悠远的馨香;走在故居两进三天井的小世界,一种清静之感便油然而生。于是我想,先生把“明事理”当作一生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明事理”,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淡泊;而这种可贵的性情,不也是基于故居从小对他的熏陶吗?
当地一位朋友介绍说,毛先生在衢州中学堂毕业后,在老家自修了近两年,真可以说是心无旁骛,唯书为伴,“一心只读圣贤书”。
诚如此言。但在我看来,先生的读书,绝不是死读书,更不会读死书,而是把书读活:也就是“既读得进去,又悟得出来!”而先生之所以能把书读活,就是一有静心,二有恒心,三有灵性。只可惜,我辈还能那样静心读书吗?而要是当代的年轻人也能像先生那样读书,那又何愁成不了大家?!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附带说一桩“趣事”。

毛子水故居外景(沙牧摄)
据当地对清漾毛氏族谱的考证,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竟与毛子水同是清漾毛氏的56世。而且,毛泽东和毛福梅都源于清漾迁江西吉水的毛氏一支。于是,清漾也就被宣传成是毛泽东的祖居地。应当说,考证是一种严谨的学问,能考证出毛氏如此盘根错节的血脉,当是一大功德;但如此命名,却让我困惑。因为倘说清漾是毛泽东的祖居地,那在清漾之前和在江西吉水之后的毛氏族人居住处,又是毛泽东的什么“地”呢?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祖地”,这不是在折腾他老人家又是什么?真不知道毛泽东在天之灵对此会作何感想?
更让人费解的是,清漾毛氏“名人馆”的第五展厅居然还以《东方红》为先声,介绍了毛泽东的一家和毛泽东的一生,这于情于理又从何说起?据说,扮演过毛泽东的著名演员唐国强就止步于“第五展厅”之前,说:这样的展厅应当在韶山,你们咋也能这么搞?虽不知当地作何感想,但我却觉得绝对值得深省!
发展旅游,无可非议;扩大影响,理所当然。但江山有关方面的这一作为,恕我直言:就算这不是一种“拉大旗”,难道不似乎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吗?
言归正传。前些年,当地出资修葺了毛子水故居,并辟为毛子水纪念馆。故居中有一尊毛子水先生的半身铜像,目光是那样的宁静,就像先生重返了故乡、正沉思于他以书为伴的一生。于是我又想到:人,总是多读点书为好,而像先生这样的读书人,则更是越多越好!要不,世界还会那么喧嚣浮躁吗?
- 江南的其它文章
- 豆蔻年华的微笑——我的备忘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