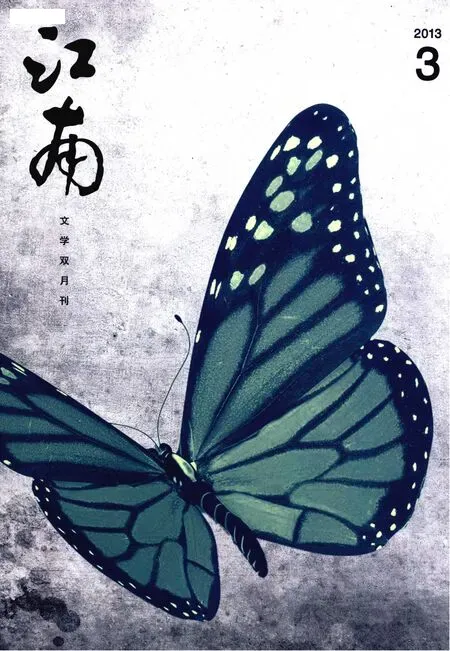书写那个年代是我的天职:蒋韵访谈
蒋韵 张滢莹 董倩
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行走的年代》授奖词
这是一篇气象宏大、诗性饱满的小说。两位不同时间的女子,以相同的激情和梦想进入真假诗人的生活,行步在浪漫和理想的大地之上。她们彰显了诗的神性,却被生活改写了自身的命运。小说直入80年代的精神通道,用两个平行而相交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地行走到一起。小说具有女性气质,语言明亮,个性飞扬,在忧伤的浪漫主义气息里,洋溢着奇妙的理想主义、辽远的历史回声和清冽的艺术气味。这篇回忆逝去历史的作品,再次显示了蒋韵对生命存在和精神救赎的深度思考。在这个泛娱乐的年代里,《行走的年代》有着特立独行的文学品格。
一
记 者:在当下的写作中,许多作品在出版商、读者兴趣等影响下存在一定范式,近年来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尤其如此,许多作者忙着标新立异,最终却形成了题材、写作方式、表达手法等方面更大范围的雷同,写作的独特性丧失殆尽,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倾向的?在您看来,一位作家的独立性应该根源何处?
蒋 韵:其实很简单,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就在于他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在于他是否能够刻骨铭心地将这种忠实呈现和表达出来。所以,说到底,是看你有没有“心”,看你这颗心感知世界、感知生命的质量和能力,这大概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吧。
类型文学是大众文学的必然走向和产物,这并不奇怪。“类型文学”和“类型化”我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类型文学”就像“类型电影”,其中也有非常出色的作品,非常精彩的表达,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劳伦斯·布洛克的推理小说。你要说的大概是所谓“纯文学”范畴内的那种复制现象吧?“标新立异”没什么不对,我在多年前,也曾经非常迷恋现代文学“新”的形式和“新”的表达,至今,也还有人更喜欢我的那一类作品,认为我如今的小说是某种程度的妥协。其实,如果有比较了解我的读者应该能够发现,我小说的变化是在2003年,那是我在美国住了三个多月回来之后发生的,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两者肯定是有关联的。可能是纽约那个艺术之都让我看到了,在今天,无论怎样的“新”和“异”,都能够被迅速地克隆复制,然后淹没。这感觉是惊心的。那么,什么是你自己呢?还有,什么是你族群的呢?这种追问和思考自然而来,它使我的小说观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试着在更为隐秘的地方和深处小心翼翼埋下“我”的印记,就像农民把种子埋进土地。假如你埋下的是麦粒,你还会担心它长成马铃薯吗?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 者:许多作家曾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同国家应在各自的文化积淀下坚守文化“母题”,文学创作也当如是。您如何看待?您又是如何理解在写作中所呈现的“受伤的汉语”?
蒋 韵:“乡愁”和“生命悲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母题”之一,而且是被表达到了极致的母题,这种极致化的表达,这种反复的咏叹,具有超越性和象征性,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最独特的贡献。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东西,是我们的精神印记。就像“毁灭与美”是日本的精神印记一样。值得思考的是,一直到今天,“毁灭与美”仍然是日本文学的母题之一,它被一个个大师不断地丰富着、演绎着、表达着……而我们,在众所周知的长长的断裂之后,至今,可能仍然认为古典的“乡愁”和“生命悲情”距离一个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很遥远,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母题,它们真的和我们今天的书写不再发生关系了吗?
君特·格拉斯多年前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道,他写作的目的是用“受伤的德语”表达一个民族的记忆,大意如此。当时我很警醒和震撼,为那句“受伤的德语”。对我而言,也许那是“语言的自觉”的又一次启蒙。和“受伤的德语”一样,汉语也是伤痕累累的呀。那是我的母语,我所有表达的归宿,也是我的命运。
记 者:在您的许多作品中,人物塑造上会存在这样的特质:他们心中有着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对自由、对理想或者爱情,这种追求不为外界变动所挪移,敏感、执着,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种决绝在当下的物化社会中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有些突兀。面对已经丧失这种对生活的极致敏感的人群,您为何一直选择坚守的姿态?
蒋 韵:很简单,我尊敬这样的人,我凭吊他们。正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日渐稀少,所以我创造他们,是想让他们成为我们精神的翅膀,代替我们飞翔。
二
记 者:《行走的年代》中女子陈香的背后可以说站着整个80年代,而现实最终使她对于一个时代的信仰被冲撞得支离破碎。透过作品,您对于这一时代的祭奠之情也存附其中。对于这个年代,最值得记忆的是什么?是否有些东西是您认为最不该被遗忘,却恰恰随着时间逸散殆尽的?
蒋 韵:《行走的年代》韩文版出版时,我为韩国读者写过一篇小文,现在我想摘录其中的段落来代替我的回答:
“我用我的小说向八十年代致敬,对我而言,那永远是一个诗的年代:青春、自由、浪漫、天真、激情似火、酷烈,一切都是新鲜和强烈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同时,它也是一个最虚幻的年代,因为,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
我不知道韩国读者能否了解这样一个‘八十年代’,但我想,人性和禁忌的永恒冲突、青春的美与壮烈、谎言和信守、毁灭和至痛的生命悲情、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切,是无处不在的。尽管今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诗’所象征的一切似乎已成为遥远的绝响,但,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固执地逆着时光行走。于是,就有了陈香,有了叶柔,有了莽河。如今,我的陈香、叶柔,我的莽河、老周们,还有令人心碎的周小船,千里万里,从中国的黄土高原来到了美丽的汉江边,我又一次将他们放逐到了路上。我不能预知他们将有怎样的命运,但我毫不怀疑,在某一个秋天的黄昏,如洗的蓝天下,‘江南’或者‘江北’,山上或是路边,一定也有一棵叶子金黄的银杏树或是什么别的美丽的树,会和他们突然遭遇。那种纯粹的、辉煌的、善意的美,一样会使他们深深感动:这就是我的期待。”
能够感动陈香们的东西,我想,是应该永恒的。
记 者:在不断有作品问世,开始回望这个激越年代的同时,也有作家提出,随着一个年代的远行,文字形式的复现,会离当时的现实越来越远,而更多地融入个人特质,并在更大意义上成为一种向外界的昭示:这样一段历史,已不可重现,也无法重建。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蒋 韵:我非常认同。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八十年代”是客观的,在文学作品中,所有的真实其实都是“主观的真实”。每个人都有他记忆历史的方式,也有他“真实”表达的方式。任何“真实的记忆”其实都是选择性的记忆。我不是“八十年代”的代言人,我已经说过了,那只是我自己的“八十年代”,那只是我自己的青春记忆。
记 者:在当下的实际创作中,对于许多青年作家来说,由于生活体验的局限,他们更愿意在虚构能力上有所长,同时存在过分依赖情节、堆砌辞藻和空洞叙事等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蒋 韵:坦白说,青年作家的东西,我看得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发言权。但我一直认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必须要面对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乱世还是和平年代。“成长”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呀!有多少文学经典是表现“成长”和出自年轻作家之手。另外,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虚构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虚构和想象力,是小说家的翅膀。当然,虚构不等同于胡编乱造,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尼采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奇特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准备的,而平凡的风景则是为大画家准备的。所以,不要忽略眼前的、身边的“平凡的风景”。
三
记 者:几乎对所有获奖者我都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同样的问题给您。
蒋 韵:我的回答基本上和大家是一样的,是为了一种内心的需要,或者再说得学生腔一点,是为了生命的需要。我觉得除了写作,我也没有别的才能。
记 者:您写作的乐趣是什么?
蒋 韵:我小时候觉得一个人只能活一辈子,如果做一个演员的话就能活无数个辈子,无数个人生,做演员我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做一个小说家,做一个写小说的人。我的乐趣就是我可以走进别人的生命之中。这个可能就是最大的乐趣。
记 者:我们也想去了解别人、去活别人的一辈子,但常常很不容易。您作为一名作家,是怎么去活别人的一辈子,而且能够真实地写出别人的一辈子?
蒋 韵:实际上,做到真实客观地呈现的确是很难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我在揣度别人的生命时,可能我难以绝对真实地呈现,但是我有一种真诚的态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记 者: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作品?
蒋 韵:这是我的一个情结。对我来说,我首先要感谢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是我的青春记忆,是我生命中最有光华、最具浪漫精神的一段时光,而且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来讲,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我是一个过来人,我跟它一块儿走了过来,真的是我内心的一个情结。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一个抒情性的作家,可能在同类的作家中间,我是属于有一些浪漫精神的人。我觉得我是责无旁贷的,书写那个年代好像是我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