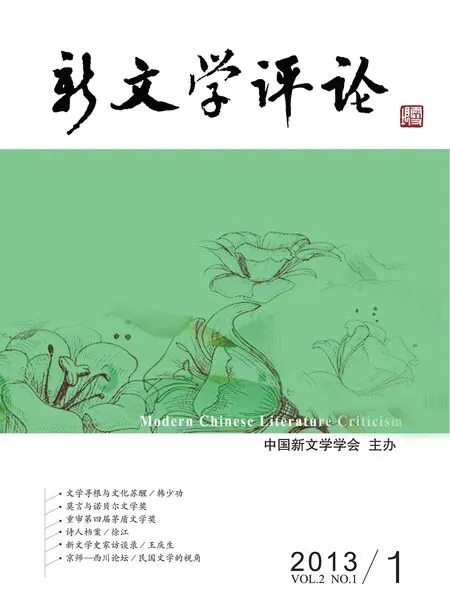文明进程中的诗歌
◆徐 江
任何一种诗歌都是与文明息息相关的。但它朝向文明的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现时段的汉语诗歌。
我不是一个“文明正确论”的持有者,我也知道在诞生了那么多“与文明共进”的伟大作者的人类诗歌史上,还存在着一批对各自时代文明持有批判态度的、同样伟大的作者。后一类人,在世界各国的诗歌传说乃至文科教科书中,还更容易占据主角位置。这样一种“偏爱”,或者更确切说是—— “偏执”,在以推进诗歌的现代审美为己任的当代汉语诗歌作者中也有一定市场,其具体表现为一些作者动不动拎出一两个源自一百年来西方文学和学术成果的关键词,在本土的世象面前表演“怀疑秀”。
多年以前,我曾在《葵》的某一期扉页上选用了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一句话:“诗人是报警的孩子。”但后来渐渐发现,这句话放到汉语的语境里,恐怕会遭遇到大多数情形下被曲解的风险:一些作者对“按响警铃”这个动作的迷恋,是远远大于对“为什么报警”的思考的,正如他们偏爱在文字中塑造自己的“形象”,更甚于用文字解析内心的挣扎与迷惘。
当某个边远的省份贯通了铁路,我们有的诗人会哀叹“原生态被破坏了”、“文明伤害了天然”,大有鲁迅在《风波》中描述的“城里文豪”审视乡村的超迈。而作为这一“超迈”的代价,那条铁路沿线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却被文人们残忍地抹去不计了。这样的高见,有些据说是源于汉语传统中的老、庄,有些则源于那些旧时代西方文明批判者的言论。
在中国,诗人、文人、知识分子对后一类言论的迷恋,有时发展得有些奇怪: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诗歌爱好者,都有可能会复述阿多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过,用同样句式去说“南京大屠杀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后面这一句,有可能比舶来的那句更能撼动本土乃至整个亚洲国家居民的心灵。人类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沉痛,绝不应该由于欧洲大陆近两千万犹太人的苦难而被忽视。当然,由于上述情形,我们更不能够指望那些生来就是“好学生”的虔诚而刻板的诗歌学徒,对阿多诺的名言发出这样的否定:正因为有那些野蛮的暴行存在,人类恰恰拥有了“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梦想”的权利!
“融入世界”不应该是以抹去自身生命中的血痕作为代价的。如果说战争和奴役是一条醒目的血痕,那么贫穷和蒙昧 (它首先包括了那种来自文人自作聪明和“特立独行”的蒙昧)则是深藏我们肢体敏感地带的那条最深的血痕。教条的思维模式,干扰着汉语诗歌的现代化 (就像它曾干扰过人类其他领域的变革一样),这种干扰试图把汉语现代诗简单置换为欧美现代诗的中译版本,同时却又在人们眼前略去了那些杰出的欧美作者植根本土人间的苦痛,酿造出心灵诗篇的艰难与决绝……不过,对致力于继唐诗之后、重铸汉语诗歌辉煌的汉语作者而言,倒不妨把这种干扰看作是来自反向的、激发诗人迈向诗歌智慧更高境地的助力。
“今日之中国,正遇千百年来未遇之变局”,这话本是某个历史剧里的台词,借来概括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以及大到汉语文明、小到汉语诗歌所面临的观念冲击与考验,倒是颇为恳切的。规律、原理如何作用于实践,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如何在剧变的时代,创造出既不媚俗复古,也不简单趋时、克隆欧美的本土诗歌,这是摆在汉语诗人乃至整个西方话语体系外的,致力于本语种诗歌现代化的各国诗人的基本问题。在我看来,解答这一问题只有一个入口:写诗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被自己在诗歌上的伟大理想所役使,他要自觉地回归于一种个人对世界的强大逼视,以身处文明和生活漩涡之中的自身感受,去回应周遭事物对人类尊严和智慧的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让诗歌安于“孤独者 (首先是生活中的)的艺术”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