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
本书旨在对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变迁图式进行剖析,力图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与相关理论进行对话。从资料方面来看,本书采取了剖析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搜集了大量1931—1999年江苏无锡峭岐地区的历史演变资料,其中包括人口、土地、技术、制度变迁等多方面的经验材料与数据。
中国为什么发展:一种探索性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60年来的发展过程表明,包括汤普逊在内的许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所做的研究的结论,几乎都错了,这种错误,不只在于对前景的悲观预测,也不在于其预言实现的程度差别,而更多地在于其预言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汤普逊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性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而这种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工业化过程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按照这种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取决于要素增长。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就是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对于工业发展来说,就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如果这些要素的存量或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意味着要素贡献增长,因而,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也就得到相应的发展。
汤普逊正是按照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前景的。在汤普逊看来,中国的农业之所以难以得到大的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诸生产要素的增长限制。他侧重分析了对农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土地资源的扩大可能性,结论是,中国的土地资源尚有潜力可挖,耕地面积将得到扩大,只是这尚不足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而资本要素,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短缺的。在他看来,不仅资本存量是短缺的,而且在资本的使用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他侧重分析了中国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制度,发现在中国,“就短期贷款而言,这些钱是用来渡过困难日子的。中国农民付的利息简直高得难以想象,月息率通常是3%—4%……结果是许多比较穷的农民不得不给那些放高利贷的寄生阶级当短工”。至于长期贷款,他说:“目前还没有组织得很好的机构来提供购买土地的长期贷款,而且看来也没有任何发展这种机构的前景,除非一个稳定有力的政府执掌了政权,通过合作土地银行以相当低的利率发放购买土地的贷款。”所以,汤普逊指出:“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少购买土地和改良土地的长期贷款,可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妨碍中国农业进展的因素。”(乔启明等,1984:139—140)至于劳动力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当然不是稀缺要素。不仅不是稀缺要素,相反地,倒是影响中国发展的过剩要素。因而,要讨论的不是增加劳动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减轻人口压力的问题。汤普逊重点讨论了通过移民减轻人口压力的可能性,包括国内迁移和向海外移民,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样,综合三个生产要素的发展前景,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是黯淡的。
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黯淡,中国工业的发展前景更为黯淡。考虑决定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三个要素的变化趋势,其结果几乎都是令人沮丧的。自然资源要素对于中国来说是稀缺的,资本也是短缺的,而劳动力同样是过剩的。不仅如此,考虑后来才提出的人力资本要素,即“现代工业需要的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和有经验的工程师、技术员、组织者、熟练的操纵机器的工人”,那么,中国过剩的是简单劳动力,而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却是短缺的。汤普逊还讨论了经济增长理论后来才给予更多关注的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但是,考虑了这种种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依然无法改变汤普逊的悲观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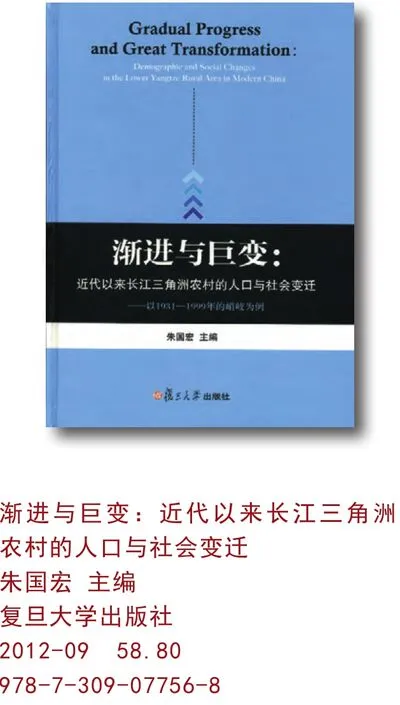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下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发展的现实相悖,部分原因在于分析者对诸要素的变化趋势估计不足,而另外部分原因则是理论本身缺乏张力和解释力。关于前者,一如前所分析,汤普逊对诸要素变化的估计确实有过低倾向,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上,他就远远低估了中国扩大耕地面积的潜力和能力;又如,对人口增长的估计也是用简单外推的办法,既没能预计到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快速增长,也没能预计到后20年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人口转变。不过,饶有兴味的是,汤普逊几处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除非”预设却在后来变成了现实。譬如,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他说:“由于我认为,如果没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的指导,现代的、复杂的工业体系不可能最大限度地为中国人民的福利作出贡献,因此,除非随着政治革命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我对中国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事实是,1949年以后中国确实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政治革命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正是这种制度变革使中国的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又如,关于降低人口增长率,汤普逊指出,“要减轻土地的压力,要使农民生活得较好,要使从农村到城市去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唯一可能的办法是降低出生率,要使人口的自然增长低于新地区新工业吸收新的人口的能力。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在三四代的时间里中国的出生率有明显的下降,这只能是希望而已。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能设想中国的牢固的家庭制度在几十年里会有很大的放松”(乔启明等,1984:168,170)。事实是,中国的出生率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就有了明显的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和幅度都是令人惊讶的,相应地中国的家庭制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关于后者,正如现代发展经济学所批评的那样,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亚洲经济增长奇迹的讨论中已多次被提及。现在看来,在发展道路、发展方式乃至发展步骤等方面都需要重新加以研讨。对中国来说,需要特别加以考虑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的积极作用与人口大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们常常注意到人口过多所引出的“人满为患”问题,但对于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这已为许多研究所证实。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发展中是否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呢?西蒙(J.Simon)就曾系统分析过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参见西蒙,1984。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曾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4人口的事实,但是,却很少有学者探究其中人口本身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珀金斯(1984:1)在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时,也只是说:“中国农民的干劲为世界的伟大文明奠定基础作出了贡献。”如果不能正视人口的这种积极作用,就很难解释中国历史上在庞大人口压力下获得的经济的任何发展;同样,也难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在更大的人口压力下获得的更大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都与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同,而作为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早在2000年前就拥有世界近1/4的人口王国斌认为,在中国,人口的明显变化,会改变工资、地租和地价之间的关系,并影响农民按照劳动需要而选择种植何种作物。见王国斌,1998:22。。在农业经济条件下,庞大的人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人地关系,是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朱国宏,1996)。同样,中国的人口国情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殊的人口城镇化道路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以高劳动投入为特征,这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似乎处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中国特定经济发展条件下却是不可逾越的,也是中国经济获得发展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事实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对于人口大国来说,高劳动投入、低资本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非被低劳动投入、高资本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不可?甚至,这是否是人口大国在一定条件下一条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克曼(P.Krugman)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亚洲快速经济增长问题时曾指出,亚洲的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奇迹”,而是一种以增加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外延型增长。如,中国1978—1984年的经济增长波,是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其实质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劳动投入;1992年以后的经济增长波,则源自大量的外资流入和农村释放出的大量流动劳动力。这似乎说明,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也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见Krugman,1994。
(2)中国的文化背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概括为儒家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显然与西方国家不同。韦伯十分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根据他的研究结论,西方文化中的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原因;而儒家文化则恰恰相反,不仅没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韦伯,1986,1995)。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的经济普遍快速发展,使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也形成了诸多对韦伯理论的批评。不管这些批评正确与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承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不同的文化对经济发展将起到不同的作用,正如韦伯比较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一种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政策措施和制度,如果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社会中去,也许会适得其反,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何梦笔,1996:25)。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加以深入的探讨。
(3)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经济学中新制度学派的崛起,既说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更说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引起关注。在解释近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时已有很多研究对制度因素的作用给以特别的关注。人们注意到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关系网络、权利结构等因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并不适合于一个具有强烈家族观念、尊重权威、重视意见的一致性、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中国。譬如,刘广京通过对旧中国正统观念的研究发现,旧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文化来实现对社会与人的控制。汉密尔顿(G.Hamilton)曾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这种用来控制社会与人民的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与西方的比较发现,这一文化的中心在于自我管理;实行自我管理的组织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地方主义基础上的社团,另一种是具有各种不同结构的家庭,前者在中国法制缺乏的条件下具有类似于西方社会法的作用,后者则发挥着类似于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作用。费孝通在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时,则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的特征,即每个人都生活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中国人的行为也因在这个关系网络中的相对地位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参见胡必亮,1996:3)。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中国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行为与西方有很多不同。因此,如果不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能很好地解释难以用西方的经验模式来理解的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特别是近30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