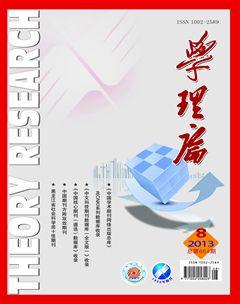论罗马法中的和解
于锐
摘 要:罗马法中,和解是一种常见的无名契约,在某些情况下也构成“不索债之简约”,和解协议因订立方式是否为口约而产生不同层次的效力。罗马法对和解的保护以契约为基点,和解虽与诉讼泾渭分明,但其效力呈现出多层次、与判决效力趋同的特征。罗马法中和解适用范围与保护手段的拓展与契约精神的发展相契合,并引领了后世和解契约的变迁。
关键词:和解;罗马法;和解协议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25-02
作为私立救济的表现形式之一,和解在原始社会即与自决一起作为纠纷解决的原初方式被广泛适用。与自决相比,和解更多地体现了某种形式上、行为上的妥协,更利于消除对抗、弥合冲突主体的情感,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肇始于罗马法。罗马法中和解的种类及效力均呈现出层次性差异,但法律对和解的保护范围在日益扩大并得以强化,这为我们从契约视角重新审视和完善和解制度提供了有益思路。
一、罗马法中和解的种类
罗马法中,“和解(transactio)者,谓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不确定之权利而发生之契约也”[1],和解的对象,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争议或者尚未发生但可能引发纠纷的争议。根据《法学汇编》的记载,和解属于债或劳务与债或劳务之间的交换。罗马法中的无名契约,当事人双方应当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在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给付后,可向他方提起请求返还之诉或者履行约言之诉。和解属于较为常见的无名契约,主要适用于一方已经履行义务的情形,与有名契约同为债的发生原因而享有诉权。
与独特的诉讼制度相适应,在各种契约外还存在着简约,不能与契约一样受到市民法的保护。其中有诉权的简约为“穿衣简约”,无诉权的简约为“裸体简约”。裸体简约虽不能成为诉讼的根据,但可产生自然债务,债务人自行清偿的,不得托辞错误而要求退还,并可以作为抗辩的理由[2]。和解也可以表现为“不索债之简约”(pactum de non petendo)或称为不起诉合意: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以简约形式约定,债权人在一定时期或者一定情况下,或永远不向债务人提出清偿的请求。该合意起初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后来在罗马法的实践中,允许债务人依此简约向债权人提出抗辩,渐渐成为一种债的免除方式[3]195。因此,和解合同在罗马法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无名契约,在某些情况下也构成“不索债之简约”,二者在法律效力及诉权行使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均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承认和保护。
二、罗马法中和解的效力
和解协议因订立方式是否为口约而发生不同层次的效力:如果以口约形式订立,则当事人可提起要式口约之诉请求履行,如合同中有违约金的规定还可以请求偿付;如果仅仅基于双方当事人对某事件之争执合意让步者,已经履行给付的当事人一方可提起履行约言之诉请求对方履行;如果当事人双方均未实际履行,此合意视为“空虚约言”(nudum pactum)[1],即“裸体简约”或“无形式简约”,是两个以上当事人采用法定契约形式以外的方式达成的协议,不能产生诉权,但在实践中,执法官往往对其加以考虑和维护。如果当事人通过简约变更了原法律关系或者达成了新的协议,即使不能产生完备的债,若一方无视通过简约达成的协议而向对方提出请求时,对方也可提出既定简约抗辩(exception pacti conventi)相对抗[3]107。因此,罗马法上和解的效力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空虚约言做出的和解具有最低层次的效力,是导致旧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原因之一,其不能创设债权,属于不起诉合意(不索债之简约)的一种情形;二是以法定契约形式做出的和解,除了具有最低层次的效力之外,还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4]。
此外,和解与判决相比,虽然解决纠纷的目的相同,但二者在效力上仍有所不同[2]:第一,判决主要是确认权利,和解可产生新的权利。在帝政后期,判决并不当然发生消灭权利的效力,仅产生“既决案件的抗辩权”,和解则当然能够消灭权利;第二,判决受“执行诉”的保护,和解则仅受“前书诉”或不特定的市民法诉讼的调整。第三,和解可因错误、欺诈、胁迫等原因被撤销,判决则不发生此类问题。
三、罗马法中和解的规定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首先,和解的定义沿用至今。历经后世变迁,罗马法关于和解与和解协议的定义沿袭下来,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关于和解的定义多包含着“互相让步”、“终止争执”等要素。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规定:“和解系指诸当事人用以终止已产生的争议或防止发生争议的契约”。台湾地区民法第736条亦规定:“称和解者,谓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防止争执发生之契约。”
其次,和解标的具有广泛性。在罗马法中,和解可产生、消灭债权,转让物权,除人的身体外,通常各种权利(包括奴隶和农奴的自由权)都可为和解标的。《十二表法》中规定,由私犯所生的债权,可因双方的和解而消灭。即使是盗窃案件,若只侵犯个人利益,当事人也可以进行和解。原则上当事人可以自由订立和解契约,但关于抚养或其他类似事件之和解,非经裁判官许可,不得为之。时至今日,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学理上亦赞同和解标的应以当事人能够处分为限。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66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具有处分争讼标的的能力。根据权利性质或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这些权利不属于当事人可处分的范围,则和解无效”。因此,物权关系、债权关系、无体财产权关系、亲属关系、继承关系甚至某些公法的法律关系,只要和解内容在法律所容许的私法自治范畴之内,即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的权利均可以成为和解标的。
再次,和解被定性为契约,乃债的发生和消灭的原因之一,当事人可以根据和解契约请求履行义务。在罗马法中,和解可以产生权利或者消灭权利,既作用于债权,又是物权取得或丧失合法化的一般原因或行为[5]。后世的民法典多效仿罗马法,明确和解契约产生和消灭权利的效力。例如《日本民法典》第6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和解被认定有争执标的权利,或相对人被认定为无此权利,当原来无此权利或相对人有此权利的确证被发现时,则该权利即为因和解而移转于其人或消灭”。
最后,对和解之债的承认与保护。罗马法中,不当得利为准契约之一种。对和解所产生之债,不适用无债清偿返还的规定,债务人若否认债的存在时,可加倍处罚,即使就不存在的债务而误为清偿给付时,亦不得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此项规定旨在保护和解的效力,避免讼累。同时,罗马法对和解的保护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初期阶段,一方当事人实际履行后,可提起履行约言之诉,此为无名契约层面上的和解。若双方均未实际履行,此合意为“裸体简约”或“无形式简约”,并不享有诉权。后期,随着和解契约适用范围的扩张,执政官逐渐考虑并认可了其效力,允许对方在诉讼中以和解为由提出既定简约抗辩。罗马法对和解之债的定性与保护为大陆法系国家和解的制度化提供了典范。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69条规定:“和解不得因当事人之间争讼涉及的诸问题中的法律错误而撤销”。法国、埃塞俄比亚等国民法典也有类似的内容。这些规定从不同程度体现了各国对和解效力的尊重与保护。
作为契约之债,和解无法获得判决所享有的“执行诉”的保护,不具有既判力。但如罗马法谚所云,“和解协议相当于已决案”。和解虽不是诉讼,但与诉讼结果极为接近。在罗马法中,由当事人订立的“不索债简约”(即和解之一种),未依法定方式免除债务时,债权人往往在免除后反悔,又请求债务人给付,为维护诚信原则,只要当事人具备免除债务和受领免除债务的能力,又曾同意免除的,如果债权人事后反悔,债务人即可提起“既定简约抗辩”拒绝其请求,因此,和解协议的效力与“已决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马法中对和解的保护以契约为基点,和解虽与诉讼泾渭分明,但和解的效力呈现出多层次、与判决效力趋同的特征,其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深远。除法国、埃塞俄比亚以外,多数国家的民法典沿袭罗马法的规定,否认和解合同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效力和既判力,却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了和解合同所拥有的确定效力。例如,最新修改的《荷兰民法典》第900条规定,和解合同所确认的法律状况即使与现存的状况不同,此确认也有效[6]。日本民法的通说也认为和解的核心效力为确定效力[7]。
作为民法法系的起点,罗马法缔造了辉煌的法律文化,和解契约的制度化亦发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中和解适用范围与保护手段的扩大,与契约精神的发展相契合,并引领了后世和解契约的变迁。自罗马法开始,和解便从未脱离契约之视域,这也正是我们冲破诉讼法之藩篱,以契约之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丘汉平.罗马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354.
[2]周.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82-183.
[3]黄风.罗马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宋旭明.传统和解立法矛盾之检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6).
[5][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中国政法出版社,1992:393.
[6]DutchCivilLaw(DCL)[EB/OL].http://www.dutchcivillaw.com/
civilcodebook077.htm,2012-3-20.
[7][日]我妻荣.民法讲义.债权各论中卷二[M].周江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