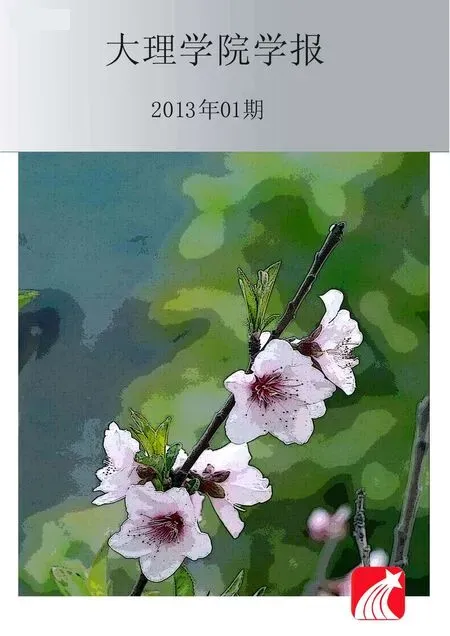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刘 黎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一、黑死病的传播
黑死病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公元1348年至1350年,它大规模地席卷英国。此一高峰过后,黑死病又间断性地暴发,如同幽灵一般,徘徊了一个多世纪,公元1440年以后,疫情才开始消退。据意大利史学家布里埃莱·德穆西记载,公元1346年金帐汗国的军队围攻加法时,其军中已发生黑死病疫情。双方僵持不下,为打破战争格局的平衡状态,蒙古军队将患黑死病而死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加法城内。后来加法城里的战争幸存者,主要是意大利商人,便纷纷沿海路逃向意大利,这些战争难民中有黑死病菌的携带者。此时的意大利是欧洲的商业中心,人员流动极其广泛、频繁,黑死病疯狂地尾随其后向欧洲各地发起“攻击”,“1348年圣施洗约翰节前夕,两只船从多尔塞特郡的麦尔卡波城驶过,其中一只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有一个船员从加斯科涅带来了可怕的瘟疫种子,麦尔卡波城的居民因而成了英格兰第一批染病的人”〔1〕。黑死病进入英国,“1349年5月,瘟疫到达了英格兰北部并于21日抵达约克城,英国全境沦陷”〔2〕。
二、英国政府的反应——“敬天命”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基督教在社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3〕。鉴于此,当黑死病来临之际,教会必须向上帝的子民解释黑死病——“一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传染性疾病”〔1〕。教会提出黑死病的病因——天谴说。“这种从属于‘原罪—赎罪—审判’信仰体系的认识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临的惩罚,而这种罪孽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上的败坏”〔3〕。约克大主教威廉·苏支说:“因为人类不可更改的命运,不放过任何人的死亡无情地威胁着我们,除非耶稣基督神圣的仁慈从天上展现给他的子民。仅有的希望就是自己尽快地回到他那里,他的仁慈比公平更重要,并且,在宽容上最慷慨的主,会为有罪的人转意归主而由衷地欣慰;用恭顺的祈祷恳求他,善心和仁慈的上帝,会消解他的怒气,收回瘟疫,不再让其传染给他用自己珍贵的鲜血救赎的人们”〔3〕。更为直接的解释是坎特伯雷主教发布的训令——“上帝……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的受苦方式涌起,并且用它们来恐吓、折磨人类,这样就可以驱逐他们身上的罪孽。进一步说,英格兰的王国因为国民与日俱增的傲慢和腐化以及他们数不清的罪孽,加之那场劳民伤财战争的重压和其他的苦难,而变得荒凉而苦痛。如今,我们的王国又处在了这场四处扩散的瘟疫和可怖的死亡蹂躏之下”〔4〕。教会认为黑死病“显然是由于人类的罪孽所引起的,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却忘了上帝的恩赐”〔4〕。中世纪的医学是神学的婢女,局限了当时的认知水平,不可能科学地解释黑死病的病因,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神的身影。“1349年,国王爱德华三世通令各主教,称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们自作自受……”〔3〕,在中世纪特定的时代局限环境,科学的医疗条件无法解除人们外部疾病痛楚的情况下,要去维持社会的稳定,消除人们内心的恐惧,宗教无疑是最有效的选择与策略。
在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教会虽然社会影响力甚大,但作为社会一大结构支柱的一国政府之作用亦不容忽视,尤其是英国,自14世纪之始,国王权力就有压过教会权力之势头,至亨利八世之宗教改革,彻底确立王权高于教权、教权服从于王权的格局,建立英国国教——安立甘教,脱离罗马教会,在此不作展开论述。所以英国政府在应对黑死病时,其作用是值得研究的,教会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地夸大。再者,“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由若干公民组合而成的,以最高的‘善’为目的的最高社团”〔5〕。此即是西方世界从部落到国家演变发展的理论基石,人类建立政治社会的目的即为此。中世纪的英国政府虽是在上帝的光环下存在,但其原始的基石还是以这种对民众的高度负责与其成熟的理性为支撑的。所以,在面对社会动荡、民众的恐慌,笔者认为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在“敬天命”的原则下积极地“尽人事”。
三、英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尽人事”
黑死病作为一场大瘟疫,首要的是进行医疗救助。但是中世纪以教会为主导的医疗体系其作用是有限的,医疗条件恶劣,难以应付如此猛烈的大瘟疫,高死亡率是必然会出现的。黑死病期间英国的人口死亡率——“与死者接触较多的受俸教士的最大死亡率代表了当时总人口死亡率的上限,约为45%;而生活优越的大领主的死亡率当为总人口死亡率的下限,约为27%;而作为普遍大众的主要组成部分,乡村劳动者的死亡率在40%左右;故而……当时整个英国的总人口死亡率在30%和45%之间”〔4〕。拉塞尔估计,“不列颠群岛500、600、1000、1340、1450各年的人口数字分别为50万、50万、200万、500万、300万”〔6〕。就此笔者作一个相对粗略的计算,英国在黑死病期间的死亡人口大致在150万耀225万。这样的数据表明,每天都有人倒下,民众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英国著名政治家托马斯·莫尔曾在书信中谓然感慨:“我相信,血战沙场也比呆在伦敦城内要安全得多”〔7〕。
英国政府积极地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在黑死病期间“英国总人口的死亡率在30%和45%之间”〔4〕,这些死亡人口需要大片的墓地来掩埋,而突如其来的大瘟疫暴发,原有的墓地在吸纳如此多的死亡数量方面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墓地不堪重负,对死者的掩埋继而成为了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中世纪教会在死者墓地的选择与开辟上具有权威的决定权,在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围绕墓地问题,民众还与教会多有冲突”〔3〕。黑死病来临之际,基督教教会首当其冲,教职人员与患病者接触的频率非常高,教皇本尼迪克特对英国境内10个主教区的受俸教士死亡率进行了统计〔8〕356。见表1。

表1 10主教区受俸教士死亡率统计情况
通过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教职人员大量死亡。虽然教会在面对此种情形下,大量地增补教职人员,但其增补的数量与其增补人员的工作效率较之之前,无疑是大打折扣的。“受制于教职人员的缺乏,此时的教会对教职人员的控制已相当有限”〔3〕。以此作为反观,政府必须承担起填补教会因教职人员死亡所产生的权力空白。虽然政府行政官员亦不能例外地受到死亡的威胁,但较之教职人员来看,死亡官员不如教职人员多,如前所述,教职人员首当其冲,与死者接触频率高。英国政府与教会通力合作,颁布大量特许状,帮助支持教会开辟墓地,例如“在伦敦开辟公墓的过程中,政府积极加以支持,爱德华三世后来还为西多会的修士修建圣慈玛利亚修道院”〔9〕37。在偏远的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经济落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教会势力不能强有力地触及,物质文明决定着精神文明,这是教会势力薄弱的地区,政府行政力量的触及深度则强于教会,疫病事宜则多半由政府行政官员及其隶属的相应部门处理。此外,在瘟疫肆虐之际,食物奇缺,一部分唯利是图的商人趁火打劫,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导致物价飞涨,民众生活紊乱;一些不法之徒或好吃懒做的宵小之徒则趁乱行盗窃、抢劫等勾当之事,等等。面对一系列瘟疫导致的连锁恶性效应,英国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显然优于教会,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些领域是不能作为的,比如教会虽然有法庭之设置,但主要是宗教事宜,而这些“世俗”之事,则不是其“分内”之责。
政府亦有大量的行政官员死亡(相对不及教职人员死亡严重),“中书法官罗伯特·保池耶在1349年因瘟疫而殁,其继任者罗伯特·撒丁顿又于次年步其后尘”〔4〕,“德文市在瘟疫流行时有1个市长、1个财政官、2个验尸官和3个执行官去世”〔10〕。英国政府积极地选拔得力官员填补空缺,保证政府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此外,黑死病肆虐期间,各方面事务增多,政府还增加了官员的职位和数量,“在多塞特郡的布里德波特,因死亡而导致的事务过多,市法庭增加了2个执行官”〔4〕,以此来处理因瘟疫而带来的大量行政事务。政府还缩短了一些事务的法律程序,如遗嘱的确立问题,在黑死病来临之前,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审批和确认,而黑死病发生之后,“往往一周甚至一日之内就可以完成”〔8〕137。诸如此类的措施,英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尽力而为,在此不作过多的赘述。
在瘟疫肆虐下,人口损失严重。在中世纪“税”人与“税”地相互交错使用的赋税情况下,这加剧了赋税征收的难度。如汉普郡“因为在瘟疫流行中死者甚众,奴仆和劳力都不可寻,当地居民悲惨地陷入了贫困之中”〔9〕38。国王下令减免赋税。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当时的英国是普遍情况当无可置疑。减免赋税这种必要的措施,在人类文明史的此类发展情形中是屡见不鲜的,也是统治者屡试不爽的政策,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相通之处。此外,政府还保障民众对土地的占有权,使幸存者有田可耕,保障生存的需要和底线的赋税,“鉴于瘟疫肆虐,允许庄园尤其是王室庄园的占有和各种没有获得许可证的佃客继续行使同样的权利,直到国家的人口再度变得稠密”〔11〕。
黑死病暴发之后,社会动荡不安,人口的流动比先前剧烈。劳动力的转移和朝圣最为普遍。“为了防止黑死病后劳动力外流的加剧造成社会动荡并为了控制工资上涨”〔9〕39,公元1349年夏,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令》:“王国之内凡身强力壮之男子和女子,年龄在60岁以下者,无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若非靠经商或做活为生,或无钱财、土地以维持生存,并且他们没有为其他人劳动,就需从事让他们做的工作。并且其酬金、口粮、薪水的支付,都需以朕即位后第20年(即公元1346年)的当地惯例为准”〔4〕。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整个英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在前工业革命时代,生产技术与效率低下,劳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口的多寡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带动或制约的作用。其作用是肯定的——在那个特定的时段地域发挥作用——应急作用。在教会“天谴说”的指引下,当时迷信和愚昧泛滥,企图通过祈求上帝的原谅,结束瘟疫的肆虐是社会普遍接受的观点和信念,而朝圣则是更为虔诚的方法,于是人们纷纷踏上朝圣之路。现在学界普遍认为黑死病的疫源为中亚地区,基督教的圣地即在于斯,这样更为加剧疫情的传播,朝圣无疑是羊入虎口,朝圣返回之人极易感染黑死病病菌回国,对疫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导致恶性循环。“1350年1月,国王发布公告,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武装人员、朝圣者以及其他人出境,如有违者,立即逮捕,所有财物一律充公”〔12〕。此措施和《劳工法令》是相联系的,黑死病来临之际,人口大量死亡,必然带来劳动力的大量缺失,要维持整个社会不致崩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限制人口流动,是必然的可行之法。
同黑死病的斗争,“大体上经历了蒙昧、理性和科学三个阶段”〔13〕205。在黑死病暴发的早期,蒙昧的态度是占多数的。随着疫情的发展,政府命令在大街上架起熊熊大火,其目的是要净化空气。“此外,大力提倡吸烟以防瘟疫,即使是儿童也被逼着吸烟”〔13〕205。尽管这些方法不能抵住黑死病的攻击,但就算这样,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力所能及地做了,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承受能力和认知范围内。
随着对黑死病认识的不断加深,其应对措施也并驾齐驱地跟进。据笔者研究相关资料表明,英国政府通过专门的卫生立法,要求居民保持街道的整洁,控制屠宰场散发出来的臭气等。意识到腐烂和污浊的空气和瘟疫有某种关联,强调要同二者作斗争。除此而外,还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禁止人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当然教会进行的所谓“祈祷”除外)以防止黑死病菌传播;对黑死病死亡者的掩埋加以规范的治理,不能随意丢弃,否则会加速传染更多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形成恶性循环之势;限制人群出入黑死病疫区;禁止和黑死病疫区进行贸易和人员往来。上述都是英国政府在当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黑死病在英格兰王国的肆虐所做的积极的“尽人事”的回应。
当时基督教教会亦发生了大分裂,教会势力每况愈下,昔日的圣城——罗马,业已变成罪恶之城,因为其在做极尽敛财之事,如抛售赎罪券,公然宣称这是进入天国的入场券。此时,法王腓力四世雄心盖天,王权与神权在此狭路相逢,经过一番争斗后,教皇一败涂地,被迫迁居法国小城——阿维农,被屈辱地冠以“阿维农之囚”,这从公元1305年一直持续到1378年。教会势力遭到重创,权威不复往昔。尤其是英国,一方面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再者由于与法国的“百年战争”,相互交织,教会在英国的影响力没有大陆国家那样的“霸道”。教会的作用固然不能否定,其体制化的组织不容忽视,但其作用是有限的。综上所述,在当时的外部“大环境”和英国的国内“小气候”的相互作用下,英国政府在黑死病降临之际的作用是不容被笼统的教会“光芒”所掩盖的。
四、结论
黑死病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频频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关注当时一国政府在面临黑死病时所做的努力的研究还是少数。从微观史学的角度看,很值得重视。尽管中世纪教会的影响和作用独占鳌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作为统领一国民众之政府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此文的主旨不在于借鉴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降临在不列颠肆虐之际所做的具体的防治措施,因为与我们今天的科学水平相比,当时的科学水平相当于人类文明史上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程度不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关系。在于借鉴在这场当时被称为“大瘟疫”的黑死病暴发并无限蔓延时,整个英国朝野所做的应对策略的精神思想,思想是人类文化永恒的结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瘟疫,英国政府很现实地与当时对社会具有权威力量的基督教教会通力合作,尽管教会所谓的“天谴说”的解释是荒谬之极的,但在科学水平不足的情况下,用宗教的精神来稳住极度恐慌的人群,维持社会的稳定,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和教会在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上有较大的差距,并互相明争暗斗。但是在灾难面前,用现实主义来实现国家渡过大灾大难,这一点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英国政府虽在宗教笼罩下运行,但并没有等着上帝的恩赐,而是积极地尽自己的能力,减少黑死病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程度。这种务实的态度,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1〕Gransden,Antomia.A 14th Century Chronicle form the Grey Friars at Lynn〔J〕.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57,72:270-279.
〔2〕高铁军.近几年国内中世纪黑死病问题研究综述〔J〕.世纪剑桥,2007(6):95-96.
〔3〕李化成.论黑死病期间的英国教会〔J〕.安徽史学,2008(1):5-9.
〔4〕李化成.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原1350年〔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89-200.
〔5〕王钧林.从《政治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J〕.齐鲁学刊,1982(5):55-60.
〔6〕Bardsley,Sandy.Women,s work reconsidered:Gender and wage differenti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J〕.Past&Present,1999,173:199-203.
〔7〕叶金.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53.
〔8〕Ole J.Benedictow.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M〕.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04.
〔9〕李化成.黑死病期间英国的社会救助与政治〔M〕//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0〕Maryanne Kowaleski.Local Markets and Regional Trade in Medieval Exet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7.
〔11〕大卫·休谟.英国史II〔M〕.刘仲敬,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226.
〔12〕Susan Signe Morrison.Women Pilgrim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J〕.The Joum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ty,2002,53(2):333-429.
〔13〕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新修订《湖北省宗教事务条例》解读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