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刺绣几何纹的功能特点及文化内涵
刘咏清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江苏昆山215325)
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的500年,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成就斐然的时代,有学者称其为人类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1]。综观人类“轴心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除了古希腊、古印度留给人类经典的早期西方艺术样式之外,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受老、庄“道学”思想影响的伟大的楚国艺术也给世界历史宝库留下了辉煌灿烂的艺术遗产,它是人类艺术史上独立于早期西方样式的典型的东方样式,在其后“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中对于西方艺术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2]。
楚国艺术的辉煌成就,除了音乐、舞蹈之外,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器物、织物的装饰工艺上。特别是织物装饰工艺,最有代表性的是刺绣艺术。由于刺绣的平面性、纯手工性的特点,较之器物装饰来说更接近于楚人的精神脉动;又由于其伴随着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而生,具有人类农耕社会的本元性特征,因此楚国刺绣艺术是楚艺术中最能体现楚国社会人文精神内涵的一种工艺文化形式。
楚国刺绣艺术的辉煌成就,除了丝织面料大量使用、针法进步之外,其“恢诡谲怪、惊采绝艳”的图案装饰,是其具有独特地域艺术风貌的主要原因。楚国刺绣中的图案就其题材类别来说,大致可分为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纹3类。动物纹主要以图腾形象的龙凤为主;植物纹主要以具有求吉辟邪功能的茱萸、莲花和生命树为主;几何纹则主要以抽象概括的菱形、方形、圆形、涡形和S形纹为主。而楚国刺绣图案中的几何纹具有与动物纹、植物纹不同的艺术功能和文化特性,因此本研究着重对几何纹的种类、功能特点及历史文化涵义做深入的阐释。
1 楚国刺绣几何纹的种类及其功能特点
楚国刺绣图案较之楚国提花丝织图案来说,几何纹所占的比重远不如提花丝织图案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花丝织图案由于织机工艺上的制约,主要表现题材是以菱形为主的几何纹;刺绣工艺相对来说较为自由,图案表现的题材及尺寸大小均不受工艺限制,因此变化多端的动物、植物纹就成为其表现的主要内容。楚国刺绣中的几何纹仅仅局限于菱形、方形、圆形、涡形、S形等屈指可数的几种类型,其表现形态大多不是作为独立性的主题纹饰,而主要是作为整体图案的布局框架,表现得相对隐晦。主要的功用在于成为图案的布局框架来规统动态强烈的动植物主纹,使其具有多样变化、对立统一的形式美感。
1.1 几何纹的种类
虽然楚国织物图案中的几何纹种类繁多,如提花织物中细分出的几何纹就有菱形、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半圆形、椭圆形、三角形、六角形、七角形、多边形、不规则形、十字形、工字形、八字形、塔形、弓形、涡形、S形等近20种之多,但如果以出现较为频繁的几何纹作一概括,却仅有几种,这在楚国刺绣图案中尤其如此。归纳楚国刺绣几何纹的种类大致可分为菱形、方形、圆形、涡形、S形5种。
菱形纹:是楚国织物图案中运用最多的几何纹样。菱形纹在(三代)铜器上较少见,在(原始)陶器上较多见,由于经纬线的直线性质,在丝织上便占绝对优势。丝织品的菱形纹变化多端,或曲折,或断续,或相套,或相错,或呈环形,或与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形纹、Z形纹、十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圆圈形纹、塔形纹、弓形纹及其他难以名状的几何形纹相配,奇诡如迷宫,由菱形统摄,似乎楚人有意要把折线之美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3]。在楚国刺绣图案中,菱形纹也是运用最多的,充分体现了楚人对于菱形纹的偏好。
方形纹:是楚国刺绣图案中出现频率仅次于菱形的几何形纹样。方形是原始方形文化的产物,菱形纹是由早期方形纹演变而来。由于方形纹在规律化的排列中缺乏动感和变化,在求动、求变的楚人看来,方形纹不如菱形纹那样与他们的审美气息相统一。
圆形纹:是楚国刺绣图案中运用较多的几何形纹样之一。它除了为主体动植物纹样作烘托铺陈的作用之外,也常常作为独立的装饰单位。作为独立装饰单位的圆形纹其表现“上天”的观念具有着深刻的历史涵义。
涡形纹:是楚国刺绣图案中运用较为广泛的几何纹之一,与传统水文化相关联。这种纹饰的变体不仅可以演化成云雷纹和水纹,而且在楚国刺绣中的主体动植物纹样大多都是遵循涡形结构来设计创作的。有时,涡形纹甚至还成为主体动植物造型中的一部分内容。
S形纹:是楚国刺绣图案中的主要几何形态之一,两两反向对应的涡形纹就形成了S形纹。这种形态以构成元素反向组合为特征,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逆、回旋反转的关系,充分表现了艺术最基本的多样统一变化的精神。
1.2 几何形的功能特点
除了少数圆形、涡形纹之外,楚国刺绣图案中大多数几何纹都不是作为独立的装饰单位出现,而是作为主体动植物纹样的背景或布局框架。由于楚人巧妙地运用几何纹规统烘托动态强烈的动植物主纹,从而形成一种曲直相宜、动中寓静,集活泼与严谨、细柔与刚直为一体,具有特定地域和时代美感的经典艺术形式。
在楚国刺绣图案中,主体动植物纹样常常是变化多端、少有雷同的。以凤为例,不仅各地出土的不同绣品上的凤形象差别很大,就是同一幅绣品上的凤形象也不尽相同。其艺术组合在视知觉上往往形成一种奔放畅达、动感强烈的效果,如果用色再富丽多变,则会让人眼花缭乱。用几何纹规范变化多端的动植物主纹,则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2号战国楚墓中发现的“动物花卉纹绢绣”(图1),在浅黄色绢地上绣出一个长方形边框,用棕色绣线,以开口和闭口锁绣两种针法,绣出4组动物花卉纹图案。绣纹粗细相配,绣技精巧娴熟。这种在长方形边框中刺绣动物花卉的组合纹样,在商周以来的丝绸织物中尚属首次发现。绣品的纹饰与同墓出土的木雕漆器花纹特征比较接近,充分显示出楚艺术的特征。1981年在湖北江陵九店砖厂战国楚墓中也发现有“一凤三龙相蟠纹绣”(图2)和多件飞凤花卉纹绣。一凤三龙相蟠纹绣和飞凤花卉纹绣都是将简化的凤鸟纹置于方形纹正中,四角各有一个圆环,这种结构模式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

图1 动物花卉纹绢绣Fig.1 Embroidery with animal and flower patterns

图2 一凤三龙相蟠纹绣Fig.2 Embroidery with a phoenix and three dragons coiling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幅著名的“一凤斗二龙一虎”的刺绣(图3),这件刺绣图案在整体构图中极为巧妙的是,利用了凤的翅、尾和花卉组成了别致的菱形纹。这种菱形结构恰好能够平衡或者摆脱其主体的动植物造型大量地运用动感强烈的曲线给观者所造成的视觉疲劳感和心理不稳定感,从而营造出一种动中有序、繁而不乱的氛围。这种巧妙地利用动植物形态组成几何形来平衡和统一画面的例子不乏枚举,湖北荆州博物馆藏战国中期的一幅“一凤一龙相蟠”的刺绣图案也是运用了上述手法。

图3 一凤斗二龙一虎纹绣Fig.3 Embroidery with a phoenix fighting against two dragons and one tiger
楚国刺绣图案中的大多数几何纹都呈一种隐性形态,主体动植物纹样多作适形构成。适形构成是指根据一定的几何外形要求来进行纹样的构图。它是将纹样素材经过变化后,组织在一定的几何形外轮廓线内,即使去掉外形,仍具有外形轮廓的特点。湖北荆州博物馆藏战国中期的一幅“三头凤”刺绣图案的长方形框架就呈隐性形态(图4)。奇特的“三头凤”和排列有序的植物纹都作适形构成。根据笔者研究,这种长方形是典型的“黄金矩形”,主体纹饰构图的节点都是依据黄金比例来考虑的[4]。

图4 三头凤纹绣Fig.4 Embroidery with three phoenixes
楚国刺绣图案中还较多地运用一种几何形的复合结构。复合造型是楚艺术造型的主要特点,如龙凤造型常常与花草植物合二为一。这种复合造型也运用到几何形的表现中,刺绣图案中常用几何形的复合结构来统筹画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湖北荆州博物馆藏战国中期的一幅“飞凤”刺绣(图5),利用凤与花草的形态组成长方形和菱形的复合结构,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既严肃又活泼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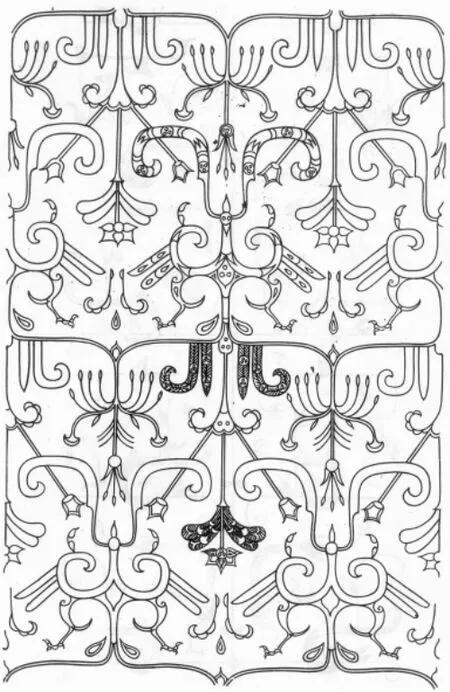
图5 飞凤纹绣Fig.5 Embroidery with flying phoenix
2 楚国刺绣几何纹的文化内涵
楚艺术中的抽象几何形态与自然形态一样,是客观事物在楚人意识中反映的结果。楚国刺绣图案中的菱形、方形、圆形、涡形、S形等抽象几何纹样,同样是客观事物在楚人意识中的反映。楚人运用几何形态来进行艺术创作,绝非是简单对于自然形态的概括,主要通过几何形的重复、重置、积聚、放射、渐变、对比等艺术手法,使主体动植物在变化丰富、运动感强烈的同时,又呈现出节奏感和秩序感。楚国刺绣图案中菱形、方形、圆形、涡形、S形等几何纹的出现,虽然是缘于楚人视觉审美和艺术创作的需要,但其自发性和稳定性显然并不完全是一种固定历史文化的审美经验模式,其特殊形态与地域古老文化的传承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文化高度概括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具有着深刻的人文内涵。
2.1 菱形纹与原始方形文化
菱形纹是由传统方形纹演变而来的,方形纹是原始方形文化的产物。原始的方形文化,包括土地观念,四时分割,以及由之产生的八分时空。据考古资料显示,生活在中国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几乎都发现和运用了方形,运用的范围包括在墓穴、房屋、灶坑、生产工具、陶器纹饰等诸多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人在墓穴、房屋、灶坑、生产工具等方面都只有方形而没有菱形,唯独在陶器纹饰上,才有菱形的表现。笔者仔细观察比较了诸多新石器时代陶器图案上的菱形纹,从最早“天圆地方”的组合体到单体的演变过程来看,原始人最初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只是在徒手表现方形时不那么精确罢了。后来由于视觉审美和艺术创作的需要,才有人刻意而为之,因而出现了菱形纹样(图6)。随后,这种菱形纹作为一种固定的经验模式自发而稳定地被保留下来。楚人对于菱形纹的特殊偏爱,是缘于楚人在艺术创作中着意追求一种飞舞灵动的自由生命气息。相对于方形来说,菱形纹在规律性的排列中更具动感和变化,因而与楚人的审美气息相统一。

图6 原始陶器中菱形纹的演变过程Fig.6 The evolution of diamond pattern in primitive pottery
另外,由于菱形纹具有方形的原始土地涵义,正在开疆拓土的楚人也常常利用其在象征性艺术中表达土地的概念,笔者前述的“一凤斗二龙一虎”图案就是象征尊凤的楚人对于东南崇龙的吴、越和西南崇虎的巴、蜀之间的兼并战争,用菱形几何结构代表疆土是非常恰当的,从而达到了形式与意义的统一。
2.2 圆形纹与传统“天圆地方”观念
在楚国刺绣图案中,圆形纹也有隐性和显性的2种形式。隐性圆形纹常常作为刺绣图案的布局框架,从而使动态多变的动植物纹样达到一种有序和谐的感觉。显性的圆形纹多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涵义,楚国刺绣图案中的圆形纹多与方形纹组合既是一种传统的“天圆地方”艺术构成的演绎,也同时表达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从楚国刺绣图案中几幅象征“天圆地方”的几何纹样来看,“天圆地方”的观念已突破了早期“盖天说”的宇宙观[5]。其象征上天的“圆”只是布局在方形外部的长廊中,或是大圆中饰一小圆,小圆中再饰3个小圆;或是饰一个太阳和北斗七星的组合而象征上天(图7)。
《系辞上传》将易数称之为“天地之数”,而将偶数作为地数、阴数;以 1、3、5、7、9 的奇数为天数、阳数,9是阳之极数。在楚国刺绣图案中,用以奇数的圆形几何纹来表示“上天”的概念应是毫无疑义的。

图7 “天圆地方”结构Fig.7 Structure of“round sky and square land”
2.3 涡形纹与楚人“水崇拜”
楚国刺绣图案的形态特征是动感,形式特征是曲线。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北荆州博物馆藏战国中期的一幅“一凤一龙相蟠”纹绣,大量的曲线极具动感,且多呈现涡形形态,其中的凤纹、龙纹、花草纹共身相蟠,几乎都用生动流畅的涡形曲线构成(图8)。楚人造物文化中的涡形纹来源于自身传统地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2个方面:稻作农业和纺织业。稻作农业是新石器时期由远古洪水崇拜向水文化转变的基础;而纺织业的纺轮文化,无疑是涡形纹起源的直接原因。

图8 一凤一龙相蟠纹绣Fig.8 Embroidery with a phoenix and a dragon coiling
楚人文化传统中的洪水崇拜历史久远,甚至于“就是人们从葫芦时代(采集)走向农耕时代的一次空前变革”的历史记忆”[6]。《洪水神话》是中国远古创世神话的主题之一,在南方各地稻作农耕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都有着内容相似的古老传说。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章的发现,证实了楚人传统文化中的水崇拜和对于水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之信仰。楚人的望祀只祀大川而不祀名山,《左传·哀公四年》记楚昭王说:“江、汉、雎、漳,楚之望也。”雎山和荆山虽然是楚国发祥之地,但楚人不祀。楚人嫌山爱水,这表明了以南方古老稻作农耕民族的苗蛮为主体的楚人传统水崇拜的古老思想。
在南方屈家岭文化遗址中,还可以看到原始纺织业的纺轮文化所带来的特征明显的涡形纹,其主要特征是呈现一种涡旋运动的状态。这种原始的涡形纹后来还与古老的“双鱼”纹结合,从而演变为一种经典的“太极纹样”。太极系指原始混沌之气,南方的道家认为它是派生万物的本源。道家的“太极图”,形象地表达了其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变化生成的哲理,同时又极具对立统一的形式美感。从图8还可以看到传统的涡形纹进一步衍化成一种以S形纹为主体的曲线回旋结构形态。这种造型结构以构成元素反向组合为特征,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逆、回旋反转的关系。楚国刺绣图案中的S形纹包含了艺术表现中最单纯的多样统一变化的实质,直接显示了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式表现的一致性,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审美意识水准和表现能力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从楚国刺绣图案中大量S形纹的运用可明显地看到,继商周“九宫格”的构图形式成熟之后,中国传统经典的“S形”构图及造型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
3 结语
楚国刺绣图案中几何纹的出现与其动物纹、植物纹一样,是历史和现实文化的集中反映。这种客观反映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出土刺绣品图案的艺术特点,绝大多数刺绣品的纹样的布局都是呈连续性的排列结构。总体来看,这种连续的排列是以规则的菱形、方形、圆形、涡形和S形等几何形为结构特征的。无论是显性的几何形还是隐性的几何形连续结构,都使得动感强烈的主体动植物纹样有序而统一,表现了很强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隐性的几何形连续结构,似乎刻意隐藏在主体的动植物纹样之间,以无代有,规统主纹。这样虚实、有无都成为了整体结构中的一部分,就如同《老子》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屋,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7]。把“有”和“无”都看成是实体的,重视了“无”的意义,从而引导了中国传统艺术自汉以后“计白当黑”“虚实相生”等艺术形式的出现。
[1]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76.JASPERS Karl.The Origin of History and Objectives[M].Xining:Qinghai People Press,2011:76.
[2]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601.SHEN Aifen.From the Path of Lapis to Silk Road[M].Ji'nan:Shandong Arts Press,2009:601.
[3]刘玉堂,张硕.长江流域服饰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148.LIU Yutang,ZHANG Shuo.Dress Cul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M].Wuhan:Hubei Education Press,2005:148.
[4]刘咏清.论楚国刺绣艺术的形式特征[J].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2012,27(4):161-162.LIU Yongqing.Characteristics of Chu embroidery art form[J].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ilk,2012,27(4):161-162.
[5]张劲松.中国史前符号与原始文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93.ZHANG Jinsong.Prehistoric Symbol with the Original Chinese Culture[M].Beijing:Beijing Yanshan Press,2001:93.
[6]林河.中国巫傩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493.LIN He.Chinese History of Wu Nuo[M].Guangzhou:Huacheng Press,2001:493.
[7]王秋.老子[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9:32.WANG Qiu.Lao Tzu[M].Harbin:Harbin Press,200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