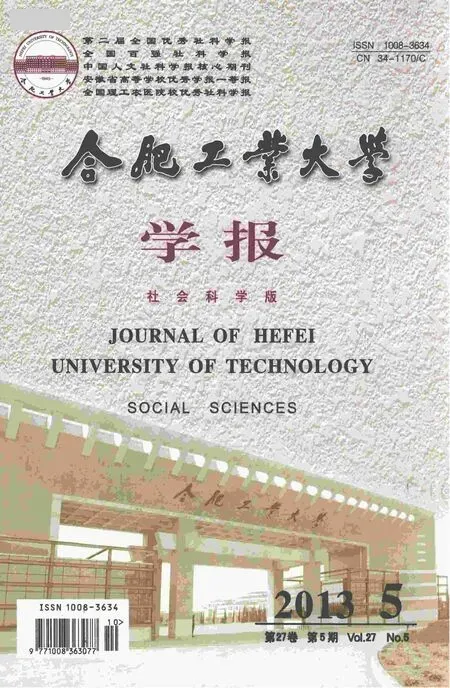图形-背景理论十年应用研究探析
邹智勇,程 平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0)
一、引 言
虽然早在约一个世纪以前,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ubin)就提出了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但其在国内语言学界真正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在这之前,国内关于该理论的著文比较鲜见。随着国内高校对语言学理论的重视和外国语言类课程的开设,该理论逐渐受到重视。按照Talmy对图形-背景理论的定义,图形和背景分别对应的都是较为具体的物体,其中图形代表的是移动的物体,而背景代表的是相对于并且作为图形参照的静态物体。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扩充,现在的图形和背景已经逐渐淡化了其具体物体的外衣,它们各自所代表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从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不论是看得见的实体,如房屋、人物,还是看不见的对象,如思想、意境,都可以分别对应该理论的图形和背景这两个核心内容。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解释力,不仅巩固了认知语言学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而且促进了相关领域(如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研究成果,为语言及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特别是当前该理论对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无疑促进了国人对经典的传承、理解和发展。本文依托中国知网(cnki.net),以“图形背景理论”为关键词对网站收录的文献展开主题检索,根据检索的数据结果,收集了2003-2012年十年间该网站收录的以“图形背景理论”为主题的文献,并按年份及文献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知网2003-2012图形-背景理论主题文献收录一览表
根据表中数据和内容归类,本文将对该理论在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理论发展背景进行阐述。
二、图形-背景理论与句法结构研究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十年间,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句子结构的分析最为流行,在全部收录文献中的比例最大,约为43%,涵盖了英语被动语态、倒装句、歧义句、if条件句、强调句、简单句、复合句、分裂句、关系分句以及动词、介词等。其中,代表性的有:华中科技大学外语系的梁丽和赵静在《图形/背景理论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图形/背景理论的特性,反映了语言在时间及空间上所遵循的规律”[1]116。作者在文中指出,图形和背景在空间上的防伪关系也可以推广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上来,具体说就是:在时间上的方位可变化的事件就是图形,具有相对性;背景就是在时间方位上相对固定的事件,具有参考性。图形-背景理论的突显特征被作者用于语言的“时间事件”结构分析,探讨了图形-背景理论在“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中的现实化,并得出“‘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是根据这一认知原则来组织的结论”[1]119。黄广平在《图形-背景理论下的英语被动句认知分析》中,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英语被动句的焦点凸显功能进行了阐释”,指出“在无施事被动句中,常式句中的施事图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现,使原本充当背景的受事移至句首而变为句子图形,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在有施事被动句中,受事置于句首,作为背景而成为认知的参照点,而原施事图形被移到了句末,成为句末的信息焦点即图形,从而获得了最佳突显效果”[2]。在《英语倒装句的图形-背景理论分析》一文中,文旭和刘先清认为倒装句作为常式句的变体,通过主语与补语的位置变换,从而改变了常式句中图形的位置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关注[3]。少数人甚至将其应用于汉语句子结构的分析,如杨芳芳的《汉语‘动词+处所宾语’结构的图形-背景理论阐释》[4]。除此之外,图形-背景理论的应用还涉及对日语倒装句的研究,如郭洁的《日语倒装句与图形背景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能力[5]。
图形-背景分离(figure-ground segregation)的观点是一个世纪前由丹麦心理学家Rubin首先提出来的,后来由完形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家)借鉴来研究知觉。他们认为,知觉场始终被分为图形与背景两部分。图形这一部分知觉场,是看上去有高度结构的、被知觉者注意的那一部分,而背景则是与图形相对的、细节模糊的、未分化的部分。人们观看某一客体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根据完形心理学家的观点,确定一个物体为图形应遵循“普雷格朗茨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agnanz),即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的物体、小的物体或运动的物体用作图形。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也可用于对语言结构的研究,例如,在表位置关系的句子The book is on the table中,“书”是图形,“桌子”是背景。这个例子也说明,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是由介词表达的位置关系;反过来说,空间介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图形-背景关系。正是由于像介词这样的语言表达式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因此,这一原则引起了认知语言学家的极大关注[6]163。
但是Langacker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用图形-背景这对术语,而用的是射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这对术语。如果某个客体处在相对于另一个客体的某个位置,或向后者移动,那么前者就叫射体,后者为界标。例如,在“足球在桌子下”这个句子中,“足球”是射体,“桌子”为界标。Brugman对英语介词over展开分析,Lakoff在Brugman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总结,运用射体-路标理论来解释over一词多义的现象,Goddard运用同样的方法对英语介词in进行了分析,英语的介词out,up和down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而被研究。上述射体-路标理论对英语介词的分析揭示了介词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介词各义项的这种统一的认知描写与早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后者认为介词的各个义项之间是不相关的[6]164。
我国汉语界学者曹先擢、苏培成在1999年编纂出版的《汉字形义分析词典》中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汉语的“上”。此外,王寅在《认知语言学》中借用国外学者对英语over和on的分析方法简要阐释了汉语中“出”字的语义引申机制[7]。
由此,图形-背景理论用于句子结构分析的尝试展开。从早期的对英语介词的分析,逐步转向对英语基本句型的分析,图形-背景理论的解释力逐渐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后发展为应用于汉语、日语乃至英汉基本句型结构的对比研究,其理论阐释能力可见一斑。
三、图形-背景理论与文本解读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08年国内才开始有学者将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中国诗歌或文本(如广告语)的研究和解读。虽然起步较晚,但此后每年都有此类的文献发表,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后来居上,以近28%的额度居第二位,仅次于句子结构分析的比例。
认知诗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认知诗学这一概念的是以色列人Reuven Tsur。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Tsur一直致力于将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1992年,Tsur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走向认知诗学理论》。这本著作被看作认知诗学研究的发轫之作。在这本著作中,Tsur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述:一是认知诗学以认知科学为工具,探究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如何影响和制约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二是认知诗学应在文学文本结构和所感效果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对这种联系进行系统的解释。1998年Tsur出版了另外一部认知诗学著作《诗歌韵律:结构与吟诵——认知诗学实证研究》。Tsur从格式塔的感知原理出发,指出韵律只有在吟诵中才能被感知,他运用George Miller 1956年提出的关于人类短时记忆中处理信息能力限制的经典论断证明了自己的韵律感知理论。
能够代表当前国外认知诗学研究现状的当属Peter Stockwell。Peter Stockwell的认知诗学研究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他关注文本解读,提出“Cognitive poetics is all about reading literature”[8]13(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重视文学阅读中的认知机制,强调应对特定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作信息处理分析,有别于其他许多不同的认知科学框架。他认为:“…cognitive poetics is essentially a way of thinking about literature rather than a framework in itself.”[8]14(认知诗学本质上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框架。)Stockwell于2002年出版了《认知诗学导论》一书;该书共分12章节;每章从认知语言学导出一个重要理论领域作为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对诗歌和小说等多种文学语篇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领域包括图形-背景理论、原型理论、认知指示语理论、认知语法理论、脚本和图式理论、话语世界和心理空间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寓指理论和语篇世界理论。
中国的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中国的诗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诗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欧洲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除了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亦反映社会文化,富于想象,语言具有节奏韵律,传统的诗歌常常对结构格式有一定要求。诗的特点在于除了可以阅读,亦宜于吟诵,又或者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表演。诗常透过特定的形象和技巧,让字词除了表面意义之外,蕴含另一层意义,或唤起情感共鸣。
传统的诗被称作韵文(verse),和散文(prose)不同之处在于有独特的结构、节奏和韵律。欧洲语言的字词本身有重轻音节的区别,因此西方的诗也特别着重字词的节奏(rhythm)。从希腊时代开始,不少的诗由轻重格(抑扬格,iamb)或重轻格(扬抑格,trochee)等的节拍(meter)组成。而在中国,由于中文的词语本身可以由两字或三字等组合而成,例如一句七字句的诗词常常可以分作“四、三”或“二、二、三”的词组。由于这种特性,每个词组之间念起来自然形成短的停顿,形成中国诗词独特的节奏感。
无论西方或中国的诗都着重字词的声韵,常常利用押韵将句子的结尾关联起来。汉语本身有平仄声调的分别,因此不少诗词对字句的声调有一定的格式要求,称为格律。传统诗对每一句的字节的数目,以及句子的数目都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利用整齐的句子或不规则的长短句来达致节奏上的美感,如西方的十四行诗,和中国的近体诗有五言绝句、七言律诗等格式。诗常常会利用字词、句子和段落的组合来赋予涵义的层次性和关联,亦会透过对仗、排比、叠字、叠句等技巧来表现美感。押韵和节奏除了营造音乐般的效果,亦可以达到联想和共鸣的功用。在内容上诗歌常常运用隐喻、譬喻与借喻等等手法来暗示一些文字以外的意义,透过对景物的描写来加强想象,甚至可以创造两个迥然相异的意象互相辉映,如运用歧义、象征、反讽等“诗的语言”的文体手法,使诗作遗留多样、自由的解释空间。
诗的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与Peter Stockwell所说的文本前景化的方式不谋而合,即为图形-背景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契机和切入点。Peter Stockwell在《认知诗学导论》一书的第二章节对图形-背景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文学批评观点中,前景化(foregrounding)现象与图形-背景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前景化指的是文学文本的某些结构或成分相比于其他部分更重要或是突显程度更高,因此也是注意力的焦点。文本的前景化可通过重复、调整句法结构、双关、头韵、隐喻等手段来实现。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焦点(attention)。作者认为:“Attention is selective rather than an undiscriminating blanket phenomenon.Certain elements in a visual field are selected for attention,and these will typically be the elements that are regarded as figures.”[8]18(焦点具有选择性,而不是一视同仁的。知觉场中的某些要素被选中作为焦点,被选中的要素通常视为图形。)“Reading a literary text is a dynamic experience,involving aprocess of renewing attention to create and follow the relations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8]19(阅读文学文本是一个动态的体验,是一个不断更新焦点来塑造和追随图形-背景关系的过程。)
很显然,这些手段都是建立在词或句子结构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而这些正是构成文本的基本要素,学者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也是基于文本的用词或句法结构来着手。从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词或句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早,这和该理论形成初期对英语介词的解读是紧密相关的。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宋代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宋代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唐代的诗人多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大臣个个是词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著名词人,女词人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使宋词得以佳篇迭出,影响久远。关于诗的成语有“诗情画意”、“诗以言志”、“诗中有画”、“画意诗情”等,单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诗和“情”、“画”、“志”、“意”是紧密联系的。中国学者将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对中国经典诗词的研究和解读,尝试以不同于本土的文本解读方式,探寻蕴藏其中的“情”、“画”、“志”、“意”。目前,国内图形-背景理论对诗词的解读集中在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名家作品上,以李白、杜甫、李清照、王维、张若虚等为代表。这种现象本身也和图形-背景理论相呼应,他们作为唐诗宋词的代表,其名作得到的关注更多,因而被选为研究的对象,即我们所说的图形。一如董璞玉在《图形-背景理论下的唐诗解读》中所说,图形-背景理论为分析、鉴赏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文章利用大量素材探讨了图形-背景理论的主要特征和图形-背景分离原则在格调高雅的中国唐诗中的应用。作者认为图形背景之间的突显关系、映衬和被映衬关系有利于分析唐诗中意象的图形背景关系,既为唐诗的表达增添光彩,同时有益于诗歌意境和内涵的深入理解[9]。在《图形-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的作用》一文中,梁丽和陈蕊从方位词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着手,对唐诗中图形-背景关系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形成产生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读者对经典诗词意境和氛围的理解和感知提供了新的视角[10]。高超则在《图形背景理论对<鸟鸣涧>意象解读》中,结合认知诗学理论,将图形-背景理论同中国诗歌具体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从认知角度深刻探讨了中国经典诗歌的内涵[11]。
四、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理论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多体现在汉语文本的英译研究,如颜色词的英译、隐喻的英译等,此外还涉及汉语复句的英译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或对比研究。图形-背景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可借鉴上述该理论对英汉句子结构的分析和诗词的解读来理解。从图形-背景理论对句子结构的分析我们知道,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体现在两种语言图形和背景的选择和位置关系上。Peter Stockwell认为:“…attention is paid to objects which are presented in topic position(first)in sentences…”[8]13(出现在主语位置或首要位置的对象受到关注(焦点))。
如汉语“截至目前,我读了三本书”翻译成英文,若要强调(突显)是“我”而不是“你”或“他/她”读了三本书,我们可译为I've read three books until now;若要突显“我”读的是“三本书”,而不是杂志或其他的读物,可译为Three books have been read by me until now。诸如此类,在汉语英译的实践过程中,借助图形-背景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准译文的中心和焦点,这样既可以避免生硬的对等翻译,又可以把握住原文的精要,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涵义。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的关系,正如郝霞在《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中的论述,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的相关性在于四个方面: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都是认知的;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都与意义相关;图形背景理论的主要概念,参照与对比,在翻译中也有涉及;翻译的过程与图形背景感知的过程有一定的相似性[12]。理清图形背景关系有助于译者更好的理解并传达原文的意思,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图形-背景理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对诗歌英译的影响。该理论对经典诗词的解读,涉及诗词意象的选取及转换,也就是图形和背景的转换。从上面我们知道,图形就是焦点,也就是英文句子的中心词。通过这种转换分析,可以帮助译者掌握句子成分的主次关系、句子成分位置的调整和句型结构的选择,新型的组合关系和结构对应于中国经典诗词言简意赅的意境,可以有效地表达原作的诗情画意。诗歌组成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诗人为表达其情感在诗中所营造出的意境,因此,对于诗歌翻译,能否将诗人的情感通过意境再现并尽量保持与原诗在形式上的对等尤为重要。在《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一文中,李蓉将图形-背景理论用于对中国古典诗歌不同译本的比较,对该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中国古典诗歌以其意象见长。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通过场景描述和意境的营造来表述诗人的情感,描述和营造的过程既是图形构建的过程,也是认知体验的过程。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诗的意义,译者就必须要整齐地把握诗中所突显的‘图形’和描述的‘背景’,从而更确切地理解作者想通过意象传达的情感,同时只有译者把诗中突显的‘图形’在译文中同样突显强调出来,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保持与原诗意义上的对等,再现原诗的意境,同时保持与原诗形式上的对等”[13]。此外,夏杨在《图形背景理论关照下的诗歌意象翻译》中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意象再现的成功与否对于诗歌翻译极为重要”,且“诗歌意象更具有图形背景特征”[14]。可以看到,图形-背景理论的应用有助于加深对原诗的理解,有益于原诗意象的再现,而这是传达诗人独特情感和感知的重要步骤。
图形-背景理论的应用十分广泛,大到诗词等文本,小到句子结构甚至介词、动词等。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很复杂,这也解释了近十年来关于该理论阐述的文献相对较少的现象,时至今日都没有单独的书籍对图形-背景理论进行详尽的研究和探讨,较为常见的则是在Peter Stockwell和王寅等的著作中有相关章节的介绍,内容也不甚多。尽管如此,图形-背景理论的解释力是显而易见的。
五、结束语
图形-背景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近十年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而被应用于各类研究。本文选取了近十年来有关图形-背景理论应用的文献,并分别从句法结构研究、文本解读以及翻译理论研究三个方面,阐述了该理论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发展现状和理论背景。从文中可以看出,图形-背景理论对句法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基本的英语句型几乎全部被覆盖,相比之下,鲜有学者尝试将其应用于其他语言的句法分析,这或许成为日后该理论应用的一个新的方向;另一方面,将图形-背景理论用于解读文本尤其是中国经典诗词的实践虽然起步稍晚,但已渐成趋势,这种应用前景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该理论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得益于其在句法结构和文本解读方面的发展,有可能成为日后重要的翻译批评方法。
正如该理论本身的特点,其应用也呈现一定的“图形”和“背景”选择,间接地反映学者理论研究的重点、发展趋势乃至文化价值的走向;同时也希望有助于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以期将该理论应用于新的领域的研究或解读。
[1]梁 丽,赵 静.图形/背景理论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16-119.
[2]黄广平.图形-背景理论下的英语被动句认知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52-53,60.
[3]文 旭,刘先清.英语倒装句的图形-背景论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12):438-443.
[4]杨芳芳.汉语“动词+处所宾语”结构的图形-背景理论阐述[D].长沙:中南大学,2012:5.
[5]郭 洁.日语倒装句与图形背景理论[D].长沙:湖南大学,2009:5.
[6]Ungerer F,Schmid H 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11:163,164,169.
[7]王 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187,190,218.
[8]Stockwell P.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13,14,18,19.
[9]董璞玉.图形-背景理论下的唐诗解读[J].绥化学院学报,2012,(3):126-128.
[10]梁 丽,陈 蕊.图形/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的作用[J].外国语,2008,(7):31-37.
[11]高 超.图形背景理论对《鸟鸣涧》意象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2):94.
[12]郝 霞.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2):261-262.
[13]李 蓉.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1,(7):69-70.
[14]夏 杨.图形背景理论关照下的诗歌意象翻译[J].陇东学院学报,2009,(3):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