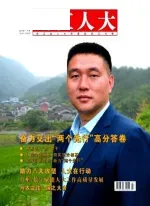我们圆桌会:共话城市治理
/朱狄敏 谢金金
我们圆桌会:共话城市治理
/朱狄敏 谢金金

围坐在圆桌前,“我们”是平等的个体,有着相同的话语权,讨论同一蓝天下的城市治理。张林摄
从两年前的默默无闻到今天成为杭州城市治理实践上的一个标志性品牌,《我们圆桌会》在城市的公共治理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平等、公开、多元的“圆桌”形式,一幅城市治理主体的“我们”图谱渐渐呈现。
小圆桌讨论大问题
解说:《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提交人大讨论。
应敏(市住保房管局):2007年搁置下来以后,我们没有停下来。
解说:城市里的老建筑对于杭州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潘一禾(浙江大学):自己的根。
魏英杰(评论员):把这个城市、把文化都能够串联起来了。
解说:现存老建筑的状况又是如何?
刘晓东(市规划局):我都有一种救火的感觉。
…………
“关注我们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城市,‘让我们生活得更好’!”2012年11月7日,《我们圆桌会》节目如期播出,话题是杭州市民十分关注的“保护老建筑究竟难在哪里?”
据悉,《我们圆桌会》是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的一档互动交流谈话类节目,于2010年12月20日首播,每期时长30分钟,每周一至周五20∶00—20∶30播出。该栏目秉承“民主促民生”的理念,就城市共同关注的话题,邀请专家、政府工作人员、市民等各界人士共聚一“桌”,对话、沟通、交流,达到理解与共赢。在话题上,注重新闻事件切入与社会现象分析相结合,注重把舆论热点中社会心理分析、情绪疏导与专家学者所关注的深层次思考和背景相结合。
截至2013年1月30日,《我们圆桌会》已播出500多期,涉及260多个城市公共话题的讨论,先后有3500多人次嘉宾走进演播室,成为杭州城市治理实践上的一个标志性品牌。
“创新执政,务实传播,公民参与,只要有心,大有可为。《我们圆桌会》搭建政府、媒体与公民平等沟通的平台,省会城市台成为理性传播的领跑者,接地气、有胆识、有诚意。媒体一小步,民主一大步。”2012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2012中国年度电视掌声·嘘声”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隆重举行,杭州台《我们圆桌会》获得了“年度掌声”。
近年来,杭州市政府积极改良民众参与的渠道与方式,扩大协商民主,推行“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我们圆桌会》这个谈话类节目正是这样一个民主民生互动平台。
“《我们圆桌会》通过城市治理理念的探讨,聚焦于城市共同体的精神塑造,注重城市在治理中的职能转型”,这是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对《我们圆桌会》定位的评价。浙江大学教授潘一禾表示,《我们圆桌会》搭建了政府与民众交流和沟通的公共平台,通过这一节目可以对社会生活、城市建设增进认识,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
可见,把“圆桌会”开到电视上,千家万户都来看,还能通过电话、网络发表意见,小圆桌变成了“一张城市治理的大圆桌”。
“我们”的角色定位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各个人群都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公开表达出来,互联网便成为了民意表达最方便的渠道,于是无数单个网民所发出的成千上万种声音导致参与的爆炸,由此造成了诸多误解的产生,问题的积累,分歧的形成。如何让民众有序、理性地表达,如何让政府与民众良性的互动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政府如何构建制度性民主协商对话的平台?如何在这个平台上推进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政府决策过程如何向老百姓开放、让老百姓参与?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圆桌会》是政府开放式决策的延伸,是开放式决策的常态化。坚持以知识与价值引领社会发展,以‘民主促民生’,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城市情怀。而它平等的交流、民主的对话本身就是正确价值的体现。”栏目总策划、杭州市政府研究室原主任王平说。
杭州市清晰地意识到,现代城市治理必须从城市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出发,塑造一种现代的群体认同观念——“我们”,才能真正树立城市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
那么“我们”又包括哪些人呢?从官方文件《关于创办交流谈话类电视栏目“我们圆桌会”实施方案》中似乎可以找到“我们”的表述:“我们圆桌会”体现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的理念。因此,“我们”就是杭州这一城市共同体的代名词,不管是官员、老百姓还是专家,都是“我们”中的一员,对解决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发展负有共同的责任。围坐在圆桌前,只有职业的区别,没有身份标签、没有高低顺序、没有等级高下,“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有着相同的话语权。
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在对该栏目分析报告中指出,《我们圆桌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对“协商治理”理念的一次有益尝试,它是一种具体的问题解决载体和意见沟通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城市理念,是城市治理理念与城市问题的解决途径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桌面上的平等沟通”与“桌面下的有效治理”两个层面的复合。

媒体一小步,民主一大步。《我们圆桌会》荣获2012“年度掌声”。项 辉 俞春江 摄

《我们圆桌会》已成为杭州“民主促民生”工程的一个标志性品牌。
实际上,栏目的定位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也经历了多番调整。如改进市民代表的产生机制以保障参与的多元性,不断为栏目挖掘现行制度资源等,尤其是2012年开始,栏目中逐渐出现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身影。
“这不仅开辟了一条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创新实践在力求与现有体制接轨”,王平对此做出了积极评价。其实,“圆桌会上的‘我们’只是这个城市共同体的一个缩影,杭州市的社会建设还需要更多的‘我们’。这要求政府搭建更多的互动平台,创造条件培育市民的公共精神与政治参与意识,从而形成具有独立性和差异性又拥有平等对话权的‘我们’。”王平说。
“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市民的参与既是民主的体现,又是政府优化治理的一个很好的资源。通过城市治理过程中所有层面的公民的有序参与,最终形成城市对人生活本身的回归。”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韩福国在栏目的分析报告中写下了这番评语。
对话的力量
圆桌会作为党政机关借助媒体开展民主民生互动的平台,给予了“我们”围绕城市治理议题进行平等、理性对话和交流的渠道,成为党政机关决策的重要参照,其成效逐渐显现。
——对话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效能。杭州市积极创设各种平台让杭州市民参与对话,在圆桌会上,民众可以就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直接对话职能部门领导,同时通过讨论和互动,专家、行业企业和市民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得以汇集。
“过去由于城市公共治理上缺乏良好顺畅的沟通渠道,一些误解与分歧难以消弭。现在,利用‘圆桌’沟通打破了隔膜”,王平认为,“圆桌”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圆桌会上提到的“蔬菜直通车”、“公交车接驳地铁方案”、“交通拥堵治理”等建议已被相关职能部门接受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对话有利于培养公共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追求“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人们的主动参与性非常弱,缺乏“公共性”的价值诉求。《我们圆桌会》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环,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而这也正是评价政府治理良莠的标准之一。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余逊达教授认为,“最好的治理必须是最有助于培育市民精神,最有助于提升公民参与能力的,杭州人民的公共精神的培育是否达到最佳的状态,杭州人民的知识、认知水平是否得到最有效的提升是杭州市是否得到最好治理的两个尺度”。
潘一禾教授则寄希望于圆桌会“形成一股正面的引导力量,以我们的主动意愿唤醒那些沉默者”。如今圆桌会正成为民众对话党政机关、实现民主权利的平台,民众的声音开始变得强有力,积极性也得到极大的提升,每个人都平等的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
——对话有利于民众情绪的释放。对话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形态来说都是必须的。“哲学最高的水平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商谈”,当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认为该栏目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对话。缺乏对话,民众与政府之间就容易形成误解。圆桌会的目的也是为引导公众相互理解出发,就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建设性的交流互动,关注诉求,反映民意,疏导情绪、引导情绪、凝聚人心,达到城市各个生活群体之间,尤其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行为互动和信息交流,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即便达不 成共识,也要相互的理解或者相互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地释放民众的情绪。
对话背后的社会力量
“杭州很多经验的推动力量都来自于社会,治理的动力也来自于社会”,林尚立评价,正是社会力量的推进促使杭州市政府加快了调整角色和定位。
经验表明,公众参与程度的高低与该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等有着很强的正关联性。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经济总量和产值也一直处于增长状态,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高新技术发展迅速。福布斯在发布“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时以这样的口吻报道杭州,“让杭州进入世界视线的不仅仅是西湖,更多的时候是民营企业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开始注重对个人及纳税人利益的维护以及对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渴求。物质上的富裕有利于民众积累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经验。正如浙江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叶国文所指出的,“杭州市的民主实践,运用了复合民主这一实践形态,以民主形式创造发展,同时又以发展促进民主建设。而这种模式与杭州市的经济条件、民众文化、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不无关联。”
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方式,体现了社会文明的程度。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越广泛、越平等、越具有相互约束力,民主的理念才能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这些特征在杭州社会参与进程中得以证实。杭州市党委政府在实践中提炼了三点工作方针“要不要干由百姓定,怎么干由百姓选,干的好坏由百姓评”,从而让民众有序参与城市公共治理。
“今天,几乎每一件关系市民社会生活的重大事项,杭州市民都有民主选择的权利”。据悉,杭州开放式决策的深化,市民参与、选择城市发展的热情得到激发,政府决策更加科学、人性化,市民当家做主已成为杭州市民的一种生活文明。
“这些都是在缺乏现成经验、缺乏参照的条件下取得的进展”,王平认为,“凡是创新和探索,其实都是不完善的,还需要回到进一步的实践中去”。所以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落实具有持续可行性并非单靠民众的参与热情,还需更为细致的民主政治理论建设以及悉心推进公众参与实践的智慧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