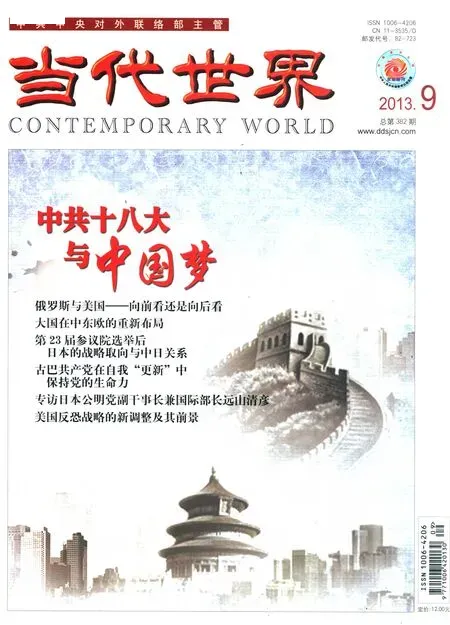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印度国大党的发展
■ 宋丽萍/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政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体系,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等都是政党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的社会现实,也是政党自我调适,实现健康发展的推动力,这对成立已有125年历史的印度国大党来说更是如此。印度政治社会的变化与国大党的沉浮息息相关。因此,将国大党的发展置于印度政治生态下予以考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其沉浮的历程及原因,同时也可以加深对印度民主制度、政党政治和百年来印度社会变迁的认识。
一、国大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
独立前,印度是英属殖民地的一部分,国家独立是印度各阶层的共同奋斗目标。虽然它们的主张不尽相同,但由于有共同的外部斗争对象,印度民众能够保持相对统一,不分种姓、宗教、阶级都团结在国大党旗帜之下。独立后,国大党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主张的多元化与公民政治意识的增强
独立后,国大党领导人把世俗主义和民主政治作为建国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公正、经济平等经济政策。印度政治精英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主导,这些人一般都有西方教育背景,眼界相对开阔。但20世纪60年代后,印度政治精英结构发生变化,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中富裕起来的农民日益活跃在印度政治舞台。这批农业精英在国内接受教育,乡土观念浓厚,对世俗主义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认识缺乏全民族的视野,积极维护地方利益。
随着社会集团分化的加剧,不同政治组织的频繁建立,印度公民的政治意识也日益增强,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89年以后。1989—2004年是印度政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阶段3M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中心议题,三者代表政治集团意识对抗的三种意见,以三者为中心,环境整治、妇女等政治议题也逐渐进入政治议程之内。传统单向度的国大党一统或者左右分野的意识形态对抗被不同层面具体问题的对抗所取代。这也使政治发展更接近民众,民众参政意识日益提高。在后国大党时代,低等种姓和低等阶级、妇女、部落民参政热情高涨,而作为印度政治发展主流和引导者的传统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则有所降低。
(二)社会分化加剧,矛盾冲突增多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宗教、种姓、语言众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各集团之间利益争夺日益公开化,对抗也越来越激烈。在这些社会集团中,对国大党非常重要的社会集团有表列种姓、其他落后种姓和阶级、穆斯林集团,它们都是国大党的传统支持基础,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集团慢慢从国大党的支持基础中剥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表列种姓一直是国大党的忠实支持者。国大党政府改善表列种姓集团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举措都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针对原贱民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引发其对国大党政策的不满,并建立贱民政党。其他落后阶级则是因为经济地位提高,在政治上向高等种姓发起挑战。1990年,维·普·辛格政府决定实行曼达尔报告。此令一下,随即引发了印度社会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的两极分化。正如《经济和政治周刊》所说,“整个印度教高种姓突然变得坚如磐石,原教旨主义的和世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甘地主义的、城市的和乡村的高种姓,都从来没有过那样团结一致”。低等种姓政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成为一些重要邦的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成员。种姓政治的发展对国大党的打击是致命的:其他落后阶级的政党和表列种姓政党将低等种姓和表列种姓从国大党的社会基础中拉走了;印度人民党则夺走了高等种姓对国大党的支持。这样,国大党作为全民政党的社会基础大大萎缩了。
国大党另一倚重的社会集团穆斯林也因为国大党公开利用教派主义和印度政治中教派主义倾向的增强而逐步走向极端化。20世纪60年代开始,穆斯林政治组织日益活跃。80年代初,国大党为了选举利益,公开利用教派主义情绪,此举引发穆斯林集团的分化,尤其是沙·巴诺案件和阿约迪亚寺庙之争促使印度穆斯林重新思考国大党保护者的角色。他们已不再单纯依靠国大党的力量,而是寻找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全国性世俗政党和地方性世俗政党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保护集团利益。
以种姓和宗教为单元所造成的社会分化,瓦解了国大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边缘集团提供了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机会,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加剧了印度政党政治的碎片化。
(三)地方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联邦政治的地方化
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国大党逐步失去了对政局的掌控,开始是邦政权,接着在联邦政权上失守。与此相对应,地方政党日益活跃。地方政党的兴起对国大党社会基础的巩固和扩张却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为地方政党的兴起分割了国大党的全民社会基础。对国大党而言,从独立运动以来,它一直以印度民族代表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反对以种姓、宗教等社会要素分割印度民族。无论在选举政治中,还是联合政治中,国大党都不像其他政党那样公开利用地方因素和感情,通常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社会动员方式当然无法与地方政党赤裸裸利用地方感情开发政治资源的竞争方式相抗衡。
1989年之后,联邦政权进入联合政治时代,政治竞争结构也发生改变。在1989年之前,联邦政治始终是印度政治发展的主流,控制着印度政治发展方向。但1989年之后,邦政治成为政治选举和政治对抗的主要领域,由于不同邦在社会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分殊,选举竞争已不再是全国范围内的竞争,而只不过是邦选举结果的聚合,1998和1999年全国大选进一步加剧了联邦政治地方化这一趋势,邦政治成为决定联邦选举政治和政党命运的有效竞争单元。每届内阁总理都试图建立新的政治操作空间以扭转这一趋势,维·普·辛格政府提出曼达尔报告,力图吸引其他落后阶级的支持,拉奥政府抛出经济改革的议题,力图以解决经济问题为自己加分,然而因为经济改革政策和效果的时间差而下台。瓦杰帕伊以核试验重振国威,提振士气,然而最终也避免不了下台的命运,他们都无法成为英·甘地那样能够操控民意的领袖。
(四)政党政治的变化与政党意识形态主张的模糊化
在1989年之前,除了国大党是全民政党外,其他政党基本持一种意识形态而排斥其他意识形态。但20世纪90年代后,每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主张上日渐模糊,因为经济改革的原因,目前各个政党都在谈论社会公正,多数派和经济自由化。如印度人民党不再反对私有化,而主张积极的私有化。印共(马)虽然反对自由化,但在其执政的邦也执行自由化政策。贱民也不只是谈论保留制,还强调种姓平等。政党政治领域主要游戏者开始变得界限模糊,政治责任感缺失。原来的边缘集团进入核心领域后并不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一些敏感政治议题反而被束之高阁,动荡并没有带来政治转型。不同政党所卖的都是同样的商品,这对品牌商标的忠诚支持者是一个打击,但在一定程度却增加了国大党这样持多元主张的政党的政治回旋余地。
(五)威权政治模式向绩效模式的转变
随着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主张上差异的日渐模糊,民众对政党的评判越来越集中在绩效上而不是口号或意识形态差异上,这对于在联邦政治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而言,自然有利于国大党。因为印度人民党的上台主要的依赖力量是国民志愿团,而国民志愿团是一个认同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机构,而对于政治动员的认同度非常之低,失去国民志愿团的支持,印度人民党的力量将会大大削弱。而对于国大党来说,因为其多元主义的主张,并不集中特定社会集团,而可以从中渔利。
二、国大党的应对
政党的首要目标是夺取政权,面对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国大党从政治战略和自身建设上做出积极回应。
(一)在政治战略上,国大党依据形势变化,调整政党决策模式、动员模式和选举战略
其一,政党决策从合意模式转变为威权模式。在尼赫鲁时期,国大党的决策机制是多年以来形成的一致同意模式。英·甘地并不具备尼赫鲁的领袖气质,尼赫鲁去世后,受到辛迪加派的控制,她采取手段切断了这些实力派人物的权力来源,然后推行与民众单一交流的模式,国大党各级人员任命都由她来决定,甚至小到区一级的领导都要由国大党中央任命。这一趋势在其后的拉·甘地和拉奥时期都没有发生改变,二人也同时兼任国大党主席和国家总理。威权模式的另一个表现是国大党领导选择模式的家族化。1975年的桑贾伊和1980年的拉·甘地都是以火箭般的速度进入国大党领导机构,担任要职。现在国大党力推的拉胡尔也是尼赫鲁家族的接班人。在社会利益主张多元化的条件下,只靠个人是无法拯救一个政党的,因此,国大党如果要在政治上有大的发展,必须摆脱家族政治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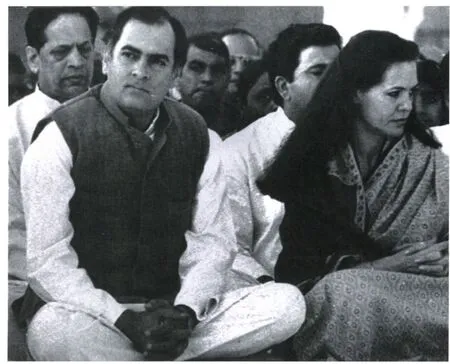
1986年10月2日,印度总理、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和夫人索尼娅·甘地在新德里参加圣雄甘地诞辰117周年的纪念活动。索尼娅·甘地于1998年3月14日被推举为印度国大党主席。
其二,国大党政治动员模式的转变。英·甘地在操纵政党的同时,也在选举动员方面大展身手。1971年选举,她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提出消除贫困的口号,与此同时,她也令联邦和邦选举同时举行,这样地方的选举也全部由国大党中央主导。1980年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时迈出了更危险的一步,弃世俗主义政策于不顾,公开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1982年初,英·甘地在阿吉米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印度教“达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1983年,在比旺迪,她非但没有谴责湿婆军领导煽动暴力的行为,反而要求印度的少数派学会适应环境。国大党的政治动员走上了另一条轨道。拉·甘地的上台并没有过多改变国大党的这一政策。1986年,国大党政府通过了《穆斯林妇女(离婚权利保护)法案》,规定离婚穆斯林妇女在没有任何亲属和生活来源的情况下由各邦瓦克夫集团负责其生活费。这一法案实质上维护了穆斯林个人法的现状。巴布里清真寺也是在拉·甘地执政时期开放的。
其三,选举战略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选前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6年以来印度政治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国大党却没有根据社会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依然相信只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参选即可达到半数以上的多数席位,而不采取建立选举前联盟的政策,后来的结果证明,国大党并没有得到民众如此的青睐。当国大党意识到单独执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时,不得不改变选举策略,开始与地方政党联合,例如在比哈尔邦、安德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泰米尔纳杜邦。2003年年底,国大党甚至抛弃了对中央权力分享的反对而开始致力于选前联盟。
(二)在自身建设上,国大党也历经起起伏伏
其一,在组织建设方面,国大党从最初的民主机制转向威权体制。英·甘地取消了党内民主机制,地方领导的选择都由英·甘地来控制,她挑选地方领导的标准是服从自己。这样导致一批地方实力派人物退出国大党,另组新党。与此同时,他们也带走了国大党的地方社会基础。拉吉夫在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时候,力图恢复政党内部的民主运作,宣布1986年举行党内选举。但是,拉·甘地担心党内选举可能出现伪造选票,不可能达到净化党组织的目的,而且实力派人物主导选举,可能导致自己在党内地位的下降。因此党内选举被无限期拖延,拉·甘地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也被束之高阁。1987年,国大党在一些邦的选举中落败,拉吉夫遂采取权宜之计,加强国大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依靠青年国大党为自己服务,但这些措施导致党内一些宗派领导的不满,一些国大党成员加入到反对党,宗派斗争削弱了国大党的力量。
拉奥就任国大党主席后,因为并非来自尼赫鲁家族,没有领导魅力的光环,而且其政治基础主要在安得拉邦,因此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均想取代拉奥。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拉奥沿袭了英·甘地以来的政党建设策略。在就职后,拉奥曾宣布举行党内选举,重新恢复国大党的民主作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空口许诺。1991年人民院选举后,拉奥认为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势力过于强大,不易控制,因而利用自己国大党主席的职位,以工作委员会内部缺少妇女、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成员为借口,强迫其中的一半成员辞职,这些成员中包括来自马哈拉施特拉的帕瓦尔和来自中央邦的阿琼·辛格,他们都是国大党内的实力派人物。之后,拉奥拒绝建立国大党议会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而依靠实力较弱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和邦国大党委员会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拉奥的这些措施非但不能加强国大党内部的凝聚力,反而使党内更多人对他非常不满,国大党内部的民主进程和凝聚力在继续下滑。组织建设依旧是国大党的一个软肋。
其二,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回归多元主义。国大党是全民政党,其宗旨是为印度人民谋求福利,以和平手段建立一个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所有人机会均等,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但是在政党发展过程中也有曲折。尼赫鲁是世俗政策的创始人和坚定的支持者。但其女儿英·甘地却以权力为导向, 20世纪80年代初公开利用教派主义情绪,损害了政党的世俗主义主张。拉·甘地和拉奥时期试图继续走英·甘地的路线,但是,教派主义开发并没有带来实际的选举利益,反而替印度人民党搭桥。1998年后国大党又重新强调坚持多元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2004年选举中,农业集团在击败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大党在执政后,强调增加农村信贷,以缓解农民不满,但效果有限。对一个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民众的期望,尤其是现今社会,资源有限,所以生存安全是所有社会集团最优先考虑的方面,如果哪个政党无法为民众寻找就业机会,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那么风向会立即转变。如今国大党缺少的恰恰是有能力、有责任感、有活力的领导。
三、小结
政党的存在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就国大党而言,印度特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铺就了国大党调适与发展的道路。然而,国大党发展的历程也反过来影响印度政治发展的方向与轨迹,而且,后者对印度政治发展的影响甚至大于前者,这反映了第三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成熟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随着贱民、其他低等阶级、表列部落等边缘人口成为活跃的参政力量,政治与社会两大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印度政治发展也将逐步走向成熟。
由于印度社会多元性和复杂性,按照语言、宗教、种姓、部落等基本单元形成的区隔使政治结盟成为重要的选战手段,以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为首的选战联盟鼎立的局面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大党复兴的路还很长,它必须在政治战略方面作出调整,紧紧依靠家族政治是无法挽救国大党的。
就国大党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关系而言,其必须尊重自己赖以生存的客观社会政治系统。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一味以强权手段调整政党的政治战略,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例如,国大党不顾印度多元社会的性质,不尊重少数集团,迎合教派主义的主张,最终导致落后种姓、表列种、穆斯林集团等传统支持基础的背离。
[1] 3M 即曼达尔(mandar)、寺庙(mandir)和市场(market)。
[2] 印度教有四个主要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除上述外,在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传统上称他们为“阿丘得”,即不可接触的“贱民”,有的也称其为第五种姓,今天称之为“哈里真”或“表列种姓”。
[3] 高鲲.印度的保留政策和种姓矛盾.南亚研究, 1992(2). 6.
[4] Prakashi Chandra, Changing Dimensions of the Communal Politics in India, Delhi, 1999: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