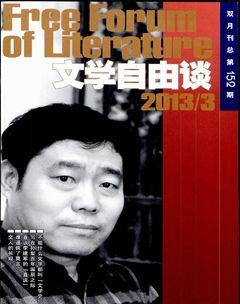兵站内的灵魂厮杀
王志红
小说家严歌苓,是具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她写出许多直面人生、直击心灵的小说。她以独特的才华,塑造了形象各异、蕴含丰富的女性形象。那些鲜活而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遭遇。她们情感细腻、个性鲜明,对生活中的困窘与挤压呈现出柔韧而又独特的姿态。
读严歌苓的小说,总会让人发现一些惊喜。这些惊喜来源于她作品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诗意、唯美的理想追求。她的小说,没有机械的、严丝合缝的复制现实,而是在精练而又确凿的现实基础之上,对人物和事件展开理性、丰富、诗意而又唯美的想象,并使这些想象的情境悄然且自信地抵达了读者的内心深处。《少女小鱼》、《白蛇》是这样,《天浴》、《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是这样,《谁家有女初长成》更是这样。
在严歌苓的众多小说中,《谁家有女初长成》是很独特的一篇。之所以说它独特,是主人公再也不是作者身边发生的事情,再也找不到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融合间的碰撞,总之是离她的生活很远的一篇。然而,远并不意味着模糊和冷漠。相反,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倾注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她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位作家所肩负的道义和使命。
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中国西部偏远地区发生的故事。出生在四川黄桷坪的巧巧,是个刚刚二十岁的山区姑娘。她在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中孕育着一个愿望,那就是想让自己变成能在流水线上班的城里人。“她的一个儿时朋友在深圳做流水线上的女工说,看看那地方,死也闭眼了。”就是这个的小小的愿望,使她在奔向梦想时,遭遇了人贩子曾娘、潘富强、陈国栋等人的数次欺骗、拐卖。之后,她不得不沦为养路工大宏和他的傻兄弟的共同财产。两个能笑成一副面孔的兄弟,将手中的存款凑在一起,合计一万元,就从人贩子那里把巧巧买到手。从此,贫瘠而空旷生活空间里,又多了一个比大宏二宏更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人。当软弱、无奈的巧巧再也不甘命运的摆布,对两个养路工揭露、指控、咒骂都无济于事之后,她手起刀落,结果了两兄弟的性命,她也因而铸成了杀身之祸。这之后,她逃到一个兵站,在这个特殊的空间里,与官兵们度过了一生中惶惑不安却又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日子。可惜好景实在短暂,杀人的事实,使她那一段“汪着水”的青春,不得不画上句号。
这个故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情节,有了好的、真实的情节,不一定就能编织出荡气回肠的故事。然而,严歌苓是个例外。她不仅可以组织出比现实还真实的情节,而且还对结构故事有着超常的驾驭能力。她小说中浪漫色彩以及理想的虚构能力使她的作品始终散发着人性的、博爱的艺术魅力。
在这篇小说中,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对巧巧命运的设计安排上。巧巧杀人后,作者既没有让她逃回家中,也没让她死于被拐卖的过程中,而是将她引入兵站,与此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审美,巧妙的构思,精彩的铺叙,融入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就因为这安排,作品没有像凶杀、暴力类小说那样流于平庸,有着悲惨遭遇的主人公,也因而沐浴着善与爱的光芒。由此,官兵们面对巧巧身世及遭遇,也展开了心灵间的搏斗与厮杀。
当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巧巧置于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兵蛋子”中间时,空气中即刻像撒入了化学试剂,那些兵们言谈举止都出现兴奋的失常。这些情节的铺叙让官兵们从一点一滴的对话、一言一行的动作中感觉到巧巧的平凡与美好,同时也为巧巧的离开给他们带来的“不忍”和“震动”做了很好的铺垫。
作者精心选择了三位军人,从三个不同角度抒写了作者对花一样生命的关注。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金鉴,对巧巧的表现虽然矜持冷淡,但也发现了她的“窈窕的丰腴、美丽的愚蠢”,这令他恶心,但也令他心动。当他得知巧巧家乡的男孩女孩都早早辍学了,就“显出操心和轻微的愤怒”,好像文盲率在大幅回升,大部分的责任在于“巧巧”们的不明事理而显现出的无知选择。而大批失学的孩子跟大人上山伐木,则会引起水土流失,气候恶变。作者通过金鉴与巧巧的对话,展示了一个“学生气”的军官对无法扭转的丑恶现实的“愤世嫉俗、救度天下的书呆子式的胸怀”,当他得知巧巧来兵站的真正缘由后,他那冷若冰霜的脸柔和下来,说,你该早些告诉我,我们军人有责任保护你这样的受害者。
爱读文学杂志的小回子,先是对巧巧感到沉痛的失望,哪一点儿也没有文学杂志上写的美好,可后来却把巧巧看成是“每一秒都增添一分美丽的年轻女人”。最讲实惠的刘合欢,左一声右一声地“小潘儿”一叫,就把巧巧叫成了兵站里的主角。她可以把两个手插在裤兜里走向舞台的中心——篮球场,那些兵们的“球艺马上有了长进”,并且,跑起来的动作“又添了层造作的潇洒”。她的一个眼神儿,会让那些兵们快乐,也可让他们感到不适,更会让小回子的脸红到脚后跟,在心里一遍一遍为一个爱情故事开头。之后,“他的感动在他心里形成一串串泉涌般的句子”。一个小小的篮球场成了她有生以来最辉煌的舞台,她本可以那么婀娜多姿。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巧巧帮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帮他们拾柴摘菜理发,她忙碌的身影给官兵们带来无尽的快乐。作者将她主人公如花的岁月恢复了本来面目,她像湿润的空气,甘甜的泉水,温暖的阳光,肥沃的土地。那些兵们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很容易地让自己感到满足,觉得对生活应该充满希望,随便哪一个都会因她的存在而焕发活力和生机。
官兵们灵魂里的厮杀,是通缉令被兵站里的官兵知晓后发生的。
作者把巧巧带入兵站后,使官兵们对这个南方女子产生了无限向往的美好,所以,当巧巧“杀人”事件暴露,小回子先是吃惊得眼睛发直,体温持续下降,脸色异常,继而隐藏了“通缉令”,虽然他知道隐藏的后果,但他无法相信那是真的。几天之后又与司务长刘合欢数次吞吞吐吐,最终将“通缉令”交给刘合欢。他们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巧巧会是杀人犯,但在事实面前又无法改变它的残酷。而刘合欢见到通缉令上的照片后,先是反弹,继而“吃力地读着一个个字,像是错了天大一笔账”,他为这样一个好看的女孩所遭的罪孽和以罪孽的方式回报而心碎。之后,他忙着和同乡联络车辆,以图协助巧巧再次出逃,又找金鉴为巧巧的事求情、争吵,说“你看看这小丫头,能天生是个杀人犯?她是给糟蹋得快成渣儿的时候才不得不反抗的”,但金鉴还是坚持这事件合情而不合理。他坚持交到法庭去讲,毕竟杀两个人不是失手之举。之后他口头儿答应刘合欢不过问怎样将巧巧放生,却又同时搞了突然袭击,安排文书小回子在凌晨四点,兵们还在睡梦中,便把巧巧“送走”。这让小回子“突然仇恨金鉴,这个书生长官竟这么阴毒!”。刘合欢有他自己的粗鲁和仗义,当得知金鉴将他精心替巧巧安排的出逃计划毁于一旦,他只能用拳头回击他。作者将刘合欢掏心掏肺式的表达,描述成兄长式的护佑。
作者通过对三个军人形象的虚构,描述了军人对柔弱女子特有的护佑情怀,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军人是保家卫国的,但“他们”却目送着属于自己职责保护下的如花的生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无奈地消失,然而却又束手无策。面对生活中的被压迫者、被蹂躏者,作者骨子里流淌的那股军人的血液在汹涌地奔腾着。读者可以在严歌苓貌似冷静的文字下面,感受到她对人世间的罪恶是怎样的血脉喷张。可是,她手中却仅仅有一支笔,纵然是一支生花妙笔也没有能力去搭救众多的巧巧们。所以,她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兵站,在那里对她们给予了真诚的关照和剖析。然而,这观照和剖析却使读者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如暮鼓晨钟,回响不已。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用优美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将真实的写实与理想的虚构相互融合、相互依托,既合情合理又游刃有余。作者在写实与虚构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情感与理智之间,用诗意盎然的文字书写出情节、人物、故事彼此相生,相互和谐的旋律。它真实而又委婉,既不不空洞,也不做作,如歌咏般使她的理想或曰梦想的情境完美地抵达了读者的心灵深处。书中结尾部分,作为军人的金鉴及他的士兵们,在巧巧逝去之后的种种表现如空谷足音、扣人心弦,使作品在展示作者博大的关注视野的同时,引领人感受到深沉隽永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