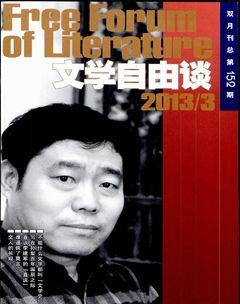春天,想起两位诗人
严英秀
刚杰·索木东:“我只能用一种方式守望甘南”
2013年春节,吉祥水蛇藏历新年,诗人刚杰·索木东携着年轻的妻子和一天天淘气起来的稚子,回到了他的家乡——藏王故里,洮砚之乡卓尼。当他暂别生活了二十年的繁华城市,一路向南,当遥远的甘南之南在车窗外渐次绽开,刚杰·索木东的脸上心上该是怎样的表情?衣锦还乡的世俗自豪,是否使他格外地关注到了那些在寒冷的天气里捧着书本憧憬着远方的少年?他们多么像他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十六岁。或者,轻薄的成就感转瞬就被另一种更有力的情感消融?那是巨大的幸福和悲怆,它们横亘在故土的每一缕空气中,只要他走来,每次他走来,它们便倾巢出动,候在他必经的回乡路上:“一条悠长的路通向甘南,亘古的风雪塞满我的温暖故乡啊,甘南一堆篝火燃起一匹马的寂寞贴紧热身子是你痛心的贫穷……”
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之外。一直以来,关于刚杰·索木东和他的诗和他的甘南,我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他和它们离我太近,亲缘缠杂的生活使我无法退居到一定的距离外,保持一个恰如其分的审美姿态。
二十年前,刚杰·索木东在跨进大学校门的同时,就开始了他的汉语诗歌创作。虽然他读的是数学专业,虽然数学被称为“最迷人的艺术”,但显然,奥妙无穷的演算和推理并不能有效安妥一个离乡少年的狂躁悒郁,心灵的出口无可选择地指向了诗歌。这被当时的老师同学所讶异的专业错位,或者说不务正业,其实究其细里是再自然平常不过的事,藏民族有发达的抒情传统,民间生活中充斥着古老的谚语歌赋,许多人开口即诵,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大多从诗歌起步。刚杰·索木东开始以诗歌的方式述说时,身前身后已堆集了太多的同族诗人。他和他们并无异样,在一天天变着模样的城市里,浪迹于意念中的故乡,那离别半步即成天涯的草原。从那个时候开始,刚杰·索木东一路写到了今天。今天,那些青春作伴的身影已渐次相忘于江湖,诗人和诗歌共同告别了曾葱茏无比曾辉煌无比的好年华——但诗歌,依然是眉头的结胸口的疼,但歌咏故乡依然还是需要用剩下的日子慢慢去面对的事。诗人刚杰·索木东,在经历了生活中的太多之后,比以往更加确信,没有什么途径比诗歌更能抵达故乡,没有什么词语比故乡更适合安眠在诗歌中。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这是生活在草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诗人海子偶尔路经草原时留下的诗句,但这分明是刚杰·索木东的切肤之痛。广袤的甘南草原,美丽如画的藏家山水,在现下铺天盖地的旅游宣传里,它是美轮美奂的图景,是关于各种奇异浪漫的风情、优美淳朴的民俗的演示,是许多个“最后一片净土”中的其中之一。但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儿女眼里心里,它其实是立在村口地头悄悄抹泪的白发亲娘,她的胸口不再是你恬然安居的地方,她注定要看着你远去,但你注定永难割舍。是的,刚杰·索木东所有的诗章只是在轻轻诉说:故乡是甘南。而他,在远离它的地方,“坚持用一种方式”,“坚持用一种心情”,“坚持用一种姿势”,“完成着一生的眷恋”。
刚杰·索木东的故乡,亦是我的故乡。甘南从梦中走过,月光诗一样铺满金子般的草原。但即便是在梦中,我们也忘不了,甘南并非乐土,它有多么美丽博大,就有多么荒凉贫瘠,它有多么温暖悠扬,就有多么忧伤局促。它在夏日里捧出世间最美的海子,又在初秋的第一场风雪里就让羊群和草地在凛冽的肆虐中褪尽了颜色,它诞生了传奇和史诗的那些英雄部落,如今在城镇化的潦草慌乱中,呈现着尴尬苍白的命运。这样的故乡,刚杰·索木东在他乡的忙碌奔波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回望,他叩问自己:“走出故里我就能摆脱困苦吗甘南,遥望经年的故乡贫穷苦难夜夜撕裂我流血的心愿……”多风雪的甘南,“羊皮袄捂不热的甘南”,总是不经意间就错乱了诗人的天气,“秋末,对一场大雪的虚构其实是对故土和乡愁的虚构那些在秋雨中缺少狗吠和鸟鸣的村落那些在秋雨中散去炊烟和歌声的寨子此刻,向乡而望的眸子里过冬的念想还会是回归故里的匆匆脚步吗?”
“故乡是甘南”,是刚杰·索木东的创作母题,这使得他的诗歌很容易被划归到乡愁诗的谱系。这是一个无比强大久远的谱系。从最初的《诗经》中“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的乐句开始,乡愁便成了再无断绝、历久弥新的诗歌主题,屈原说:“陟陞皇之赫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李白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贺知章说:“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马致远说:“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当代诗歌中,郭沫若有《黄浦江口》,闻一多有《太阳吟》,戴望舒有《游子谣》,余光中的乡愁诗以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震撼了海峡两岸共同的心弦。乡愁诗一路走来,风情万种,“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虽然如今的乡愁,其产生的背景时势已大不同,但古典的传统的影响还是明显地表现在刚杰·索木东的诗歌中:对民族的认同、归依,对故乡的思念、眷恋,对文化的挚爱、追寻。深沉的悲患情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文化精神,使刚杰·索木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美建构。而惯常的主题在他的诗中因其独特的藏族文化和甘南地理,而显得更加深邃、斑斓,他以他清新流丽的诗篇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乡愁诗划上了一笔别样的色彩。
但其实,我并不想做如此理性而愚蠢的分类和概括。我知道,刚杰·索木东之所以“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甘南”,之所以绵绵不绝地写着草原,写着草原的星空、神鹰,格桑的绽放和马莲的忧郁,写“大金瓦寺的桑烟刚刚升起”,写“黝黑的屋檐下畏寒的麻雀”,写“长夜漏风的黑帐篷”里“以泪洗面的新娘”,写“阿妈刚把最后一粒种子连同秋天一起收起一场大雪已经迫不及待地落满草原”——是的,他之所以刻骨铭心于这一切,只是因为这就是曾属于他自己的过往岁月,这就是他自己的青春记忆。所有的追怀都让人“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个少年”。正是在这一点上,刚杰·索木东的诗歌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在东部期待视野下的所谓西部诗歌,那种邀宠炫美式的“民族写作”,更区别于那些观光客冷漠时髦的漫笔纪事。无关痛痒的浮尘,从不会缭绕在刚杰·索木东的诗笔之下。对于他,所有的地理人情土风民谣,都是成长的印迹,都是心灵的故事。他以自然的笔调记录它们,他以神圣的情感追怀它们,那些正在草原上一点点消逝的事物,那些渐行渐远面容模糊的古老文明,他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定格在挽留中,如同老家的木楼早已在时间中倒塌了,但他的灵魂始终流浪在它的旧尘缭绕中。是的,刚杰·索木东轻声吟唱的只是一支旧调子: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拆除,可以重建,可以从头再来的。关于故乡甘南大地上的一切,它们本来就是他,他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如今,“游牧在一座城市”,他不过是找到了可以回望、追怀它们的适宜地点,找到了弥合那种身心撕裂的无奈方式。诗歌的力量正在于此,它以微弱之光持久地照耀着我们黯淡紧窄的人生里那些“松懈”的缝隙,那些存放在记忆深处的眷恋和热爱,放弃和疼痛。
正因如此,刚杰·索木东的诗自然,本色,真挚,热烈,是纯粹意义上的抒情诗。在当下的语境中,“感动”是一个极其被滥用的词汇,但我仍然想说,刚杰·索木东的诗会感动很多人的心。也许,他的忧伤,他的悲愁,他对于故乡甘南多年如一的执着守望和呼唤,显得简单绵软了一点,“正常”公共了一点,但诗歌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诗人心灵的力量,刚杰·索木东从不缺乏。真情的重量,远胜于一切旗帜潮流的标示,胜于任何先锋后现代的诗歌技艺。
2010年,对诗人刚杰·索木东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年度。这一年,儿子问世,使他完成了一个男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阶段。在《2009,最后的絮语》中,他写道:“不知道春暖花开在今年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初为人父在今年会是什么样子向上,再向上一点似乎2010年我会这样提醒自己。”事实上,他正如自己所期许的那样,2010年之后,在诗歌创作上,他有了长足的进步,诗风趋于更加深沉、内敛、丰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目光在眺望故乡甘南的同时,终于也落到了他所身处的城市环境中更广大的艰辛奔波的人群中,他开始切入到了更凡俗更真实的日常中,去面对现代人共同遭遇着的漂泊无根的心灵现实。由此,他的乡愁和抒情有了与之前不同的另一种况味,“那十个来自高原的蝈蝈在水泥铸就的窗台边叫了整整一夜那十个远离潮湿的泥土和阴凉洞穴的蝈蝈那十个远离嫩绿草芽和甘甜露滴的蝈蝈在尾气和闷热充溢的笼子里在自来水和温棚菜的饲料里叫了整整一夜……曾伴随麦浪曼舞的十个自由的蝈蝈啊我知道,此刻在这座临水干涸的城市你们和我一样无法做到优美地高歌当生灵被视为玩物有谁还愿意仔细聆听羸弱的我们,卑微的我们嘶哑的诉说,咳血的音阶”(《十个蝈蝈,或远离的高原》)。
《残缺的世界》是一组简洁有力的好诗。刚杰·索木东作为一个诗人的独到观察和表现力,在这组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多年城市生活的忧心焦虑结晶出了思想之果,草原少年的柔弱心灵开始以悲悯之手抚摸匆匆人流视而不见的“残缺的世界”,那些在高楼大厦的角落被我们擦肩而过的伤痕疼痛,“谁能对一只断手熟视无睹?藏我于衣袖吧藏我于,永远无人可见的黑暗我将于一缕血痕间独自珍藏有关扼腕的所有秘密”(《残缺的世界》之《断手》)。“你真能给我一个支点吗哪怕只是给我,用一截木头触摸大地的甜美谎言”(《残缺的世界》之《断腿》)。“如果剜心之后尚能存活那我必将选择永远的沉默这个世界已经残缺如此,即使拥有一颗七窍玲珑的心我又怎能把深处的创伤向人类诉说”(《残缺的世界》之《空心》)。
长冬无雪,但春节之后是情人节,是元宵节,热闹总是找得到一茬又一茬的理由。在被烟火璀璨装扮着遮没着的城市天空下,你会觉得一个人不融入盛世的欢娱是可耻的,所以,当刚杰·索木东颠簸在回乡又离乡的路上时,我正疲累于远离故乡远离藏历的节庆里。这样的时刻,我知道我不是找不着星空,找不着那曾照亮了我少年梦想的另一片星空,而是今天的我,找不到可以瞭望星空的窗口。这样的时刻,想起海德格尔说,归乡是诗人的天职。想起另一个优秀的甘南诗人阿信说,回得去的叫老家,回不去的才叫故乡。想起刚杰·索木东“在古老的屋檐下,醉卧成游子的摸样”,他是否看清了炊烟升起的方向,感受到了血脉奔流的那份通畅?或者,“失去母语的那个村庄”,已然成为他此生无法回转的故乡?或者,他正在贴近着的甘南,我正在遥望着的甘南,注定要成为我们共同的甘南记忆?还要经历多少次的归去和离别,我们终将淬心砺骨地懂得,“自己既非过客,也不是归人”?
好在,还有诗歌。因着诗歌,那一场遥远的风雪再一次温暖地落到了我迷茫干瘠的思念里,“年关的那一场大雪已经不再那么可怕所以,我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心情给在城里出生的儿子堆一个憨厚的雪人这样,在他的尖叫声里就会找到回家的路偶尔也会在宿醉的夜半偷偷醒来,偶尔也会在静谧的院落数数童年的星星温暖的炉火旁已经很难听到亲人太多的叮咛了因为自己,也在慢慢老去”。
老去的,只是年纪。因为我们依然愿意相信,不老的是青春,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以心的温度捂着的故乡,是故乡之脉盘根错节生生不息的诗歌。
桑丹:没有比康定更深的爱了
在中国,或许没有人不知道那首月亮弯弯的传世情歌吧,它缭绕旖旎的旋律,撩动了多少多情的心灵,使他们对遥远的康定小城滋生无限的向往。世事沧桑,年华更替,但跑马溜溜的山上那朵溜溜的白云,在绵延不绝的吟唱中,以亘古不变的姿势招摇着天籁之美。
女诗人桑丹就出生在康定,那个藏语叫达折多的地方——这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被情歌映亮的小城,怎会没有诗歌的清音?一片英雄美人代代流传的土地上,注定要盛开前世今生的格桑。桑丹款款而来,她“口含一块幸存的美玉”,“将不能轻易倾吐的献辞”唱给了等待着的故乡,从此,她成为诗人。从此,康定在她的笔下成日地舞着,夜夜地歌着,从锅庄到弦子,从情歌到酒歌,马蹄飞扬长袖如云,醉生梦死处,千年积雪以诗歌的光芒闪耀在高高的贡嘎山巅。桑丹说,“有一种永久的迷梦有一种永久的苦难或光荣隔着茫茫岁月像河水把我照耀”,“那致命的诱惑足以使我耗尽一生的心血”。
我想象不出桑丹沉醉于诗歌宿命的面容。我至今未能与她有一面之晤,但我多年前就读到她的诗。虽然时下的诗歌每每让人失望,但我读诗总是比读其他更多些。偏执的阅读兴趣使我从堆积如尘的文字中邂逅了写诗的她。我先是发现了她的诗,发现了那种让我心头一亮的色彩和温度。继而才在后面的简介中,看到她是藏人,生长于康定,而今还生活在那里。我对诗人桑丹的了解,从最初到今天,仅此而已。其间,我也认识了一两个来自蜀地的她的文友,但我无意打听关于她的种种。我只是在每一次听到康定情歌的时候,都会想,哦,桑丹在那里呢。就像想起一个熟人。桑丹分明已立在了我的面前。她长袍垂地,环佩叮当,这个美丽的康巴女子,和她的诗句一样真诚,一样鲜活,她轻而易举就掳掠了我绿松石般鲜艳红珊瑚般飘忽的前生。
该是为梦中最真的一次苏醒和守候而写诗的吧,该是为心中最痛的一次告别和领悟而写诗的吧?生长在那样一个情歌之城,哪个女子不渴望一场盛大的相遇,一份恒久的拥有?然而,所有的爱情都有料峭的身影,太多的女人都适合在幻灭中眺望,“往返的路上你孑然一身你将隐忍命运所赐的悲欢”。于是,到最后的最后,始才懂得,惟有脚下的土地才是最坚实的支撑,唯有身后的跑马山,眼前的雅拉河,才是最忠诚的依傍。懂得“一位河岸的歌者需要恒久的修炼才能让喑哑或高亢的声音承受命运的悲悯……”诗人桑丹,在无言的岁月经历了一个女人“一生最完满的悲伤”后,终于于身心深处唱出她创作的最高音:“没有比康定更深的爱了,没有比达折多更浓的情了。”
是的,桑丹与康定密不可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康定山水,这“雪地上唯一的故乡”,便成了她诗歌创作不竭的主题。她肯定没有预料到,文学表达与地域维度的关系会越来越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贡多,大江健三郎的北方四国森林,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杜拉斯的湄公河岸,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以及眼下正在千宠万爱中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因了这一切,荣格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扎根于大地的人永世长存”,成为卷土重来的新时髦。在所谓“接地气”的热潮中,作家们一哄而上,在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飘忽的“故乡感”中掘地三尺地寻找着故乡。而桑丹,她从来用不着刻意地过分地开采“故乡”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她写或不写,故乡都在那儿,故乡就是她日日经历着的人和事,就是夜夜落在她窗前的月亮弯弯。所以,所有的孤独与悲怆都深植于现实的土地,错杂着生生不息的根系,死亡与痛苦带着民族文化最深刻的烙印,盘旋往复在她的诗笔下。她的创作是有根的,是带着地气的温热的,她从未停留于外在的追求与表现上,而是尽力让诗歌直达内在的诗意,这种诗意是桑丹独创的属于康定山水的,属于更辽阔广大的康巴文化的,同时,它也是属于整个藏民族的深层诗意。这样的诗意,使桑丹的创作毋庸置疑地拥有了和她的故乡相匹配的海拨高标。
这是个喜欢将复杂的文学做简单归类的时代,尤其在三十年来的当代诗歌进程中,命名运动风起云涌,什么先锋写作常态写作,什么西部诗歌女性诗歌,什么“下半身”又什么“新红颜”。我不知道在遥远的康定小城,在诗歌之外做着一份平凡工作的桑丹,是否会关注这些喧哗与骚动,但我相信,即便关注,她也不会为其所动,为自己的创作如何被命名而苦恼,因为无论是作为“女性诗歌”,还是“西部诗歌”,她知道自己诗歌的内在艺术品质是始终如一的。无论诗经历着怎样与时俱进的浪潮,对桑丹来说,写诗只是让她“优美地绚烂”或转瞬即逝的“花朵,荆棘,还是滴落的水珠”,是“活着的理由之一”。她惟有甘于边缘,潜行修远,以写诗的方式唱出对故乡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她才能拥有自己生命的本真。诗是她生命的另一个宗教,她通过诗去触摸那慈悲无边的神的呼吸,她依靠着诗才能“翻越高处的风雪,还终点一个神圣而悲壮的洁净”。
就是这样,桑丹的诗集中描绘了她对康巴故土至情至性的热爱和守望,她深情地赞誉着她的民族和这片雪域净土所赐予她的命运之旅,就是在这样的心灵的跋涉和求索中,她找到了生活与德行之美,也找到了由神圣信仰与民族文化回归共同建构的属于她自己的诗歌风骨。她不喜空泛的抒情及抽象的议论,也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屡见不鲜的因为写高地写边缘写少数民族而生出的“天然”的崇高。桑丹情深谊长歌颂故乡的诗章,字字行行都带着康定小城特有的热辣和皎洁,赤诚和谦卑。她擅长诗歌的“写实”,注重情感的在场,她以身为康巴女性中的一员所具有的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塑造了众多的女子形象:康巴女子,木雅女子,锅庄阿佳,掂香姐妹,卓玛,以及在整整二十八首《扎西旺姆》中爱恨长存的外婆扎西旺姆。在这些诗中,桑丹以她细腻的理解,深切的体贴,以灵慧的诗笔,使身边的生活中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成为“世间至上的母亲”、“世间至上的女人”“世间至上的情人”,她们绝尘而来,在她的诗中光芒熠熠。桑丹有源自骨子里的理想情怀与浪漫色彩,但一旦落实于具体的人和事,却能具备明锐洞穿的超乎单狭女性立场的视界,去表现男女共同的生与死、苦与乐的人性世界,所以她不撒娇,不煽情,懂得付出和领受,所以她细密而又广阔,尖锐而又温润,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和穿透力。她说,“一场宿命漂泊不定在我手中青铜的杯子早已碎裂在我心头一朵灵验的花瓣正在凋落”,但“即使神灵预示了所有的苦难和忧伤引领你向前的始终是悲悯和爱”,“如果那是你命中注定的一切我将在各种临风摇曳的容器里喝尽这枚时间的伤”。
写诗二十余年,桑丹至今偏居康定小城,安守着那里的美丽和清寥,这使她在中国当代诗坛甚至在藏族诗坛中都没有获得所谓应有的名气和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她是藏族诗人中富有艺术精纯性的成功诗人。许多诗评家都激赏她的《田园中的音响》和《河水把我照耀》等诗,认为是转型期中国汉语诗歌的优秀之作。在这些作品中,桑丹诗歌最令人赞叹的细腻与大气,精致与洒脱相结合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词语意象组合,出人意表又具体切肤,既有深切的现代意识,又蕴含藏语古歌的韵致,境界舒放,格高思逸,像“我的翅膀在你高远无际里展开”的那种感觉。如此散发着“一种从容不迫的幸福”的诗歌,必将不会被时代花样更迭的潮流时势所左右,它更适合“像清洁的酒深埋在我的心中被轮回的光阴慢慢地痛饮”。
桑丹喜欢写金黄的田园,写隐秘暮色的秋天。和许多诗人一样,她也喜欢写河流,河流是文明的发祥地,是诗歌的栖身所。她说,“只要最早一次看见河,就不要轻易离开它”。我不知道她的康定城里那条叫雅拉的河,在藏语的清晨和黄昏,变幻着怎样的风情。我不知道在城市和乡村都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大家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今天,雅拉河是否还会是她“最早一次”看见的河?冬去春来,当我消磨劳顿在远离她的另一条大河边,偶尔会让思绪飘向歌声氤氲中那座溜溜的小城,小城里那个临水而立的女子。“岁月的积雪汇聚成河”,像命运一样与她邂逅时,那个叫桑丹的女子,照见了自己怎样的容颜?
在刮着风扬着沙的坏天气里,遥想一位诗人和她明亮的故乡,我觉得自己也被照耀。
2013/3/20于兰州黄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