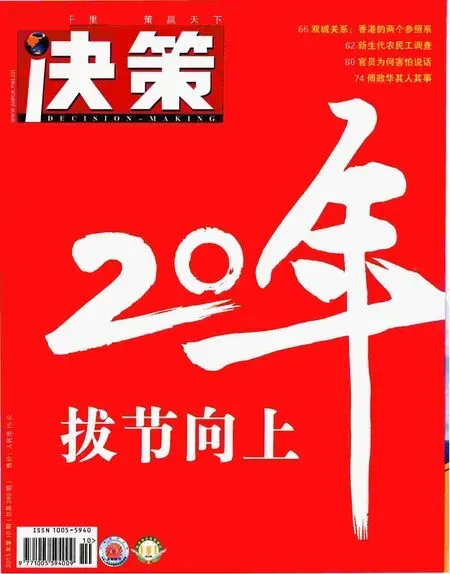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熊易寒

新生代农民工究竟“新”在哪里?他们区别于父辈的特性是什么?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稳定有何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在上海市进行了一次覆盖全市范围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09份,其中有效问卷906份,有效率为99.7%。
调查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考察,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劳动者,也是有着权利诉求的公民,更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作为劳动者,他们要求的是收入和福利;作为公民,他们要求的是权利;作为人,他们要求的是尊严。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恰恰是我们以往的城市化道路和分配体系所忽略的。
更注重寻求个人发展
906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男性占69.5%,已婚有配偶人员超过半数,达到56.4%。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仅高于他们的父辈,而且也高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水平: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只有42.8%,持高中和中专学历者多达41.2%。
从问卷和访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来沪务工的动机是复杂多元的:既有迫于生存压力的,也有为了获得更高收入的,还有为了实现梦想、增长见识或体验城市生活的。
虽然生存取向的经济动因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65.1%的受访者将“赚钱养家”作为自己来沪工作的首要动因,但是选择“过城市生活”、“见见世面”、“寻找发展机会”和“为前途考虑”等非经济动因的受访者也多达33.2%,其中“寻找发展机会”占16.2%,仅次于“赚钱养家”。
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动机正在由提高家庭收入向寻求个人发展转变。他们外出务工的动机与父辈已经呈现一定的差异,即从生存取向转向发展取向,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有62.9%的人来到上海后打过1-2份工,29.9%的人打过3-5份工,打过5份工以上的仅为7.2%,这反映出外地来沪人员的求职与实际工作过程较为稳定,能够很快找到工作并长期从事。
63.2%的外来人员签订了1年及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1年以下劳动合同的只占21.5%,无劳动合同的占7.2%。这反映出无劳动合同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建筑业工人无劳动合同的情况较为多见,其待遇和保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正成为他们的就业新趋向。商业服务人员是所有工作种类中比例最高的,达到了25.5%。同时,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也达到了25.2%。
被访者平均每周工作5.6天,每天工作9.28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或7天的占到总人数的61%,每日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到53.5%,加班和超时工作的情况较为普遍。
有77.4%的受访者认为,“没有技术”和“学历过低”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求职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外来务工人员也很少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的培训,86.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农业培训,84.6%的人没有接受过非农培训,仅有29.9%的人有过学徒工经验。
问卷调查和访谈都发现,与父辈农民工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或生产经营场所不同,只有50.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工人宿舍中,有41%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与他人合租房屋或是独立租房。他们不仅将
住房作为一个遮风避雨的居住空间,也将其视为一个体现个性的私人空间。
通过走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处,我们发现:青年农民工往往对房间进行了精心的、个性化的布置,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她们不是将出租房视为一个临时居所,而是倾向于将其布置为一个温馨的家。
对于他们而言,宿舍不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场所,一则因为存在较多的纪律约束,二是无法拥有个人隐私。但独立租房的成本又太高,于是群租成为多数人的优先选择。值得关注的是,4.3%的受访者(39人)拥有自购房,这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经济分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动机正在由提高家庭收入向寻求个人发展转变。他们外出务工的动机与父辈已经呈现一定的差异,即从生存取向转向发展取向。
压力大,权利意识更强烈
46.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压力“很大”或“较大”。同时,有50.9%的受访者认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主要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大所致。这些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中可能存在紧张情绪,普遍的劳动和工作压力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过激行为。
面对巨大的压力,略多于1/3(36.4%)的受访者,以听音乐作为舒缓压力的首要方法,优先选择看电视和电影、上网,以及睡觉的人数共计占到了43.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找朋友倾诉”、“向父母和亲人诉说”、“文体活动”以及“加入社团”等方式的总共仅有9.6%。这说明个体性活动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舒缓压力的首要渠道,社会交往性活动偏少,甚至有3.8%的人选择“沉默”或是“哭泣”。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社会交往和人际网络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自杀率上升、反社会行为增多。减轻外来务工人员精神压力,降低他们的工作强度,帮助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已经刻不容缓。
当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外来务工人员会选择采用何种方式维权呢?有23.7%的受访者选择优先向同乡或亲友求助,这说明链式移民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倾向于抱团。优先选择向单位领导或是政府部门求助的共计40.6%,这一现象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劳资双方的经济性冲突最后都由政府“买单”,这无疑是一种潜在的治理风险。
而本应在经济纠纷和维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工会和党团组织等,却并没有得到劳动者应有的认同,选择“党组织”、“团组织”和“工会”作为维权手段的总计仅有11.4%,和选择“自己解决”的比例相等。如何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如何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主心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对30名新生代农民工和20名老一代农民工的访谈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提及“人权”、“自由”、“平等”等词汇,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提及“命运”、“忍”、“没办法”等字眼。当问及个人权利是来自政府的规定、法律的赋予还是与生俱来的,大约五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是与生俱来的,1/4左右认为是法律赋予的;而超过七成的老一代农民工认为是政府规定的。
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较之上一代更为强烈、清晰,更接近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公民人格。这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多地接触互联网,从而接触到更多的非官方信息。
文化消费: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夹心层
一般而言,获取文化产品的主要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市场购买,譬如去电影院、剧院消费;二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譬如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新生代农民工则处于二者的夹缝之中,他们收入微薄,无力承担相对高昂的文化消费。
在访谈中,有多位青年农民工表示:“进电影院看进口大片需要80元,一般的片子也要40元,太贵了!”另一方面,他们缺乏户籍身份,也无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以受访者的首要娱乐开支为例,上网占40.7%,购买书报杂志和支付手机娱乐费用等,开销较低的活动共计33.5%。
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是缓解工作压力的有效手段。在访谈中,新生代农民工也表达了对电影、音乐会、图书等文化活动的向往,但当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却让低收入的他们捉襟见肘。
在此次调查的受访者当中,月收入在1200~3000元之间的人数占到了3/4(76.4%),更有4.4%的人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上海几乎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无力在文化产品上有所投入。
在被问到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障碍时,58.5%的受访者坦诚“价格偏高”是自身进行更多文化消费的主要障碍,他们希望有更多公益性质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
就其家庭每月具体开支来看,样本平均每月总消费为2433.2元。其中,食品消费和房租是家庭每月开支的主要部分。同时,汇款占收入的比重较之父辈大大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汇款比重为15%左右。以上三种开支每月平均达到了1329.7元,占每月总开支的54.65%。
另外,外来务工人员年龄层次较轻,因而子女教育也是日常开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每月达到320元左右。而本研究所关注的文化娱乐消费,只占6.65%,每月约花费161.8元。这一数据与前述工资水平较低的观点相互论证,可见外来务工人员在文化娱乐生活上的相对贫乏。
社会嵌入性低,精神文化生活贫乏
从调查和访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嵌入性较低,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太发达,社交性活动相对缺乏。
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老乡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同乡网络虽然重要,但重要性已经相对降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平常很少有社交性活动,与同乡网络的关系相对松散,学缘关系、业缘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上升。
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不再囿于同乡网络等地域因素,更加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相对脆弱,在业余时间里,他们往往倾向于从事个体性的活动,譬如睡觉、上网、听音乐、看电视,而很少与外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导致缺乏情感沟通、生活压力难以释放。
与上文提到的减压方式相似,50.7%的受访者会将业余时间主要花在听音乐或看电影电视上,更有13.7%的人会以睡觉打发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比重极低。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们业余生活的单调乏味,同时也间接体现了农民工的高劳动强度。
42.5%的人认为,“空闲时间少”和“精力不够”是制约日常休闲娱乐的主要障碍。这也与他们较低的收入直接相关,40.9%的人认为经济因素使他们难以奢望文化娱乐。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活动范围狭小,而且对所在社区文化生活的参与程度也偏低。由于户籍制度的排斥与居住空间的隔离,使得他们成为城市主流社会的局外人。问卷显示,“根本不知道社区有活动”和“知道,但没被邀请”的受访者共占63.3%,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仅有7.7%。
受访者认为所在的企业以及共青团组织所提供的文化活动偏少,分别有53%和53.6%的人表示,从没参加过企业和团组织的文娱活动。
从整体上来看,精神文化生活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块软肋,主观满意度较低。52.1%的人认为,“上海不过是我打工谋生的地方”或“我只是上海的过客而已”。我们在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状况的时候,需要着力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