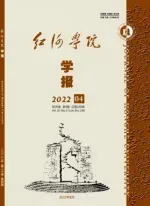淮南三王复初思想之比较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但由于种种原因,人的良知往往又遭受蒙蔽,如人的“躁”、“荡”、“歉”、“忽”、“傲”等主要是心不纯,要通过修养使其陶冶“心学”和“道心”。不过,王守仁并没有提出“复初”这一概念。真正的“复初”概念是由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来的。①王艮的复杂思想非常丰富,其弟子王栋、王襞也就“复初”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应该说“淮南三王”的复初思想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具体的观点与论述也有不少差异,本文试作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 王艮去除杂性的复初观
王艮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什么是“气质杂性”?王艮讲解说:“张子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语亦要善看,谓‘气质杂性’,故曰‘气质之性’。[1]”(《答问补遗》)当然,王艮也认为,这种“气质之性”并非人本有的性,他对学生说:“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清固水也,浊亦不可不谓之水’。此语未莹,恐误后学。孟子只说性善。盖善,固性也,恶非善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故言学不言气质”[1]。(《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恶”不是性,而是“气质杂性”,如同水中的泥沙不是水一样,水清则泥沙自去。人的气质性就如同这水中泥沙一样,也是可以变化的。所以人有“气质杂性”不要紧,因为“以学能变化气质。[1]”(《答问补遗》)王艮还认为,道德教育可以去除这种气质杂性。“明得尽,渣滓便浑化。[1]”(《答问补遗》)也就是说,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改变气质,去除气质杂性,保持善心,减少人世间的争斗,进而实现天下大治。
王艮讲“气质杂性”的目的是要人们诚心诚意地改过迁善。他说:“是以迁善改过,日入于精微也,不然则抱道自高,未免于怨天尤人,此所以为患也。[1]”(《答邹东廓先生》)以良知为例,“良知”是“知”,是人的知觉本能,而保持人的知觉本能的原初状态,就是体悟良知。他指出,人性本是善的,人们只要认真领悟内心固有的良知,去不善而复善良本性,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人生目标。所以王艮讲去除气质杂性,就是要恢复人当初的本性,做一个真实的人。他在《复初说》中解释“诚心”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则无事矣。故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是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1]”(《复初说》)
那么怎样去除杂性以复其初呢?关键要做好这样几点:一是要“守身”。王艮要求人们不要被功名利禄所困扰,他反复说,“今人只为自幼便将功利诱坏心术,所以夹带病要,终身无出头处。[1]”(《语录》)“日用间毫厘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盖功利陷溺人心久矣。[1]”(《语录》)由于气质杂性的起源与受污染有关,所以要保持最初的纯洁,先要守身防污染。二是要正心。他说:“心之本体,原着不得纤毫意思的,才着意便有所‘恐惧’,便是‘助长’,如何谓之‘正心’?是诚意工夫犹未妥贴,必须‘扫荡清宁’,‘无意、无必’,‘不忘、不助’,是他‘真体存’,‘存’,才是正心。[1]”(《答问补遗》)王艮对心之不正者非常愤恨。当然,王艮也看到了一种客观的规律,人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之中,社会的现实总会对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王艮特别强调正心的作用。三是要修仁。王艮认为,“仁者安处于仁而不为物所动;智者顺乎仁而不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随约乐而善道矣。[1]”(《语录》)而这一“善道”主要是“仁”的作用。所以王艮认为,只有处于仁的状态,人才会减少受外部的影响,进而保持最的善心。
二 王栋正心求初的复初观
王栋的复初理论主要是就良知而言的。他继承了王阳明的良知蒙蔽说。在王阳明看来,人人皆有良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人的良知往往又遭受蒙蔽。如由于不察而产生的蒙蔽,由于人的贤愚差异产生的蒙蔽等等,而人有贤愚之分,也是因为人受到蒙蔽的结果。同时,王栋也接受了王艮的“气质杂性”说。事实上王栋综合了王阳明的“良知蒙蔽”说和王艮的“气质杂性”说,其一,他认为人的良知蒙蔽是由人的气质不同而引起的。曾经有人与他辩论说:“既是良知自明,何俟学术透露?”他说:“夫人性体虽一,而气质不同。[1]”(《会语续集》)因为人陷于日用应酬而使“良知”滞泥。王栋认为,“良知虽人人自有,多为见闻情识所混,认识不真。[1]”(《会语正集》)其二,王栋认为,人蒙蔽与人对良知的错误认识有关。他认为良知非“知”,今人把“良知”与“知”搞混了。他说:“今人只以知是知非为良知,此犹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动不虑而知之灵体,其知是知非,则其生化于感通者耳。[1]”(《会语正集》)其三,是因为人陷于日用应酬而使“良知” 滞泥。王栋认为,良知本体自辨自真,于日用常行之中应事接物。也就是说体悟良知离不开日用常行,但良知本体“洁净无私”,故“不为见闻情识所混”(《会语正集》)[1]否则就会陷于日用应酬,而产生良知受蒙蔽的现象。由此他说:“良知虽人人自有,多为见闻情识所混,认识不真。[1]”(《会语正集》)良知遭受蒙蔽怎么办,当然要“复初”。王栋认为,复初要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其一,要体悟良知以保洁。他说:“本末不乱,方是良知洁净,而不为见闻情识之所混也。[1]”(《会语正集》)王栋的意思是,对良知本体要潜心体悟,岁月磨砻,自有所得,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见闻色象。他曾作诗曰:“讲堂游侣发歌声,天籁无端日夜鸣。真乐得来非色象,良知悟破自灵明。见闻情识休相混,势和纷华岂足樱。此是乾坤真诀窍,敢矜私秘说师承。[1]”(《示讲堂诸生》)其二,良知要不为情识所混,还必须注重反身格物。他说:“吾人欲得透露良知,则必反身格物,从实体认,默而识之,然后此知此明,不为见闻情识所混,不为智愚贤不肖意见所偏,则信乎良知直指性命之机缄,格物又为学术之把柄。[1]”(《会语续集》)王艮与王栋都强调主观内省的重要性,并依靠主观精神以自我调节,反映在对良知本体的证误上,更见其用功精密,一脉相承。“人而明此,则但反求诸身,色色种种都从我一念诚恻怛中自然流出,自无不蔼然真实,无不感动得人。若不明此善在我,而只勉强从外而掇拾将来,都只是装点作伪而已。[1]”(《会语续集》)、其三,要以正心求复初。王栋认为,只有正心,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挡得住世俗的诱惑。王阳明主张“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王栋对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应对心有仁义礼智之德与知觉作用做出区分,前者是决定心之所以为心的本质规定,而后者则不过是心的血肉之躯,即外在形态。因为“性是心之生,理于中,自具五常之德[1]”(《会语续集》)所以如果无性生于中,就不能称之为心。由此他明确反对混以知觉作用说心说性,认为这是导致后世邪说横流的病源。不难看出,王栋的这种心性论也是对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进一步纠正。
王栋的“复初”理论的根本点还是强调道德修养。他认为,人的道德的形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努力,即“自成之德”。所以正己修身才是主体之要。他说“身为天下国家之本,决当止于至善之地,此之谓知止,然后志不贰于自修,心日休于有主。人虽欲指议其非,且无所自况,复有莫之与而伤之者哉!是此身常止于安吉之地,而至善在我矣。[1]”(《会语正集》)这都是从修养结果而言,他认为做到了止于至善,也就达到了复初的目的。之所以要这样说,,因为止于至善才能致中和。只有致中和,才能做到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 “宰乎其发”不致于“乱发”[1]。(《会语正集》)那么,如何做正心的的功夫呢?一是要有行乐功夫。什么是乐?王栋认为“今日用间,但觉忻忻融融,无忧郁烦恼处,即是乐也。[1]”(《会语正集》)他认为,汲汲行乐,乃是为了导养中和,“以立天地万物之本耳”[1]。(《会语正集》)并指出,“当时孔子与点正是此意,若不识此意,却只是偷闲学少年,自了一身而已。[1]”(《会语正集》)二是要做到勇往担当,心中有主,不怕人谤。他说:“人为学,须是勇往担当,模糊着终不济。[1]”(《会语续集》)三是要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实际上就是一种“仁和”精神。他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和兼容。此外,王栋还认为,复初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做到不迁怒,不受情绪的干扰。
三 王襞保洁修道的复初观
王襞与孟子和王艮、王栋他们在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他始终把天命之性视为人之本有的东西,且这种东西是清纯的。他曾作诗说:“清清玉洁冰凝人,事简利名轻不思。游燕不纵闲情倦,依龙隐卧歌趁鸟。和鸣霁月光风意,思高山流水音声。细悟形骸皆外物,已知天地得吾生。”(《清闲安乐步天阶四韵》)但是,他认为人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本源之性有可能出现“失真”现象。比如良知本来是人人都有的,但后来“只为世诱在前,起情动念,自幼便染污了。[1]”(《题冯生一龙云江图卷》)所以“开眼便错,搅搅扰扰”,“起情动念”,糊糊涂涂”[2]。(王士纬《东厓学述》)
王襞还认为,由于良知本体的自然真性易被情欲所蔽,致使百姓在“日用动作”之始即“失其妙运”[1]。 (《语录遗略》)以良知为例,虽然人之初个个具有“纯粹至精”的良知,但随着人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人的这种良知品性也就受到了污染,从而逐渐变得不纯不精了,这就要复以保持固有的良知。同时,王襞虽然讲“圣人与百姓日用同然之体”,但也承认圣人与百姓在本体之性的认知上存在差异,所以“圣人者永不违其真焉者耳。[1]”(王元鼎《先生行状》)而百姓“违”者,是因为百姓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固有的良知品性。在王襞看来,无论是尧舜还是孔子,都是具有“良知”这种崇高人格的圣人君子,其心性都能自做主宰,所以率性而动,日用皆道。后学者之所以对此没能贯通,是因为他们不能了解尧舜与孔子的崇高人格的妙用,而受到外界种种知见干扰,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像尧舜与孔子那样崇高的人格。他说:人“在纷华势利中,为其所惑,乃生妄见,将虚洞之府,掩蔽其真窍,而日用动作,始失其妙运矣。惜哉![1]”(《语录遗略》)王襞认为,若人最初的本性“失真”或被染污,“则不自知其日用之本真而获持之,一动于欲,一滞于情,遂移其真而滋其蔽,而有不胜之患矣。”
怎样“复其真”?其一,为人要讲“洁”。 在王襞看来,心体原无一物,良知本自现成。“复初”就是要守持“良知”,只要守持“良知”,自能辨别是是非非。同时,只有讲“洁”,人才不会被世俗人情所惑。而讲“洁”又在于“守本”,即守住人本自现成的、纯粹至精良知善根,使之不遭污染。其二,要做到“心中有主”。王襞认为,只有做到“心中有主”,才能排除外界的影响,抵制外部的诱惑,从而保持本有良知的纯洁。其三,要淡视名利。他说:“文士多饰情,恐为名所误。[1]”(《凌千春•漫言》)人要保持已有的良知,就要正确看待名利。王襞强调“乐道善言”,强调“做人须要十分全”。他提醒人们“何事世人终不悟,回头应作等闲看。[1]”(《寒夜会中作示诸友》)王襞反对私欲,反对贪富恶贫。他认为“人其舟也,财犹夫水也;舟而无水则困矣,可乎?所恶于财者,谓其私也,积而不能散者也。积而能散,则尚嫌其不多耳。[1]”(《次日再复畴翁书》)
王襞关于复初的思想本质上是要人通过修道的办法“去其蔽,复其真。[1]”(《率性修道说》)修道除了要淡视人欲以外,还要注意“忧道”,即儒家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当然,王襞的忧道与传统儒家所说的不注重物质享受,富贵贫贱都不要去计较,无论居于穷困的环境还是居于安乐的环境,都能安于“仁”德,乐“道”不倦,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浸润在学“道”之中不同。他说:“以故不为小小功果上知之士,所以自甘竭尽肝脑,若救生于水火之中者,不谓干涉事大,而故乃急急于是而求之也。[1]”(《寄会中诸友书》)从王襞的这一论述来看,他不仅要人不要计个人成败利害、荣辱得失,而且不要把心思放在“小小功果”上,而是要救生民于水火,干天下国家之大事。
注释:
①泰州学派诞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消亡于明万历三十——三十二年间(1602-1604),前后,持续76年左右。泰州学派是一个遍布全国的大学派,也是一个极具启蒙性质的平民哲学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其次王襞(1515-1587),族弟王栋(1509—1581)为均为皆学派核心人物。
[1]袁承业辑.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O].东台,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2]王士纬,袁承业辑.心斋学谱[O]. 东台,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