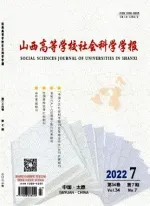贿赂犯罪证明标准的虚与实*
吴宏毅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贿赂犯罪案件中的证据问题,一直是检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与经济建设伴生的贿赂犯罪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一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运行机制发育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二是惩治贿赂犯罪的力度明显不足,这个不足很多时候表现为证据、证明问题。
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定罪量刑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必须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即“证明标准”。这个标准在理论上,不管是表述为我国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实际上,都不是可以实际操作的标准。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所谓案件事实是司法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识,而且还有程度问题,也就是说不是绝对的客观的真实。从哲学上看,这是一种蕴含价值观的事实认定标准[1]。
一、贿赂类案件的证据特点
贿赂类案件的证据较之其他案件具有更大的易变性、隐蔽性、复杂性和间接证据的决定性等特点,这是由贿赂犯罪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证据的易变性
大多数贿赂类案件的认定,由于行、受贿行为的秘密性,知情人少,主要依赖于言词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有时甚至仅限于言词证据。但是,言词证据本身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如个人对客观事物感知的主观差异性、记忆的有限性、语言表述的不确定性等,都会影响到言词证据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作证时,大都具有复杂心态。犯罪嫌疑人归案后,有可能会部分或全部供认犯罪事实。然而,因为对可能受到的法律惩罚怀有恐惧心理,或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又可能推翻原来的供述。行贿人、证人容易受到威胁和收买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出现证词变化,有的甚至多次反复。犯罪嫌疑人被查处后,大多数出现恐惧心理、逃避心理、抗拒心理等,思想波动强烈,常常出现翻供现象,以及由于记忆的原因,供词出现前后不一致,致使证据不稳固。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往往造成证据的反复。
如果案件侦查重心全放在言词证据上,就会使案件的证据基础相当薄弱,一旦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证据有变化,整个案件成立与否都成为疑问。
(二)证据的隐蔽性
贿赂与其他类型犯罪相比一般无作案现场,犯罪也往往是有预谋的、隐蔽的、连续的作案,周围群众多不知情。贿赂案件往往是行、受贿双方各有所图,在没有发生利害冲突的情况下,一方不会主动报案。而且,犯罪手段隐蔽在各种公务和经济活动的深处,在建立正常往来关系的同时,又建立一种隐蔽的、默契的贿赂关系。贿赂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一般较强,大都利用其职务或职权,建立一定的关系网、保护层,且往往订立攻守同盟,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知情人也因种种原因不愿作证或作伪证。
总之,贿赂案件的证据有很大的隐蔽性,这给收集证据认定犯罪事实的侦查工作带来相当大难度。
(三)证据的复杂性
其一,犯罪主体身份难于判断。在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阶段,所有制形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加之聘任制、合同制等人事制度的改革,给认定贿赂罪主体的身份带来一定困难。例如,在笔者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人是国有公司派出到下一级企业的技术人员,随后该企业与香港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这给某人的主体身份取证带来了相当的复杂性。
其二,证据收集的复杂性。收集贿赂案件的证据过程,有的涉及会计、经营、贸易管理等多方面的专门知识;有的是案件的证人,同案件有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在作证时心理活动复杂,不愿作证或作伪证者较多;有的贿赂活动往往被其“合法性”外表或者不正之风所掩盖,非法特征不明显,这都增添了证据收集的复杂性。
其三,证据种类也很复杂。案件中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相互交织。例如,对利用职务之便这个行为,有不同利害关系或出于不同考虑的证人会做出不同的证言。贿赂案件中能够直接地和单独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直接证据较少,大量的是间接证据。如果被告人拒不供述,又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间接证据。
(四)间接证据的决定性
由于贿赂案件的直接证据基本上仅限于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又具有不稳定性,那么,间接证据的大量收集和运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间接证据虽然不能直接和单独地对案件事实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是,不仅对直接证据真实性的判断要依赖间接证据的印证,对有些只有行贿人证言而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案件,形成证据链条的大量的间接证据就决定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的间接证据具有体系性,与受贿犯罪的过程相对应,每个环节均有相应的间接证据予以证实,而由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条,推导出一个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结论,证明了受贿行为的存在。所以,间接证据在受贿案件认定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从“虚与实”的辩证角度分析贿赂犯罪证明中的特点
行贿与受贿是以贿赂为中介进行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易。从我国现行立法可知,贿赂的财物是指金钱和有形物品。因此,在贿赂案件中,必然伴随着财物及财物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行贿方付出财物,受贿方得到财物。而财物必然有迹可查,这是贿赂犯罪证明中的实。
贿赂犯罪与其他犯罪,例如杀人、盗窃等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贿赂犯罪主体不是“单兵作战”,而是隐蔽于正常生活之下的受贿人和行贿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巧妙“合作”。即使索贿案件,一般也被迫在隐蔽环境下一对一交易。而且请托的事项也往往掩盖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这类以多种方法遮蔽的犯罪,往往难以顺利取证定罪,这是贿赂犯罪证明中的虚。
如何以实证虚,由虚探实,虚实互证,这正体现了贿赂犯罪证明中的体系性思考。
2012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在明确提出“证据确实、充分”可以定罪这一证明标准的同时,进一步给出三个条件,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体系性要求。从中应该可以看出证明标准设立的因素是分阶段、多重的、复杂的,证明标准不会是一个笼统而单一的标准。而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是在诉讼一开始就能达到的,也不是认定有关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而是伴随着对案件事实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最终达到的证明要求。
三、虚实结合的证据收集对策
要实现贿赂类案件的证据充分,需要充分结合本类案件的特点,想办法、找对策来实现证据充分。
(一)“实”的证据收集
1.把财物这个“实”牢牢抓到手。把这个“实”牢牢抓到,或者说紧追不舍,是受贿者最担忧的。这是贿赂案件最本质特征,权力和金钱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吸引、互相利用的体现,是整个案件侦查中最摸得着的东西。但是,犯罪手段具有狡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我们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例如,家属亲人受贿,以借为名,信息费、顾问费等名义,长期提供使用权,暗中合伙经营、坐收红利,股票债券的时间差、地区差等。
2.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第148条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当今工业化、信息化十分发达的大背景下,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管、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秘密取得物证和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必将发挥重大作用[2]。在侦查过程中,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例如对犯罪嫌疑人在新媒体环境下发送、传达、接收信息进行监听监控,获取犯罪嫌疑人利用移动电话、电传、因特网等新技术手段进行串供、销毁证据、掩盖罪行的行为,就是揭示案情有力的间接证据。
(二)“虚”的证据收集
1.受贿行为的连贯性、一致性问题。对多次收受他人钱财的情况,应当结合具体事实加以正确地判断。
第一,如果行贿人为了某个特定的具体请托事项或者为了同一个连贯性的整体请托事项而长期反复送钱,国家工作人员也为了长期为他人谋利而收受财物,应当认定为受贿。比如,在某个长期的工程项目中,为了从招投标、施工到结算整个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获得关照,而在整个过程中反复送钱财给某一相关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为了不断获得建设项目,反复向他送钱物,而该人员为送钱财者不断获得工程而提供帮助。在这些行为中,尽管其中某一次或某几次送钱时,没有明确说出请托事项,但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具体请托事项,或者存在着内容、目标指向和性质同一的连贯性的整体具体请托事项,双方都明白,每一次送钱都是为了这个特定的具体请托事项或者为了这个内容、目标指向和性质同一的整体的请托事项。由此可以断定,双方为此建立了长期固定的权钱交易关系。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反复收钱,应认定为受贿。
第二,在某个职位上,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多人请托事项而长期反复收钱,应当认定为受贿。虽然这些多次反复的收钱行为是分别为了不同的行贿人的具体请托事项而分别多次收钱。但是,每一次不同的收钱行为已经与不同的行贿人形成了明确的对应关系,每一次的收受行为也与不同的行贿人的特定请托事项形成了明确的对应关系。这表明国家工作人员与每一次不同的请托人之间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权钱交易关系,但确是同类型的权钱交易关系,应认定为受贿。
2.高度重视“再生证据”。“再生证据”是指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为使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追究,而进行的掩盖犯罪事实、隐藏、包庇犯罪嫌疑人等反侦查活动形成的、新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事实。犯罪嫌疑人不甘心束手就范,会采取种种反侦查活动,如行贿受贿双方或者被收押的犯罪嫌疑人与监外人员进行串供,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以及采取伪造、补写借条、还款收据等。这些情况基本上每案皆有。我们应加大对反侦查活动的侦查力度,获取反侦查活动的再生证据可以突破案件,有的甚至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使断层的证据得以链接。
四、虚实结合形成证据链
通过上述虚实互证,虚实结合的证据收集对策,案件的证据链就可以形成。
证据链是由证据材料构成的证明案件全部事实的证据体系,是由大小不等的证据材料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证据链中环环相扣的正是虚与实结合而成的证据材料。“实”的受贿财物必须放在受贿行为的大背景下,放在便利要素证据、收受财物证据和谋利要素证据的整体环节中,才能成为定案的扎实基础。整个受贿行为是一种关联性行为,即行为人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职务上的便利,具有直接的作用性或影响性关联。正是它的关联性,行成了行受贿双方的需求性关系。抓住每一个证据材料本身与抓好环节之间的衔接同等重要。证据链的形成源自于能够独立证明案件某一事实的证据材料,因此证据链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或者说证据链的生命,取决于证据材料内在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据材料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和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
就证据链的形态来看,它是一个由众多证据材料构成的证据链条。但是,据以形成的证据材料在未形成证据链之前是孤立的,它本身不能单独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而据以构成证据链的,是由相关证据材料构成的经过司法人员依法打造的能够独立证明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据体系。因此,环环相扣的证据材料,赋予了证据链足以证明案件全部事实的证明力。
综上所述,证明标准的确立,应当形成一个切实可行、具体明确的体系。证据链的构建,让司法人员站在法律的层面,客观、全面、深入的审视和把握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案件公正的予以评判。结合贿赂犯罪中证据与证明的特点,必须从虚与实相结合的角度来解决这一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难题。
[1]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29.
[2]郎 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