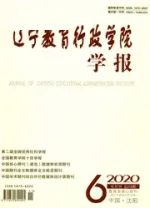北魏边疆经营与北镇问题
王明前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史学界对北魏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对北魏前期社会性质以及迁都前后均田制、三长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诸问题建树颇多,亦对北魏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过一定探研。北魏虽然统一北方,但是北面和南面分别面临游牧民族柔然和东晋南朝的军事威胁,边疆问题始终困扰着北魏统治集团。对此,学术界尚缺乏必要关注。笔者认为,边疆问题影响北魏政治的始终,并最终演化为倾覆北魏皇祚的导火线。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分别对北魏不同方向的边疆经营做条陈缕析,进而探索边疆问题的焦点北镇问题与迁都之间的关系,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北魏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北魏对西部疆土的经营
北魏对西部疆土的经营,是在先后攻灭盘踞关中及其以北地区的赫连夏,以及割据凉州的北凉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早在太宗明元帝拓拔嗣时期,河西游牧部落便不断向北魏境内迁徙。永兴三年(411年)六月,“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1](P51)神瑞元年(414年)五月,“河西胡酋刘遮、刘退孤率部落等万馀家,渡河内属”。[1](P54)神瑞二年(415年)二月,“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内附”。[1](P55)之后世祖太武帝拓拔焘夺取统万,摧毁为患多年的赫连夏政权,加之先期已从夏手中夺取长安,从而获得了历史上西部重要的关中经济区。
根据世祖“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经济策略,凉州成为北魏重要的畜牧业区,保留其原有区域经济特色。“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馀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1](P2856)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十月,北魏打败吐谷浑王慕利延后,吐谷浑贵族伏念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1](P98)吐谷浑邻近河西,又是被晋王伏罗率领的凉州驻军击败,因此这些吐谷浑民户被安置于凉州从事游牧生产的可能性更大。460年,北魏“发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猎道”,[2](P4053)是一项旨在沟通平城中心经济区与河西凉州经济联系的宏观经济行为。
在保留凉州游牧区域经济特色的同时,北魏也通过移民屯垦加强凉州的农业经济基础。对此,崔浩力谏世祖:“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1](P825)崔浩充分考虑了凉州的军事地理价值,并参考西汉成例,力主移民农垦,为凉州迅速融入北魏国家经济一体化作出贡献。袁翻则建议把内附北魏的柔然部落安置在凉州。他认为“其婆罗门(柔然部落首领名——笔者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处婆罗门,于事为便,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宜遣一良将,加以配衣,仍令监护婆罗门。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他预计:“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损,岁终大计,其利实多”,[1](P1542-1543)从而实现实边、抚民兼顾的综合效益。北魏夺取上邽后,刘洁“抚慰秦陇,秋毫无犯,人皆安业。世祖将发陇右骑卒东伐高丽。洁进曰:陇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赐优复以饶实之。兵马足食,然后可用。世祖深纳之”。[1](P688)高祖孝文帝元宏延兴年间,朝议欲废敦煌之戍“,欲移就凉州”。韩秀力排众议,表示:“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馀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1](P953)以上地方官员的施政思路均与崔浩相仿,追求农垦实边的政治与经济效益。
北魏屯田条件相当恶劣,如不能实现自给,则需内地物资支.。这就使运输问题显得十分棘手。蒲古律镇将刁雍建议以船运代陆运,提高运输效益。泰常七年(422年)他上表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前被诏,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栗,溯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1](P868)刁雍对蒲古律镇有一整套严谨的农垦方案。他事先对水文、山川地理状况做了翔实的调查后,上书请求在富平艾山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他指出:“夫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狭小,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讫。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馀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赡。”鉴于“平地积谷,实难守护”的窘境,他建议:“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镇自建立,更不烦官。又于三时之隙,不令废农。一岁,二岁不讫,三岁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陆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办”。[1](P867~869)当然,在处置柔然的问题上,北魏也曾有过重大失误。如永平元年(508年),朝廷拟议迁徙显祖时安置在高平、蒲骨律二镇的柔然降户千余至淮北。太仆卿杨椿引前例“先朝处之边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别异华戎也。今新附之户甚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驱之使叛也”。他提醒朝廷:“且此属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歼尽”。[2](P4585)事实不幸果然如杨椿所料。
关中地区虽然在前秦、后秦时期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是在被赫连夏占据后,经济逐渐凋敝,直到北魏攻灭夏政权后才得以逐步恢复。世宗宣武帝元恪时,华州刺史元燮上书建议选择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冯翊古城取代李润堡,理由是前者和洛阳之间有更便利的水路交通优势。他陈述道:“窃见冯翊古城,羌魏两民之交,许洛水陆之际,先汉之左辅,皇魏之右翼,形胜名都,实惟西蕃奥府。今州之所在,岂唯非旧,至乃居冈饮润,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譐誻明昏,有亏礼教。未若冯翊,面华渭,包原泽,井浅池平,樵牧饶广。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旧雉,功省力易,人各为己,不以为劳。”[1](P518)尉拨“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各庐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1](P729)可是,至孝文帝时,关中形势仍不稳固。“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1](P1048)北魏为稳定洛阳中心经济区,对关中从安全角度大力经营。永熙(533年)二年,贺拔岳任都督雍华北华等二十二诸军事,“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部趣泾州平凉西界,布营数十里,使诸军士田殖泾州”。[1](P1783~1784)
二、北魏对沿南朝边境州郡的经略
北魏对沿南朝边境的经略,在南北朝纷争的时局背景下,自然以军事屯垦为主要行政方向。北魏考虑到“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统治成本高昂。于是“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1](P2858)而这必然要求北魏必须事先关注战略据点的选择,因为这一战略据点其实也正是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
淮南是北魏从南朝夺取的新疆土。景明四年(503年),任城王元澄上表陈述寿阳对经略淮南的利害。他指出:“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溢以灌淮南诸戍。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首秋大集,应机经略,虽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无虞矣。”之后世宗下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2](P4530)高闾则进一步指出:“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长,救.实难。忠勇虽奋,事不可济。淮阴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且安土乐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军还之后,恐为敌擒。”他进而建议:“降附之民及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进兵临淮,速渡士卒,班师还京。踵太武之成规,营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敌衅,布德以怀远人,使中国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镇,自效可期。”[1](P1207~1208)高闾旨在提醒孝文帝,当前尚无充足实力经略淮南,因此斯时迁徙淮南兵民于淮北以图再举更为明智。而且从景明四年(503年)六月朝廷“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1](P196)来看,北魏对边境地区的经略除就地屯田外,尚需经常从内地调拨人畜加以充实。
北魏在淮南大力兴办军事屯田,对巩固迁都后的河南经济中心区具有战略屏障意义。范绍任郢州义阳郡太守,“值朝廷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1](P1756)正始元年(504年)九月,世宗“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馀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也”。[1](P198)
地处西南边境的雍州,政治军事环境复杂多变,因此北魏强调军事屯垦,以巩固边境安全。显祖献文帝拓拔弘时,刘藻任北地太守,“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藻书其名籍,收其赋税,朝廷嘉之”。[1](P1549)孝文帝时,崔亮任雍州刺史,“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1](P1481)仇池是长期独立于南北朝的氐族聚居区,叛服无常。皮喜任仇池镇将,“申恩布惠,夷人大悦,酋帅强奴子等各率户归附,於是置广业、固道二郡以居之”。孝文帝也十分重视仇池的战略地理位置。他认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 险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觇之徒,绝其侥幸。勉勤戎务,绥静新俗,怀民安土。”[1](P1132~1133)但至正光年间,“仇池武兴群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运久绝”。直到张普惠任西道行台,“至南秦,停岐、泾、华、雍、豳、东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统;令送租兵连营接栅,相继而进,运租车驴,随机输转”,[1]1741形势才稍有好转。南秦州情形类似。杜纂“诣赭阳、武阴二郡,课种公田,随供军费”。[1](P1905)正始四年(507年),北魏“开斜谷旧道”,[2](P4574)以沟通梁、益州与内地的联系。
东南边境的青州,先后处于南燕和刘宋统治之下。纳入北魏版图后,得到大力经营。泰常八年(423年),北魏攻克青州,“魏军至,无所得食”。世祖派刁雍为青州刺史。刁雍“抚慰士民,皆送租供军”。[2](P3753)太和七年(483)正月,孝文帝“诏青齐光东徐四州之民,户运仓粟二十石,送瑕丘琅邪,复租算一年”,[1](P152)用丰荒互赡的办法调剂地区经济交流。
北魏对徐州的经略,仍然以军事屯垦为主要方向。但是,由于鞭长莫及,起初效果并不理想。“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府,任其私用,常苦饥寒”。彭城镇将薛虎子建议在徐州屯田,认为“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馀兵尚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1](P996~997)此议深得孝文帝赞赏。同时也可证明最初北魏对边镇的经略更多采用的是从内地抽丁实边的办法。此外,李彦任徐州刺史,“延昌二年(513年)夏,会大霖雨,川渎皆溢。彦相水陆形势,随便疏通,得无淹渍之害”。[1](P889)崔鉴任东徐州刺史,“于州内冶铜以为农具,兵民获利”。[1](P1103)
总体而言,直到世宗时南部边地与内地的整合仍不成功。卢昶反映:“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各地自身经济基础不稳固,自然难以保证各经济区域整合的成果。正始元年(504年)崔光痛陈:“义阳屯师,盛夏未返;荆蛮狡猾,征人淹次。东州转输,往多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北方霜降,蚕妇辍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1](P1489)
三、北魏长城的修筑
为保卫北部边境免遭柔然侵犯,捍卫农耕文明成果,北魏继承历代中原王朝传统,致力于长城的修筑。太宗泰常八年(423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1](P63)孝文帝时,源贺提出在筑长城的同时辅以屯田的北疆防御策略。他建议:“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廷恒有北顾之虑也”。[1](P922)可惜此议未能通过。而持同议的源怀经过不懈努力,终获朝廷认可。他请求世宗“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1](P928)同时,北魏对北邻柔然的内附要求欣然接受。宗室拓拔孚建议:“借其所闲地,听使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以见保卫。驭以宽仁,縻以久策”。[1](P426)这当然比修筑长城的政治成本要低。长城的修筑为北魏农业经济的转型构筑了外围屏障。“建筑长城和拓拔化农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长城本身意义,就是分隔草原与中原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象征”。[3](P37)
尽管北镇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但其经济生活一旦与内地隔绝,不仅会损害北镇的经济基础,更会危害国家安全。因此,有识之士呼吁朝廷重视北镇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问题。高闾首先肯定长城有五大利处:“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1](P1202)他进而建议:“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开云中马城之食以赈恤之,足以感德,致力边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其处。开关驰禁,薄税贱籴,以消其费。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赡。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1](P1205~1206)同时,均田制也未贯彻到边地。“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馀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1](P1539)
四、北镇与迁都问题
北镇本来是维护平城中心经济区安全的屏障。平城时代,北魏对北镇十分重视。神鹿二年(429年),世祖“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刘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2](P3812)世祖时,赵逸任赤城镇将,“绥和荒服,十有余年,百姓安之”。[1](P1145)但是到孝文帝时,北镇经济问题已很严重,尤以粮食缺乏为甚。因此,为稳固北部边境的经济基础,高闾建议:“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楯,二万人专习骑矟,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七月发六部兵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分散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1](P1201~1202)这其实仍然是采用军事屯垦方法解决北镇的军粮问题,力求经济自给。
尽管历史传统和北魏自身实践均证明军事屯垦是解决边境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北镇与伊洛社会组织不同。迁于洛阳的北人早已成为编民,中国传统的宗法组织成为他们的社会组织,但北镇却不相同,除一部分编民外,更多的是府户、部落与罪人”。[4](P154)这使鲜卑人在迁都后由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而必然出现族群分化。结果,迁都后北境经济发展滞后于南部。“北边荒远,因以饥馑,百姓困弊”。[2](P4533)特别是北魏朝廷因迁都和汉化,对北镇问题的态度早已不如平城时期那样重视。“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1](P430)源怀则上表反映均田制在北镇落实不力的弊病:“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灾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以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馀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1](P926)
为此,北魏朝廷对北镇居民极力安抚。肃宗时,“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郦)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1](1925)这是迁洛后的北魏对六镇的一次区域经济整合努力,试图给予六镇与内地一样的政治待遇。熙平二年(517年)十月,诏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1](P226)这些都试图协调南迁洛阳后原平城中心区与洛阳新中心区之间的关系。北魏朝廷此诏表面上表示并不因迁都而偏废旧都,希望未迁者“安堵永业”,但是两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迥异,加之政治中心随迁都而南移,国家经济整合的基点和重心也必然相应南移。
孝文帝以果敢的决心强制推行汉化,迁都洛阳,改姓易服,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事件,为后世史学家高度肯定。其实,通过上述分析,孝文帝迁都的时机并不十分成熟。因为北魏经济尚处于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中,北境虽然通过长城的修筑和自身的军事实力阻挡了柔然的袭扰,但是南部与南朝边境地区的拉锯局面仍然使疆土变动不定。孝文帝以“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1](P359)的理由迁都,如果作为选择可以进一步促进各经济区域整合的新重心,本身并非不明智,但是迁都后孝文帝仍然不断南伐的举动则充分证明,孝文帝迁都与汉化的最主要动机并不是致力于巩固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成果,以洛阳为中心致力于境内各经济区域的整合,而是以洛阳为跳板南下实现统一。孝文帝的国家行政意识过于超前,在并未充分巩固和消化生产方式转化成果的条件下,便把南征作为主要任务,这至少不是最佳选择。其实,北魏经过世祖到孝文帝几代帝王对南朝的持续用兵,特别是趁南朝宋齐交替之际,凭借本来就占有的军事优势,陆续将青、齐、徐、兖诸州和淮北、淮南纳入版图,更加强了北魏的地缘政治优势。北魏所需要的是在充分实现自身各经济区域的整合,以提高其综合经济基础特别是主体农业经济的基础的同时,等待南朝政局出现可资利用的变局。而北魏计不出此。孝文帝南迁后想利用南朝齐梁交替之际不断南征,虽然有局部胜利,但是斯时南朝局势迅速稳定,而北魏自己反而延误了促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时机。孝文帝去世后,由于汉化进程过于急进,代北和迁洛鲜卑人逐渐发生族群分化,北部边境屏障自我坍塌。北魏终于尝到了边疆问题处理不当的苦果。
综上所述,边疆问题影响北魏政治始终。虽然北魏的边疆经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由于北魏经济尚处于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中,不仅南部与南朝边境地区的拉锯局面仍然使疆土变动不定,而且北镇问题因孝文帝汉化进程过于急进而激化,并最终演化为倾覆北魏皇祚的导火线。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孙同勋.拓拔氏的汉化[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