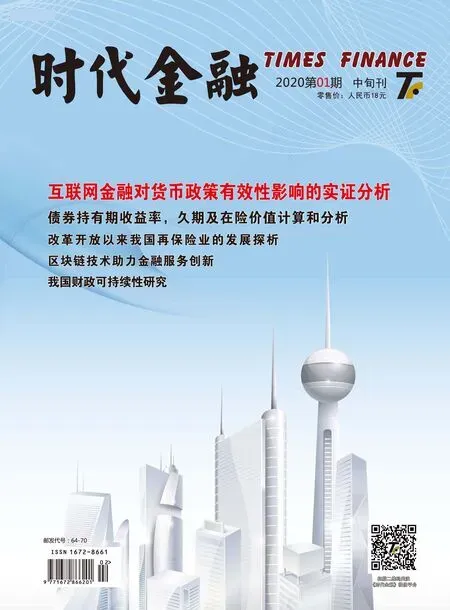中国酒文化的自虐性
文唐学鹏
当政府和军队开始收紧酒消费之后,茅台为代表的酒行业股票大跌,近日,解放军报发文说《不喝酒并不伤感情》,意思是军队不要将喝酒当做拉近关系和感情的一种行为。
酒文化好像被认为是中国的古韵之一,但中国的人均酒精消费其实并不高,清朝时的传教士就发现,中国人有酒士但无酒鬼,餐酒传统不显著,酒桌文化很醒目,大家会凑热闹,一起故意将人灌醉。但自己没事吃饭不会抿个小酒。即使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酒精消费依然不是“强国”,主要原因是没有餐酒传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费酒精大约4.21升,美国酒精消费是8.44升——这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很一般的水平,但足足比中国高了一倍。
全世界最高的酒精消费水平都是有着餐酒文化传统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是11.03升,捷克高达14.97升,法国德国奥地利和白俄罗斯是一个层级,大约都在11升附近,连亚洲的韩国都有11.8升。很显然,高丽人的餐酒文化传统比中国要高,当然有人说,因为韩国人冬天冷的时间长,需要没事来点小酒御寒。但是暖和的泰国有6.37,非洲的尼日利亚和乌干达都有9.78和10.93。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人其实是不好酒的。
中国人不好酒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女人的酗酒率,这个数据基本可以证明一个国家是否真的爱喝酒。日本、泰国和韩国的女人酗酒率都比中国高。女人的体内水分比男人少,在饮用同量的酒精后,女人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会比男人高,所以女人如果真的爱喝,她们有着比男人更高的酒精依赖。女酒鬼出产比较多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餐酒文化非常盛行的国家。
另外一个试验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所做的调查,他们对华人移民到加拿大之后的酒精消费感兴趣,发现跟国内相比,这些中国人的酒精消费大减,降低幅度甚至高达70%。原因很简单,这些中国人在国内都是有身份的人,应酬很多,但搬到加拿大之后,没有多少熟人,适应了国外那种不咸不淡的人际关系,酒桌减少了很多,跟在加拿大的韩国人不同,他们又没有餐酒文化传统,所以导致华人移民的酒精消费量大减。
虽然中国人不好酒,但是爱劝酒,没有像俄罗斯一样盛产大量酒鬼,但盛产大量居心叵测的劝酒士,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跟俄罗斯人相比,大部分中国人其实不觉得酒是好东西,不需要抢着喝。那么为什么爱劝酒呢?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伤害性建立社会资本”的游戏规则,这可以算是一种“投名状文化”:你必须通过某种伤残自身的方式来显示诚意,如果双方都显示诚意,那么就一起醉吧!
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曾经描述过多种社会资本建立的途径,比如同一宗教、同乡同口音、同一幼儿园的家长……但是他没法想象到有一种“酒精侵害性社会资本”的文化,如果不能喝酒的人愿意冒着头疼脑裂风险醉酒一场,那么他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进入了诚意的门槛。
中国社会长期是层级社会,是没有个人主义传统的,个人必须社区化或者官僚科层化生存。对于底层人来说,他们需要某种身体上的受损付出以获得信任,而对于高层来说,他们顾忌的是面子,但愿意用自己的“出丑”来获得信任。那么酒桌的酒精文化则完美地满足了这两点,酒精既可以伤害人的躯体,同时醉酒也容易出丑,酒精是一个完美的“统筹物”。在当下中国,军队是最严格的等级化组织,而商场官场则是科层化社会,乙方有求于甲方,下级献媚于上级。而在酒桌文化之后,中国人是厌恶喝酒的,他们大部分不愿意将酒精延续到家庭餐桌。
几乎餐酒文化传统都有限制酒精的各种文化或者势力,比如宗教。正儿八经的宗教基本上都是禁酒的,认为酒精消费是有罪的,虽然基督教有圣餐酒,那是一种缀饮,将酒看做是耶稣的血。伊斯兰对酒的禁止更是严酷,甚至严厉过猪肉的不洁。印度教也是讨厌酒的,但因为有“酒入药”的传统——韦陀医学认为酒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作为一种治疗的辅助,但印度教总体上是否定“酒入药”以外的饮酒;就连鼓励多妻制有点淫荡色彩的摩门教也是限制酒精消费的。
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没有对酒精限制的文化,本土的儒家没有道家没有,连中国改良的佛教在唐朝鼎盛时期,都没有向全社会推广禁酒的立场。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本质上不好酒,酗酒不是个大问题,也没必要禁酒。中国人将酒作为“伤害性建立社会资本”的手段,中国人的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却热衷提高至与身体素质不匹配的烈度水准。中国的酒传统是一种有点变态的“社交江湖机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