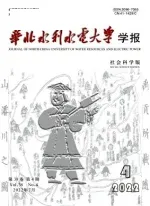齐泽克视野下《金色笔记》中女性主体的建构
杨新立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在谈到社会性别建构问题时,著名法国哲学家拉康提出了“女性并不存在”的思想,认为任何说话的存在物都可以潜意识地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进入性身份定位结构中,女性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由,完成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建构[1]。这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的论断契合。女性主体的建构也为众多文学家所关注,成为诸多文学经典的主题。2007年诺奖作家、英国人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就探讨了女性克服意识形态压制自我建构的历程。
莱辛的小说并没有仅仅囿于探讨两性关系,她着眼于更为宏大的主题,着力描述女性在更浩繁的社会场景中的主体性建构。在更广阔的语域下,如果你“选择活下去,那么你选择的是整个世界(即堆积在你眼前的、有着各种奇观和痛苦的世界)”[2](P300)。《金色笔记》讲述的就是女作家安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包罗万象、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下,追求“自由女性”梦想的经历。小说主要由黑、红、黄、蓝四个颜色的笔记本和穿插其间的小说《自由女性》组成。四个颜色的笔记本分别承载某种社会符号秩序,内置小说“自由女性”穿插于四本笔记之间,彰显了女性主体的建构受到意识形态的重重束缚。
自由女性面对的重重符号秩序凸显了意识形态对实在界的压抑,所以,主体建构的过程也是主体被符号化的过程。在齐泽克看来,主体性建构的意义就在于自我不被某种一致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而是体验为我所在的独特性和特殊性[3]。齐泽克关于实在界和符号秩序的论述,构成解读《金色笔记》的潜文本。作为拉康的追随者,齐泽克极大地拓展了拉康关于主体建构的学说。
一、安娜◇自由
拉康的幻象公式S|◇a在《金色笔记》里可以表述为:安娜◇自由,即安娜觊觎自由。这完整地诠释了《金色笔记》的主旨内容,彰显了“自由女性”梦想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题。公式左边的安娜是被打上斜杠的S|,即被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公式右边的自由,是欲望的对象——原因,也就是欲望对象所以出现的成因;中间的小菱形◇是幻象框架,它隔开了主体和对象a,使主体与对象a相安无事[4]。意识形态幻象为安娜的欲望提供框架,也由此将其“自由女性”的梦想包裹在符指网络内。
小说中黑、红、黄、蓝四种颜色笔记本物化了安娜必须面对的意识形态网络,即殖民主义、苏式共产主义、男权思想等权力话语,是意识形态在种族关系、政治秩序、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演绎。《自由女性》穿插于四色笔记之间,象征“自由女性”梦想是主体横贯始终的追求,也意味着“自由女性”欲望为意识形态建构,被意识形态的符指化力量所包裹。红色笔记记载了安娜最初带着无限热情投身于苏联式共产主义,坚信其能够真正地解决人性的自由,从根本上解决自由所面临的窘境。而黄色笔记中的安娜,最初则梦想着爱情和正常的家庭机制,能给予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在黑色笔记的内置小说里,安娜开篇就描绘了爱情跨越种族殖民语言、不同肤色的人自由相爱的童话世界。被虚无幻象建构的安娜以为,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她可以实现自己“自由女性”之梦,获得理想化主体身份。
二、“自由女性”实在界被压制
“幻象是‘表现欲望之实现的想象的场景’,回答了‘Che vuoi(你到底想怎么样)’的问题。”[5](P118)四本笔记所承载的符号秩序,为安娜分别提供了在殖民、政治话语、两性关系和精神生活中,自由梦想实现的坐标系和框架,这也就回答了安娜“想怎么样”的问题。主体被意识形态建构成S|,她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反倒由此被掩盖了起来。意识形态就是要构建一个没有对抗性分裂的社会,通过意识形态幻象来掩盖实在界与符号秩序间的分裂缝隙,制造统一、整合的社会安全感。因此,主体建构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对实在界压制的过程。
作为作家,安娜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独特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作为女性,她又必须面对男权话语和传统家庭机制对于她的妻子和母亲角色的质询。实在界与传统符号秩序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她与丈夫的婚姻和与迈克尔的情爱,都是她屈从意识形态、试图在符号体系内建构自己的方式。她希望通过融入传统机制,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事实上,无论她选择丈夫还是迈克尔,意识形态都成功地压制了她对自由的追求,把她缝合在符号体系上,成为意识形态幻象的组成,为社会营造了统一安全感。意识形态和自由女性实在界之间的对抗性裂缝,也以此得以掩饰。
女性建构主体性的过程中,既要面对男权话语的束缚,也要克服种族殖民秩序的阻隔。黑色笔记中安娜的小说《战争边缘》、《战争笔记》描写的跨越种族的爱情童话,就彰显了阻碍主体自我建构的种族殖民话语。故事中餐馆的白人女老板、她的女儿乃至整个白人社区,都对自己肤色有一种天然的骄傲认同;而故事里的几乎所有黑人女主角对种族歧视话语都缄默无语,更是彰显了“白人至上”作为普遍性语言的符指化力量。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跨种族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保罗对自己与黑人女友的故事噤若寒蝉;皮特被迫回国,黑人女友沦为妓女。意识形态企图用这样严厉的语言驯服主体,遮蔽寻求自由爱情的实在界,掩饰种族殖民话语造成的社会问题。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性别歧视、社会危机等问题,安娜意识到政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她以为苏联式共产主义这一新的政治话语是使人性解放的新的宏大方案,但党内的官僚主义、同志间相互的攻讦以及残酷的权力斗争,证明这种政治秩序不能为人们提供任何意义的自由,反而演变为套在脖颈上新的枷锁。这个新的政治话语成为对安娜“自由女性”梦想的嘲讽。安娜在旧秩序中建构自我的失败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自由女性”梦想也不可能在这虚幻的框架下获得成功。
三、“自由女性”实在界的入侵
社会是由实在界与意识形态这两个矛盾冲突构成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社会为抵御实在界入侵而建构的一套谎言,因此,实在界“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裂变的可能性,随时都会穿透符号界而现身”[4]。安娜在旧秩序中安置自我的失败,使她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本质。四本笔记中貌似强大的政治体制和男权话语等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只是实在界与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脆弱而易碎的平衡而已。一旦实在界的创伤以偶然的方式爆发,那么,穿透意识形态谎言的“自由女性”就会迅速突破意识形态封锁,吞没社会现实,使其土崩瓦解。
《金色笔记》中安娜的怪梦表现了实在界对意识形态的穿透。在梦中,安娜看见自己成了一个坐在笼子里的儿童,而索尔则变成一只趴在笼顶的老虎,警示下面的儿童不能逃出笼子。安娜随后又梦到索尔成了自己人生故事的放映员,对她的生活秩序颐指气使。笼子象征着束缚“自由女性”的意识形态网络,索尔的意象被凝缩成趴在笼顶警戒的老虎以及安娜人生故事的放映员,则隐喻索尔成为意识形态的象征并为其张目,试图做安娜“内在的良心或评判者”[6](P656)。
梦是欲望的实在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遭遇欲望的实在界[4]。安娜在梦中看清了自己“自由女性”的欲望,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要破笼而出的儿童,她由此确定了自己前面的道路和目标。梦的出现也印证了社会现实的脆弱性,“自由女性”执着的实在界轻松地穿破了意识形态谎言的遮蔽。安娜不想再挣扎于旧的政治和两性关系秩序内,而要选择新的实现理想化主体身份之途。
精神分析学把意识形态质询的失败称为歇斯底里。意识形态对安娜质询的自以为是引发了主体的歇斯底里——为什么我得服从于男权秩序(种族话语、权力话语)?由此,安娜在梦醒后突然决定断绝与索尔的关系,歇斯底里地要求索尔离开,以免他会把自己和女儿简娜特看作被凝视的对象。安娜的果断行动也印证了齐泽克的论断:正常人只有成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主体,用突如其来的行动彻底悬置旧秩序,才能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让主体的建构成为可能[3]。
四、认同病症,建构新型女性主体
要彻底摆脱阻碍自我建构的束缚,安娜要做的首先就是认同病症(identify with the symptom),也就是说从少数派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的个别中,发现普遍性的东西,“认同例外中存在的内在合理性”[3]。安娜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凝视下,是旧的政治秩序和性别秩序中的一个少数派。要想将其少数派的特殊性认同为真正的普遍性,安娜只有悬置旧秩序,从局外人/多余人的角度建立新的符号秩序,才能创建新的不可能性社会历史空间。
文学创作能够赋予混乱以秩序,是对旧秩序的摒弃和新秩序的创建,实际上就是一种重组历史经验的“实在行动”。安娜最终克服障碍开始新的创作,正是齐泽克式的革新行动。承载压抑性旧秩序的四色笔记本得以终结,安娜从混乱的旧体制约束中解脱,新的秩序逐步取代了旧的混乱。金色笔记既是四本旧笔记的结束,又预示了《自由女性》新历史经验的开端。索尔给这本新作品预写的第一句话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新小说以对两个单身母亲的聚焦开篇,表明新秩序对所谓少数派的关注,这本身就是新秩序的建立。
索尔虽然是旧符号秩序的构成,但他对安娜的了解,使他洞察到安娜特立独行的价值观。他因此建议安娜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她的新小说,重启她的写作事业,“自由女性”的理念由此成为安娜新小说和新生活中的符号秩序,《自由女性》也成为她女性主体地位的象征。安娜的新生活秩序由她的男性理解者索尔启动,作者由此巧妙地传达了她在两性关系方面建构“自由女性”的理念。
《自由女性》的结尾,安娜与选择婚姻来安置自我的旧友莫莉吻别。她彻底地悬置了旧的符号秩序,建构了一条颠覆性的“第三性”道路。安娜的选择证明,只有彻底地摆脱旧符号界的纠葛,果断地实施行动,女性才能获得自我建构的成功。
五、结语
《金色笔记》展示了女性在意识形态网络的符指化力量下,进行主体性建构的历程。“自由女性”主体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和实在界的矛盾对抗过程。“自由女性”在意识形态网络的压抑下左支右绌,但社会的内在矛盾性组成决定了其外强中干的实质。一旦实在界以不可预知的方式透出,“自由女性”的实在界就穿破意识形态的重重封锁,社会现实迅速土崩瓦解。安娜从少数派个别中,发现了一条自己独特的主体建构之路。安娜独特的自我建构之路,也印证了拉康的“女性不存在”的社会性别建构论断。《金色笔记》中的女性主体构建历程,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每个独特个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吴芳.西方男性学者视角下的女性主义[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美]福柯·米歇尔.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韩振江.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齐泽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4]李西祥.社会现实的解构:幻象、现实、实在界[J].现代哲学,2012,(4).
[5][斯洛文尼亚]Zizek,Slavoj.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London,Newyork:Verso,1989.
[6][英]莱辛·多丽丝.金色笔记[M].陈才宇,刘新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