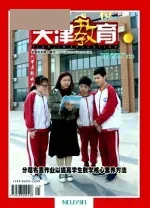创新人才的培养
■杨玉良
非常高兴来到南开中学,今天,我首先想谈现在的人才培养问题。有一段时间,我说过一句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听的话,我说,现在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批评,尤其是对大学的批评成为一种高级的舆论。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教育家,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对其他不懂,但是对教育总会懂,因为自己受过教育,或者是自己的子女正在受教育。所以对教育的评价就显得非常轻率。看到问题多,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少。我说这个话,绝对不是否认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大学教育,包括复旦大学。所以我今天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教育跟在座的各位同学密切相关,此时你们的脑子里可能会冒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要上大学”,二是“上大学,到底应该读怎样的专业”。对第一个问题,有相当多的同学会说:我中学念完了,总归要上大学;或者说我父母亲要我上大学;或者我亲戚们觉得我成绩不错,所以我应该考一所重点大学。这是受你的家庭社会的影响。至于选择什么专业,那就更加受社会、家庭的影响了。
现在好多学校的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等应用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其招生数量占到一所学校(大学)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这些专业都不是直接产生效益的专业。它很重要,我一点都不贬低它,但是一个国家对于各种不同专业的人才,是要求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架构的。如果人人都当小说家的话,就会没有读者,因为大家都是写小说的。如果人人都学管理的话,你来管什么,到最后连自己都管不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的,每一个学生选择取向要根据他自己的兴趣、他对自己能力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需求,综合做出这个抉择。但现实是,人们往往受社会的影响,比如说大家看到银行家赚钱很多,所以大家要学金融;但是你知道所有学金融的人里头,真正赚了钱的是多少?大家知道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他的一辈子是到快死了的时候才赚了一点钱。
说句实话,我对当前的大学也不满意。我觉得当前的大学,功利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中最没有功利意识的地方,可是当前,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学生,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
我们回到人类最早的时候——轴心时代,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候,古希腊出了一大批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同样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先秦时期,我们出了诸子百家。其实即使在那么早的时候,人们对教育也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教育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让一个人真正地成为一个人。就是说,要让老师带领学生、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是说再加上一种独立学习的能力。
我在昨天来的飞机上看到《文汇报》上一篇书评,介绍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教育的书。他的主要思想是说,21世纪教育的重心,将从“教制”转移到“学制”上。我觉得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如果你了解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早期的教育思想的话,它们早就阐述过。大家去看《论语》里头,这个“教”字出现的频率极低,而出现的基本上是“学”字。所以你就知道教育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自己学,是老师教会你怎么学,而不是教会你某一个知识。一直到《孟子》,再到后来的程朱理学,你才看到他们的书和文章中会出现这个“训”字,教训的“训”字。
这种历史发展不仅仅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英国的罗素就讲过,他把教育分两大类型:一种类型属于国民教育,另外一种类型是军事教育,就是军校的教育。这两种教育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两种教育是必须分开的,因为军队的教育要求是要训练学生,第一是服从命令,第二是严格执行命令,不能有偏差。要把一万个人、十万个人训练成像一个人的样子,那么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就会非常强,这是军队的教育。所以军队的教育要用这个“训”字,也就是训练、教训的“训”字。但是国民教育主要是学,国民教育是让学生学会怎么样去学习东西,这样它就成为终身的一个基本能力。
我们培养学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告诉学生,你需要自己管理自己,尤其是在大学里,这是我们的老校长李登辉任校长的时候,复旦大学最大的特色。但是如今,在这方面我们很多高校做得还不够好,我们也在力图改进它。
我想引用南开中学的校友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如果你对学生的人格不尊重,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别人的人格也不会太尊重。另外一句话是,要保证学生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我非常赞成温家宝总理的观点。学生如果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就完全是一个承受教育的机器,往学生思想里头塞教育,就跟你计算机上一个硬盘差不多,或者跟移动硬盘差不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教育肯定会失败,因为他们只会懂得什么叫服从,他们失去了自我。
所以我们经常讲,要教育学生只向真理低头,对所有的权贵或者有钱、有什么的人,是不应该低头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本源,也就是说他有着独立的人格。但实际情况离我们一直的要求,差得还很远。正因为这个目的,复旦大学就在几年前开始做了一些教育教学的改革。我认为,“通识教育”是一个方向。
对“通识教育”还有人有着很多误解,认为“通识教育”就是给你一个比较宽广的知识基础。错了!宽广的知识基础你可以听《百家讲坛》,宽广的知识基础你可以去看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那里什么都有。
“通识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好像你什么都懂一点,不是;“通识教育”更加不是培养那些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真正思想、且不会真正干事情的人;“通识教育”更加不是给你填充了某些东西,让你去投机钻营当什么官员的。“通识教育”实际上是要给学生塑造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当今社会非常缺乏的。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必须具备两种精神:第一是人文精神,要体现出对人类的关怀;第二是科学精神,要体现求真这样一种精神。因为只有同时具有这两种精神,才会真正地做到只会向真理低头,才会崇尚真理。因为人文精神的主要核心就是一个善、一个美,求真善美的善和美;科学精神就是求真。所以“通识教育”就是要把这两种精神告诉学生,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大家就有可能会问,你是不是提出一些新的东西了?不,这在以前就有,包括南开中学在历史上也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过,中国的教育改革,大家叫改革,当然改革很重要,改革永远是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某些方面,恐怕重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回归,回归到我们应有的传统上,回归到中国教育包括古代一直到近代的优秀教育家们早就认识到、早就做过,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教育思想上。
“通识教育”首先是要给学生一种精神,但“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不是对立的。可能一个技术类的学校在教一种物理课的时候,更多地教会你怎么去解题目,但是你所依据的公式是怎么来的,你可能并不知道。这种教育有一个优点,它很实用;也有一个缺点,它会导致一种对前人的盲目崇拜。我问过一个大学物理系毕业、现在读研究生的学生,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是怎么来的?他回答不出来,我说老师没教你啊?他说没有讲过,但他能马上写出薛定谔方程来,我说你想过没有这个方程是怎么来的,他说他也想过,他觉得那个年代薛定谔这些人真伟大,怎么能把这么复杂的方程想出来。所以你看,在他的脑子里这些东西就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跟这个学生引用当时的一句话,在量子力学创立的年代,哪怕是三流的、最差的学生,也可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因为在那个时代,你只要做一点点工作,就能够成为世界著名的人,这是历史的机会。所以只要你仔细研究他的背景的话,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薛定谔能导出这个方程。你也行,他也行,只要你想到了就行。除此之外,你也把他所学学科的思想发展史告诉他的话,那么他不仅仅会解题,还会解得更加精妙,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创新的思想。
我们创新的动力,人们都说是社会环境对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是你注意,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影响中国人创新能力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前人对我们的影响。中国人好说古人怎么说,这是对的,古人的经验很重要,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会让你觉得古人很权威,所以你发展不了。你如果去读量子力学,就会发现好像我们现在没办法,前人那么聪明,我们已经没机会了。所以,前人的东西对你现在的创新也是一个巨大的限制。你一定要用“通识教育”的理念教这些专业课,把学科的个案史、思想发展史等等告诉学生,学生才会感觉到:这并不稀奇,我也可以做,只不过在现代这个时代下,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应该以某个方式去做。这就是我澄清的一个思想,“通识教育”不是跟专业教育对立起来,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教育理念下面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
这是复旦大学,我们在思索。
“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把寝室转化成为一个学习和培养能力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个睡觉休息的地方。复旦大学根据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方式,结合西方发展很多年的“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的经验来建立复旦的书院。复旦的书院有这样一个特点,书院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我指的活动空间不是体育活动空间,而是大家开小型讨论会、跟导师进行对话的空间。书院里有自己的图书资料室,可以建立各种读书会,大家交流读书的经验。我们将大量的各个专业的老师分派进去,做学生的导师,然后让书院真正成为一个课堂之外更加重要的课堂,书院要形成自己的文化。书院的活动,主要是要让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未来需要怎么样的人。北大的张维迎教授写过一本书,书里有几句话我引用一下。他说,一个大学校长要考虑的问题必须是10至20年以后的事情,你不能仅仅看现在。因为现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人,15至20年以后必定是一个国家的栋梁,必定是一个国家的骨干力量,这是一个你绕不开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大学校长要考虑后面到底怎么样,国家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人。
我们现在培养的人,到了20年以后,可能40岁出点儿头,应该是世界上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我们现在这种培养人的方式到那个时候能不能够满足对人才的需求呢?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能和国家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呢?注意,我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政治家,而是各方面的人。我觉得五四时期,当时我们中学、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使得我们国家的发展尽管在近代受尽了各种磨难,但是仍然能够快速起飞。我认为,20年以后,中国肯定不得不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就此而言,如果概括一下,我们培养的人,我觉得有几个基本要求:第一,他必须对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有所了解。第二,他必须对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第三,他必须对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有足够的宽容度。西方有一个问题,它认为它的文化是最优越的,中国人可不要犯这个错误。世界上的文化必须是多元的,如果这个地球上只有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话,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灭绝的。文化有点像基因一样,要不断地杂交产生一些新的物种,所以单元文化是有问题的。我一直批评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他写过一部《文明冲突论》,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文化冲突,这本书里的思想就成为美国在最近几十年来整个国际方针的基本理论依据,但他只强调了文化冲突,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方面是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创新。所以你必须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容忍。第四,在这些问题上,他必须有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基本要求,但这些基本要求实际上已经非常高,你要能够在人家说一句话时理解在他的背景下要说这句话,即使你是一个化学家,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化学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你可能只是自己国家里比较优秀的化学家。所以,做一个更加完整的而不是科学研究机器式的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专业人员,你同样必须具备以上的四个基础。
这四个基础做到很不容易,当然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除此之外,你必须学会用合适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很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思维方式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过度的偏激,要么就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这从很多媒体文章上都看得出来,所以你必须掌握一个合适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当然是基于自己的知识基础,而且你必须学会不断学习的能力。然后我想,有了高雅的精神气质——崇尚真理,有了你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宽容和学习对话能力,有了把各种专业知识的基础作为自己工作的思维基础和你能游刃有余的工作手段,这样,不管你是在哪个行业工作,只要具有这些综合素质,就一定能够成为杰出的人物,一定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未来。这个问题可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因为任何偏激、任何简单的专业思想都会出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世界上的原子弹如果同时爆炸,可以把这个地球至少毁灭30次,所以这是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所面临的挑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的学生、一个国民,应该考虑对整个人类的贡献,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能够做出正面的贡献的话,我们的贡献必定是远远超过美国的,而且可以给整个世界展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