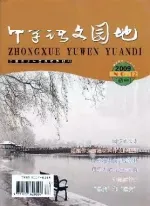诗人寂寞灵魂的象征——戴望舒《寂寞》审美意象分析
魏彦平
《寂寞》一诗中运用了“野草”这一象征性的意象,巧妙地将诗人的寂寞感形象化。寂寞感是诗人要传达和反映的情感,是概括的,典型的,但它在艺术表现上则是具体的,形象的,这种寂寞就如同“园中的野草”,“长得如我一般高”,诗人将无形的情感化为有形的意象,将抽象的情绪化为生动的具象,把诗人的情感形象化。
“野草”作为诗中的意象,它是诗人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结合而成,它是一种表意之象,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戴望舒笔下的“野草”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兴,整首诗都围绕“野草”的意象而展开。他捕捉了“野草”作为诗中贯穿性意象,也就为他力图表现的寂寞情怀找到了载体,并通过这一载体使不具象的精神性存在找到了具象的表达方式。刘熙载《艺概》中说“山之精神不写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不写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无所寄矣”,可以想象,如果诗人不是借助于“野草”的意象来传达寂寞感,那么《寂寞》一诗必然流于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
诗人一开始并没有直言“寂寞”,而是引入了“寂寞”这一意象,勾勒了一幅“园中野草渐离离”的境界。诗人望着园中的离离青草,忆起他旧时在园中“星下盘桓”的情景,可以想象的出园中遍布诗人的足迹,而如今,“野草”却从旧时的足迹中长出来,诗人旧时的足迹已被野草遮掩住了。
直到第三段“寂寞”两字才出现,“日子过去,寂寞永存,寄魂于离离的野草”。看到此,我们才感到诗人是怀着一种寂寞感在园中的“星下盘桓”,尽管诗人现在已不再到园中徘徊,但那时的寂寞并没有消减,而是随着野草的滋长寄托其中了。寂寞“寄魂于野草”,而野草却“像那些可怜的灵魂,长得如我一般高”。这种回环往复的句式,构成了“寂寞的灵魂”与“野草”之间的一对同构关系:寂寞凭借野草体现,而野草又是寂寞的负荷者,二者达到了统一。也就是说,野草作为一个意象,是诗人情感和思想的媒介,借助这一意象,表现了诗人的寂寞情怀。
诗的最后一段中,“寂寞已如我一般高”,实为一个暗喻,它仍以“野草”为中介。既然野草已“长得如我一般高”,那么“寂寞已如我一般高”也就不难理解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野草的生长,寂寞感也潜滋暗长,因此,尽管诗人已不复到园中去,但象征着寂寞的“野草”却如水随形的伴随着他,这也暗示了诗人的寂寞无所不在。
诗的最后两句“我静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让我们看出诗人在一种大寂寞的心态之中试图领悟的是自然与宇宙的沧桑恒变,体验的是一种地老天荒的亘古之感,这寄寓于“野草”中的“寂寞”是一种苍凉的寂寞。
通过以上对《寂寞》一诗的简单分析,不难发现,作为意象的“野草”是诗人对于过往形象记忆的一种重现和描绘,它是诗人“心物交融”的产物,是“人心营构之象”即艺术创造的产物,更是诗人主观的“意”和真切可感的客观的“象”的融合,诗的文本意义正是通过意象的创造而得到传达的。“象”实际上成了“意”的载体,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
思想感情和内在精神是意象所要表现的主要对象,所以作为抒情写意的文学形象,意象的特点在于化虚为实,以实显虚,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神用象通”和“拟容取心”。《寂寞》一诗中,诗人正是借用“野草”这一实物为意象,来寄寓自己某种情怀,换句话说,诗人正是把自己难以言说的寂寞感情借 “野草”而使之具象化。意象的构成由两部分,一个是主观的情欲,一个是客观物象。《寂寞》中,诗人将“寂寞感”这一主观的情寓附于“野草”这一客观存在的物象上,使得“野草”这一意象具有了心物交融,主客观相统一的特点,从而使一种浑然无形的情绪变得具体可感。
诗的世界总是通过诗人的自我来表现的。人们不能只看诗人表现的是怎样的“自我”。它是客观世界的自我反映,自我反映的还是客观世界,而不是诗人自我的唯一天地。诗人表现自我的手段是意象,用意象来直抒胸臆,因而意象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是诗人的思想与世间的万事万物,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诗人把自己灵魂中的虚幻之物,借助于真实的物象表现出来,从而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这种真实的物象也是意象。“野草”在《寂寞》一诗中就是这样一个既主观又客观,既真实又虚幻的意象。
《寂寞》一诗体现了戴望舒高超的艺术技巧。诗人为难以言传的“寂寞”找到了“野草”作为喻体,从而为不具象的精神性的存在找到了具象的表达方式。《寂寞》一诗昭示了生命的个体性,也正是借助于“野草”这一意象。在诗中,诗人并没有迅速超越开头“野草”的比喻而直接抒发寂寞感,相反,他使“野草”的比喻贯穿全诗,并且巧妙地把明喻转化为暗喻。一旦诗人多次重复运用“野草”这一意象,“野草”便超越了比喻这一层次而上升为象征——诗人寂寞的灵魂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