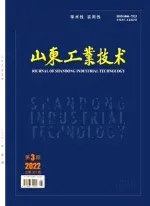中美通识教育比较分析
尹 慧
(延边大学 工学院,吉林 延边 133000)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直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在19世纪时欧美学者注意到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过于细化,专业性太强,知识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导致学生不善于独立思考,对其它的学科不涉猎,缺乏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长此以往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乃至人类的进步形成阻力。通识教育的观点在这种局面下被提出来。通识教育的构建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大学博雅教育和自由教育,其目的是首先教导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和“公民”,然后才是教授专业知识为进入社会所从事的职业奠定基础。通识教育最终目的是“育”而非“教”,不对专业进行硬性的划分,充分重视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发展方向,培养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自20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
作为通识教育起步较早的国家,美国通识教育经过百余年的实践和发展,已经总结出完整而明确的课程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知识和能力的目标;二是,培养学生人格和道德目标。通识课程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数理统计和分析能力、逻辑和批判思维能力以及综合推论能力等,还要通过理性训练、启发心智,把学生培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和有教养的人。如哈佛核心课程强调,引导学生掌握“有教养的人所必备的学识、智能以及思辨方法”,使“学生成为有教养的人”;麻省理工学院的通识课程是要“致力于使学生在科学、技术和人文基础方面得到强有力的训练和熏陶……,使他们成为非同一般的工程师、科学家、教师以及科研工作者,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领导地位”[1]。
在课程设置方面,美国顶尖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本科全部课程中占35%左右,如芝加哥大学是50%,哈佛、斯坦福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耶鲁占44%,哥伦比亚大学较低也占到20%-22%。通识教育备受重视,除了开设写作、数理统计、外语等基本技能课程外,还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领域的多门课程和科目。许多大学在通识课程内容的安排上侧重于人类最基本的知识和文化、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俄亥俄州立大学专门开设所有学生都必须选修的写作课程,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流畅、逻辑性较强的写作能力。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大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重视,使得综合课程、跨学科课程在通识课程中的比例日益提升。如美国西北技术学院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注重多学科的交叉渗透,要求学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至少修满两门课程,使学生对人类历史、人类所处的世界、人类思想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对跨学科课程极为推崇,认为跨学科课程能够巩固特定领域及学科的知识,强化批判性思考与交流能力,能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美国大学普遍设有通识教育管理机构,专门负责通识课程的规划和执行,并通过制定严格的程序和规定来确保通识课程科行而有效的实施。在课程考核方面,覆盖范围广,题型、答案灵活,考试次数多,成绩评定相对客观全面。近年来随着通识教育改革的推进,美国大学逐步以等级和文字评价来取代数字评分的做法,力求做到评定的科学、客观。新华网伦敦2005年9月16日电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美国的大学汇集了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大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44%经常被引用的论文,都出自美国的大学。在美国,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口比例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独占世界鳌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由通才教育向专业教育转变,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这种专业教育在当时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急需人才的困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专业分科过于细化的弊端开始显露,培养出来的人才基础薄弱、素质较差,适应性差。20世纪80年代末期,高校逐渐认识到拓宽专业、学科渗透、素质培养这些加强学生基础的措施更有利于毕业生进入社会后的可持续性发展[2],大学生作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对其进行通识教育显的愈加重要。
由于通识教育课程引进时间较短,我国部分高校在开设一段时间的通识教育课程后,现面临着目标不完整、结构不合理、内容不全面等困境。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大学确立了通识课程目标,如北京大学通识课程目标是“引导学生从本科教育的最基本领域中获得广泛的知识,让学生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及主要思路,从而成为能力和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和发展所必须的方法和眼界”;武汉大学通识课程目标是“向学生展示不同学科领域的各门知识及在这些领域内探索的形式,引导学生获得多种不同分析方法,了解这些方法是如何运用,以及他们的价值所在,强调的是能力、方法和性情的培养”。从上述两个高校可以看出,其通识课程目标在于拓宽专业面,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而在学生人文素质养成、善尽作为“人”和“公民”职责方面并未提及,其中心思想仍是专业化教育的委婉表述。
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 “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或被表述为“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完备的人性”,总而言之,并没有脱离学生做人方面的教育,关注的依然是人的生活、道德、情感、理智的和谐发展[3]。邓小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面向四个现代化,号召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1世纪的教育是全方面的教育,要以促进学生的五育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德育是被列为首位的,由此高校不仅要担负学生的知识培养更应该重视健全人格的养成。很难想象一个满腹经纶却心理扭曲或道德低下的人,会成为一个广受尊重的科学大师,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材。清华才女朱令“铊”中毒案、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刘海洋两次向动物园狗熊泼硫酸、云南大学马加爵不堪忍受欺辱石锤砸死四名室友、今年4月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被毒死案件,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要达到这一要求,仅仅掌握好科学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具备最起码的社会公德和一个正常的人格。对于这一点,社会、学校、家庭和青年学子自己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
从古代的八股文选才被废除改为科举制度,再从应试教育演化成今天的素质教育,然而从目前的开展状况来看,几百年的教育改革到最后实质上还是原地踏步,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内容的单一性、教学方式的填鸭式和投机性等特点,泯灭了一个民族的创造性。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绩仍是高校衡量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地位重要。各大高校高喊着通识教育的口号,走着应试教育的老路,通识教育课程通常被设置成选修课,成为了额外的、次要的、捞取学分的课程,在必修课的挤压之下名存实亡,从而导致学生对选修课的轻视。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台湾高校的通识课程学分占本科总学分的比例达到22%,而我国大学的通选课一般只占10%左右[4]。
截至目前,我国高校几乎均未设立负责通识教育的管理机构(除复旦学院外)。教务处作为全校教学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全校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通识课程的开设、选课报名、教师安排、资源配备、成绩管理等工作主要也由教务部门负责。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被默认为重要课程的前提下,增加了通识教育课程开设与实施的随意性。
教育不应是车间里的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都是同样模式、同样思维的“产品”,它的最终目的是开发、挖掘出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使个体的创造力发挥到最大值,将“制造”改为“创造”。
应试教育体制的存在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前进步伐,而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我国开展通识教育任重而道远。只有国家教育部门从根本上摒弃应试教育体制,通识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1]李楠,周建华.中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比较与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
[2]李曼丽,杨莉,孙海涛.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调查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3]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清华大学出版社.
[4]张东海.通识教育:概念的误读与实践的困境——兼从全人教育角度理解通识教育内涵[J].复旦教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