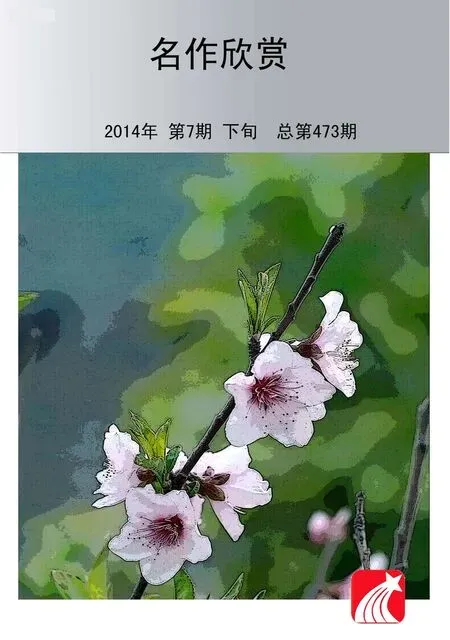流放——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变奏
⊙朱晓静[山东艺术学院, 济南 250014]
安妮塔·布鲁克娜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以讲述现代知识女性的生活而著称。她曾以蔑视的态度评论当代女权主义,将其讽刺为“仇视男性”。然而,她的多部作品都清楚地表明了她对现代妇女的处境和利益的深切关怀(注:本文中的“妇女”指“布鲁克娜笔下的妇女”,即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比如在她的代表作《杜兰葛山庄》中,布鲁克娜阐述了外表温顺的中年女作家依笛追求幸福的痛苦经历:因为一起悔婚事件(其实是因为她不愿违背真实的自我),依笛在旅游季节即将结束时被送到一个不合时宜然而合乎体统的旅馆度假,度过了一段孤寂的生活,却获得了精神的新生。
小说的表层故事之下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在瑞士的奢侈度假实质上是一群孤寂女人的集会:她们被遣送到这家过季的旅馆进行流放生活,伴以富有意味的开放式结局。这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流放。小说中“,依笛用男人的缺席来定义这个旅馆——‘女人,女人,只有女人’,这个‘雌蕊’”,证明了妇女被遗忘和抛弃的处境。另外,布鲁克娜描述了这些妇女——既包括依笛这种安静地接受抵制的女人,也包括那些贪婪而性感的女人——的精神空虚和无家可归感。依笛狼狈离家时,聊以自慰地想到至少她的花园有人打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她的心灵花园是否有人照料,这也是本作品的主要社会意义所在。
一、小说的氛围 布鲁克娜娴熟地利用景物和天气来反映中心人物的感情,并向读者暗示表层故事下的真相。小说中弥漫着压抑和凄凉的气氛,与依笛的忧郁心情相合,也紧扣情节的展开。简言之,通过这一技巧,作者为众妇女的流放生活提供了辅助的外部环境,暗示着流放的真相和不愉快的结局。
《杜兰葛山庄》中,景物和天气,包括旅馆本身,都是依笛倾注个人感情的画布;反之客观环境又以其特性影响依笛的心路——景物和天气已成为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为配合众女性角色的令人失望的生活,“文中充斥着不确定和模糊的意象,如笼罩空气、天空和旅馆周围湖水的灰色和薄雾”。另外,布鲁克娜因行文细腻而备受推崇,擅长选取涵义丰富的词汇进行精细的描述。
小说的开头两段为整部作品勾勒出一幅封面,提供了女主角和外部环境的基本信息,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主题和基调。故事伊始,一切就都封闭于灰色的薄雾中,传达出危险和压抑的感觉。从依笛在旅馆的窗子往外看“,外面是一片苍茫的灰色。灰的花园里,只有隐隐约约几种不知名的植物枝叶招展。花园尽头,遁进灰雾里,应该是一片望不见边的湖水”。“现在是九月底,旅游旺季已过,游客都走光了……”这样读者就获知:深秋时节,女主角依笛将要在一个安静、压抑的地方度假,而且当地的天气变化无常,令人苦恼。加上“灰的“”不知名的“”望不见边的”等形容词传达出的凄凉而神秘的意味,读者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依笛面临的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惬意假期。
接下来,布鲁克娜转而描写人物所处的室内环境。描写依笛的房间,她用了以下词汇“:肉红的、高而窄的、小而朴素、紧紧的、形貌拘谨的、微弱的、幽暗的、僵硬的、窄长的”,进一步强调依笛不得不住在不利于解放身心的地方。难怪她立刻致信情人大维,说此地“像个荒岛”,但旋即改口写道“,这里很安静、温暖,十分宽敞。我想气候可以算是稳定的”,说明她不愿意,或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后文中,情形并未有任何明显的变化。过季的旅馆永远乏人问津,甚至沙龙里也只有“两个影像模糊的男人”“一对男女”……,以致“虽然大厅非常明朗怡人,谁都可以感到那股死气沉沉的寂静”。依笛,如作者暗示的,一直沉浸于孤独的散步和思考中,与其他旅客的接触只让她的流放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小说的最后,布鲁克娜安排了残酷的一幕,即勒维而的求婚。她用不变的氛围暗示了不愉快的结局: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的依笛,与勒维而一起乘船驶向包围湖面的无边的灰色浓雾中,好像去一个未知的神秘的地方,看不到出路;空旷的湖面、阴沉的光线、慢得像做梦的速度……这些意象带给依笛巨大的压力,使她再一次感到不安、沮丧、无家可归,她觉得自己仿佛上了鬼船,飘向未知,甚至死亡。总之,求婚的环境不但不浪漫温馨,反而令依笛“几乎忍不住了”。果然,勒维而不但无意帮助依笛走出困境,而且故意使她感到无助和紧张,只为让她感激并接受自己的求婚。又一次,小说的氛围帮助读者感受和理解依笛承受的巨大痛苦。
如上所述,布鲁克娜运用富有含义的词汇和雾、船等常见的文学意象,成功地为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和主题的发展服务,以反映现代妇女的处境。运用传统技巧来描写现代生活,这正是布鲁克娜的特殊才能。
二、小说中的妇女流放者 通过探讨众女性角色在旅游季节即将结束时来度假的原因,可以确定度假表象下的流放真相。所有的女性都不满意小镇孤寂的环境,但却不得不待下去,等待男性的再次关注,因为她们已经失去了离开的能力,或反抗的意识。所以除了肉体的放逐,她们还经受着精神上的流放——被遗忘,被抛弃,无家可归。简言之,忽略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众女性都是被动而来“,这个旅馆似乎专为接收‘被丢弃或抛弃的人’:老年的、有某种缺陷的妇女——然而所有的人,关心的是满足完全不在场的男性的需要”。
显然,依笛的到来是完全被动的:朋友们替她安排了这次度假,直到大家认为她又是她自己了才能回去。但她并未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是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被遗弃的角落,跟爱情的受害者和流放者成为同类。这种情况既无法给她带来冲出眼前困境的勇气,也不能赋予她抛开心中痛苦的力量。例如,对客人十分挑剔的山庄经理赫伯先生,只因为她的名字有些不合英国淑女的标准,就怀疑她的身份“:也许她不完全是英国人,也许也不完全是位淑女……”这说明依笛缺少归属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她才一直想要通过浪漫的爱情或婚姻过上为世俗认可的生活。度假期间,她放任自己不断回忆与情人共度的时光,为自己能给他做饭,令他放松而高兴。只有在最后一封信中,她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你知道我的地址,两个礼拜来,我不曾收到片语只字。所以现在也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将来的地址,因为我也不会收到你任何音讯。”
表面看来,富有的普赛夫人及其女儿珍妮是来此地收集奢侈品的,但从一开始,依笛就认为她们的出现有问题。利用财富和女性魅力,她们成功地淡化了旅馆这个小世界中其他妇女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是普赛夫人赢得了旅馆全体员工的优待,凌驾于其他所有妇女之上,甚至珍妮也沦为其附庸。赫伯先生一改面对依笛的冷面,对她极为殷勤。在沙龙里,她独占舞台,强迫别人听她一人演讲……但无论如何,她身上有些奇怪的地方:她总在炫耀与已故丈夫的爱情,但关于这个人本身却无话可说,除了他慷慨地、源源不断地提供她想要的一切享受,死后依然如故。而且,很明显,当其妻女出外旅行时,普赛先生通常留在家中为所欲为。换个角度看,妻子和女儿很可能被做丈夫和父亲的“送出去了”,以大量的金钱为补偿,因此她们已经习惯了流放生活,一辈子无法摆脱。这一次,送她们来的是那个已故的男人给予她们的习惯。所以,在爱的世界里,普赛夫人和珍妮已经被遗忘了,长期陷在精神上的困境中——她们拥有的只有金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惯了这种本应痛苦的生活,她们对高身价的男性产生了狂热的需要。勒维而一出现,她们立即全力以赴,引诱他陪她们吃饭,跟她们谈话,照顾她们……最后,为了满足这个男人,母亲帮助女儿与之私通。
另一个女性角色莫妮卡美丽而有魅力。她应对普赛夫人的镇定态度和对两性关系的深刻洞察表明她以前也是个被男性宠溺的女人。但依笛后来得知她因不育而被送到这里,等待丈夫的宣判。她有一个奇怪的举动:用咖啡勺大口吞咽蛋糕。根据现代心理学,这反映了她受压抑的强烈愿望和对自己现状的强烈不满。但在流放期间,她无所作为,只有压抑而沉闷地消磨时间。因为她的旅伴只有一只狗,赫伯先生甚至省略其名,直接称之为“带狗的女人”。关于这个人物,有两个细节意味深长:其一,她用简洁而讽刺的语言劝依笛把握住身价不低的勒维而先生:“不管怎么说,他长得不坏”——是说这个人不算讨厌;“你那些衣服实在难看”——告诫依笛应该迎合男性的品味;“勒维而先生可以算是一条大鱼”——提醒依笛勒维而的价值;“谁说什么爱了?”——反映出依笛在两性问题上的天真和坚持;其二,当其夫决定让她回家时,她感到身心都焕然一新,前所未有地兴奋。以上两个细节清楚地表明,与普赛母女一样,莫妮卡也随时愿意满足男性的需求。
波内夫人无疑是双重流放最明显的例子:将房子给了儿子和儿媳以后,她被儿子扔进这个避世之地,不得不过着极端孤独的生活,无事可做,无人关注。在赫伯先生看来,她只是一位被留在旅馆里的常客;侍者很少关注她的在场和需要;她视儿子为生活的中心,而后者一个月只来看她一次,随即又将她留在孤寂中。事实上,儿子的拜访经常使她陷入更大的苦恼中:“波内夫人的笑容已经带着焦虑,跟她的儿子媳妇坐在一起,他们两人大声的谈着自己的事,她反正也听不见”;她“想多留儿子一下,可是汽车喇叭的吼声传来”;然后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她儿子消失的方向,直到她习以为常的死寂包围她,甚至连依笛和勒维而先生都感到那种死寂,她才离去”。更甚之,到了冬季杜兰葛山庄停业时,她将被送到一个更远,食物更匮乏,服务更不周的地方去——她的尊严将进一步减少。她好像已经失去了主观能动力,虽然活着,实际却死了。但令读者吃惊的是,有一晚依笛和莫妮卡隆重地搀扶她进餐厅,她立刻好像变了个人:“她的脸上浮起喜悦而又有些迷惘的微笑”,“她的头抬得高高的,态度大方,风范足以压倒周围的一切”。此处呈现出强烈的讽刺意味:虽然被残忍地遗忘,抛弃和压迫,波内夫人却保持了跟普赛母女并无二致的本质——对她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吸引别人,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更加讽刺的是,看到上述一幕,赫伯先生疾步上前相迎,侍者也及时调整了她的椅子,仿佛在宣告这一刻波内夫人是值得他们注意的。
三、开放式结局 最后,旅馆冬季歇业,众人即将离去,身体的流放要结束了,但众妇女的灵魂却没有什么改变,除了依笛——她最终对自我进行了新的诠释,放弃了一直向往的所谓被人接受的体面生活。布鲁克娜并未就依笛的两难处境给出直接的建议,只是讲述了依笛的所作所为,留待读者自己去判断。
在痛苦的孤寂中,依笛最初失去了反抗勒维而的力量,后者居高临下,意图将她变为一个只会倾听和微笑的陪衬。似乎只有高身价的男性才能给众妇女的枯燥生活带来些许改变和意义。勒维而就暗示依笛,女性只能在男性身上找到存在的意义。精通世故的普赛夫人用陈旧而有效的方法引诱勒维而——使他成为救美的英雄,加强他的男性优越感:某天半夜,珍妮的尖叫引来勒维而,后者清除了吓人的蜘蛛。这精心设计的一幕令人联想起简·奥斯丁笔下的情景:女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女性魅力抓住有身价的男人,同时装成脆弱的需要男性帮助的小东西;与此对应,绅士应该配合扮演强壮和主动的一方。布鲁克娜用客观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男性和女性仍然在上演18、19世纪的古老的爱情游戏。更为荒谬的是,勒维而接受了珍妮的邀请,同时又要求依笛作他的贤妻,侮辱了两个人。而依笛最终看穿了他的把戏,经过一番挣扎和思考,拒绝虚假婚姻,选择走一条自己的路。
种种风波之后,世事如前,只有依笛获得了灵魂的新生——至少她领悟到自己的真实需要,不再被世俗的标准所牵制。从此以后,男权社会只能强加给她身体的流放,她的灵魂自由了。至于她选择的路能否通往幸福、作者是否赞成,布鲁克娜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模糊了自己的真实意见,却赋予读者独立判断的机会。
[1]JohnSkinner.TheFictionsofAnitaBrookner——Illusions of Romance[M].London: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1992.
[2] Abby H.P.Werlock,ed.British Women Writing Fiction[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0.
[3][英]安妮塔·布鲁克娜.杜兰葛山庄[M].卢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