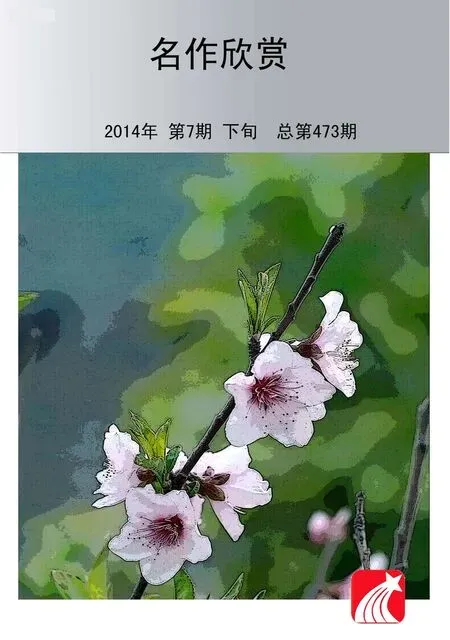在自由和公正之间徘徊——中国微博的公共空间生态分析
⊙赵春光[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北京 100024]
作 者:赵春光,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1级传播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山西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传播与传播史。
一、问题的缘起 “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这是新浪微博的广告词,但也阐述了一项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新闻事件时,更愿意处在一种动态的时空环境中,去真实地感受这个世界的变化。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正在抢占业已形成的受众市场,其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效应,技术上的原因就在于微博缩减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使得信息的传递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控制,成为了普通人能够说话的路径。“如果说19世纪见证了货物传送的成本下降,20世纪见证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下降,那么,21世纪将要见证的是,思想和信息的传递成本会急剧下降。”①
在最早出现微博的西方国家,微博虽然也产生了强大的聚集效应,但是政治交流的功能只是在中国被放大。当然,这与中国当前的现实社会环境有关。近两年中国的重大社会事件几乎都是由微博牵头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声浪,这股声浪甚至是压倒性的。然而,在中国微博声势浩大地向前推进的同时,笔者认为应当客观地来看待微博:微博是一个完全公正的平台吗?无数围观者的动机是否是道德的?一部分人在发出声音的同时是否践踏了另一部分人说话的权利?真正的公共领域是辩论还是谩骂、是追求一元意见还是多样性?
二、微博表达政治诉求的历史原因 微博之所以在西方国家没有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平台,是因为在西方的社会体制下,有着成熟的市民社会,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等才是表达政治诉求的现实途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和社会秩序理想的运作模式。它是与国家相对立的一股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市民社会的目的就是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以使国家权力在既定的界限内运作。
在西方国家,大众传播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市民是独立地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因相互需要而进行经济交换的社会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必然在精神领域成为独立的认识的主体,并疏离政治国家的社会生活空间。由于个人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个体便成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出发点。而对客观世界进行独立认知就必然要有一个介质,而新闻传播业正充当了这种介质。因此,成熟的西方国家,传统的新闻传播业很早便承担起监督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职能,并形成了程序性的政治诉求表达渠道。
然而,中国的社会情况与西方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自秦代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种治理国家的模式迎合了在春秋战国时期漫长的分裂之后秦始皇对于大一统的渴望,因此这种统治模式要求通过强有力的“法”,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都牢牢控制在皇帝的手里,高度服从皇权的意志。“法家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反宗法的,它的逻辑是强制瓦解宗法大家庭。”②秦朝迅速灭亡之后,汉承秦制但并非模仿,汉代在以法家思想统治的基础上,适时地默许了宗法大家族的发展。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逐步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一种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统治社会的方式。“从东汉开始,世家大族势力逐渐兴起,魏晋出现门阀士族,当时的政权体系、选官原则也变成了泛道德主义、伦理中心主义。”③但中央集权的体制就在这样的统治模式下开始慢慢解体。为了继续维护统一的大一统国家,自隋代开始重拾“法家”思想,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倒回到秦代,而是在儒家思想这种具有人情味的思想外衣下实现“法”的统治,这一模式保证了皇权对整个国家的绝对统治,同时并举伦理道德和法这两件武器对社会进行统治,客观上对世家大族进行分化和解体,确保了皇权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强大干预。
直至清末到民国时期,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市民组织才短暂萌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对个人权力和个性的束缚主要来自大共同体,这不仅扼杀了个人权力和个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小共同体的自治空间”④。1949年之后,在计划经济思维的主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资产阶级和地方乡绅彻底消灭,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复存在,整个国家形成了国家——市民的二元格局。国家统管人们的一切,私人领域不复存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客观作用下,独立的社会主体开始出现,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民间统治精英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这客观上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对所有社会资源都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因此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也不是放任自流的,“从整体上来看,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手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即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⑤,这就是所谓的“分类控制”模式。通过这种“分类控制”模式,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社会组织对国家构成挑战的能力不同又分别地对其进行管理。因而,这种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英美系国家所谓的市民社会,有些学者将其定义为“法团主义模式”。可以说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领域中不存在西方所谓的与国家相对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也就不存在独立的新闻传播业。在中国,新闻传播业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的,因此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国家进行监督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程序性渠道也就不存在了。
三、微博的公共空间生态分析
在程序性的表达渠道缺失的情况下,个体开始寻找其他的替代性的表达渠道,微博成为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微博是一套自足的系统,其信息传播的重要特点是反议程设置的,其与官方媒体的议程是相对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能为官方媒体设置议程。
1.微博的舆论场总是受到传统媒体的影响。在微博这个话语空间中,关注重点还是由传统媒体主宰的社会新闻事件。同时,由于微博的本身的碎片化和个人化,其对于社会新闻的呈现不可能达到传统媒体的高度,且新闻报道所需的完整性是微博所不具备的,因此,微博的舆论场受传统媒体的影响特别大。微博本身的社会公共空间是架设在传统媒体对社会热点新闻的报道之上的,可以说,微博是对传统新闻内容的开掘和拓展。因此,可以看到,尽管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蓬勃发展面前显得有些疲软,但是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依然强大。微博空间中的话题内容往往是非原创性的。
2.有着与传统媒体相对的一套舆论生态系统,在某些事件中甚至有反议程设置的功能。尽管在议程设置方面微博的空间话语总是受到传统媒体的影响,但是,话题的设置并不意味着能够左右议题发展的方向及性质。尤其中国现阶段处在一个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段,任何挑动社会大众神经的敏感事件都可能导致舆论走向发生偏转和变化。尤其是微博这个公共空间为这种舆论的偏转提供了条件,因为它有其自身的一套相对独立的舆论系统,这个系统在某些社会事件中起到了反议程设置的功能。
3.意见领袖的影响极大,存在着话语垄断。事实上,微博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话语平等的空间,其间仍然存在着话语垄断。在现实空间里,话语权的不平等在于个体声音无法传达;而在微博这个虚拟空间里,话语霸权真实反映在影响力这个问题上。而虚拟空间里的影响力正是现实空间中影响力的折射。AdMaster&SSI的《微博用户使用习惯调查》显示:网络流行热点话题和名人语录、心情语录成为无论男女网民转发最多的内容,这也就是说微博议题往往是被舆论领袖所主导。微博中的话语平民要想使自己的声音传而广之,还是需要依托微博中的舆论领袖。
4.围观情节严重,许多人参与动机不明,存在网络水军现象。来自Incitez的研究报告《微博在中国》将中国的微博用户分为四种,分别是自我表达型、沉默寡言型、热衷讨论型、社交型。前三种微博用户其实算不上完全的参与,而只有社交型的用户才是微博的真正参与者。但是根据Incitez的统计,在中国微博领域中,社交型用户只占到16.2%。也就是说真正推动和参与的微博的人只是少数。由此可见,在微博这个公共空间里,围观的是大多数,理性的讨论和参与只是存在于个别群体中。此外,这四类微博用户本身的围观动机和参与动机不明,由于微博本身的影响力,出于各种意图在微博中充当网络水军的用户不计其数,这对中国微博空间朝着理性和真实的方向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侵扰。
由此可见,微博是公民广泛参与的一种民主形式,它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但是,微博作为一种非程序性的民主形式,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想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必然要重新树立宪法的权威,畅通公民表达社会诉求的渠道,形成民主表达机制,真正将线上诉求转化为线下诉求。
①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③④⑤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第274页,第277页,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