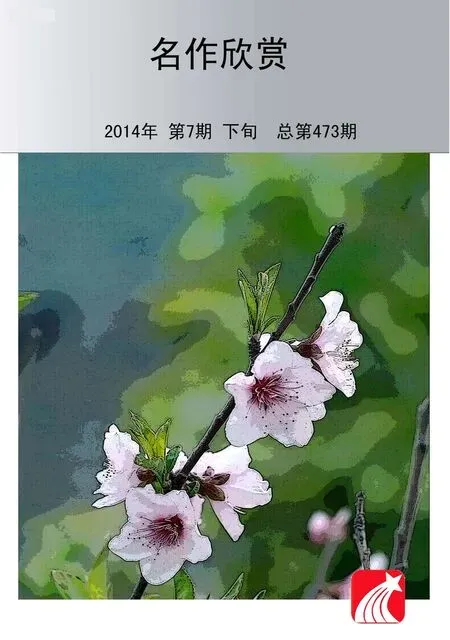沉溺与逃离:徐訏小说中的都市内质
⊙李 燕[南昌大学, 南昌 330031]
作 者:李 燕,南昌大学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徐訏的一生最为重要的几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巴黎、重庆、香港,从东方古城的传统厚重到西方巴黎的浪漫神秘、从内陆小城的内敛朴实到沿海城市的现代摩登,徐訏领略了都市的各类风情与姿态。这几个城市将徐訏的一生连缀起来,而徐訏的创作也与这几座城市不可剥离。都市的意象和形态深深地印进了徐訏的创作意识里,所以,都市的味道与色彩成为徐訏大多数小说的背景与底色。
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徐訏经历了一个由乡村进入都市的人生过程,从青山如画,绿水如镜的江南乡村进入到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徐訏感受到了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北京城的雍容高贵,上海的十里洋场,巴黎的浪漫典雅,都成为徐訏小说中都市气质的来源。徐訏写到都市的小说具有浓烈的都市味道,徐訏笔下的都市是繁华热闹、令人迷醉的,都市生活的唯美情调以及都市生活的无限丰富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沉溺依恋。
《鬼恋》《风萧萧》《江湖行》中一次又一次写到繁华的上海都市生活场景。华丽高档的舞会、豪华的酒店宾馆、明丽璀璨的服装饰品、圣洁典雅的大教堂、杂乱拥挤的赌场、奢侈的香烟名酒大洋房,等等。这些华丽精彩的都市外在意象将徐訏笔下的人物包裹在一种富贵充裕、优雅从容的外衣下。这些都市人物,有着用不完的金钱,有着令人恍神的美丽与优雅、风度与才华,有着挥霍不尽的时间与精力,有着随时可以表现的浪漫情调与高贵涵养。徐訏对都市情调的大力渲染让读者感觉好像进入了阿拉丁神灯里的地下宝库,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贵的精神生活无一不令小说人物沉溺迷恋,也令读者神往。
《鬼恋》中丰富的都市意象把故事的氛围带入到一种远离普通人群的境界,充满了都市浪漫想象。“我”和“鬼”尽情享受凄艳清绝的都市月光,尽情享受都市夜晚的静谧,这样闲静地游荡,是一种理想的都市情结;《风萧萧》也极力呈现一种令人沉醉的都市情调,包括豪华舞场、宴会厅等都市场景,包括主人公之间各种人生、爱情婚姻、历史哲学、宗教信仰等问题深奥而诗意的探讨,也包括人物艳丽多姿的衣着打扮、浪漫多情的生活细节以及人物之间暧昧不清的感情纠缠。
如果说《风萧萧》是一对次上海都市的大展览的话,那么徐訏后来在香港创作的《江湖行》就是一次在人生已经进入到一种沉潜状态时所做的对于都市本质的深刻思考。《江湖行》中几乎每个人物都经历了都市与非都市的双重生活。这些人物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自己的都市迷醉情绪。首先是“我”这个人物,放弃了简单的乡村人生来到都市,从此便流连于都市的声色犬马,难以挣脱。其次是文中几个由乡野小镇步入都市的女子,葛衣情、印弓等,她们都对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很快适应,她们脱下了从前的衣服,换上了都市的妆容,迅速融进上海都会的交际场所,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变,都市的生活没有让她们感到无所适从,反而给她们一种如鱼得水般的滋润。
一、都市情调的沉溺
二、都市欲望的逃离
徐訏笔下的都市具有典型的双面特性,有着繁华如梦的声与色,也有着内心与精神的荒芜。徐訏笔下的人物,一方面沉溺于都市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一方面又在极力逃离这种都市欲望的束缚与牵制。都市的光鲜亮丽、繁华热闹以及丰富充足的物质生活容易让人沉醉不知归路,也容易让人变得麻木僵化。所以,徐訏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与都市都有一种既依恋又抗拒的矛盾态度,他们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种逃离都市的潜在愿望。他们的逃离概括而言有如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彻底离弃,如同《鸟语》里的芸芊,芸芊自幼生活于风景优美、环境宜人的乡村小镇,跟随男主人公来到上海,她不喜欢也无法接受都市的一切习惯,于是她放弃了人间的一切繁琐,留在宝觉庵,选择了一个未染尘埃的世界。这里都市是以一种大自然的对立形象出现的,不管是男主人公患有的“都市病”还是上海带给女主人公的种种不适,都可以看到,“我”和芸芊都不是一个被都市宽容拥抱的人,然而“我”是一个久居都市的人,尽管都市会带给“我”种种的不适,但是“我”依然不能彻底舍弃它,“我”只能在都市流落,在灯红酒绿中变得盲目庸俗。而芸芊只是都市生活的一个过客,所以芸芊可以彻底地离弃都市。
第二种,离去又归来,归来又离弃的漂泊姿态。这些人与都市有着一种相互缠绕,分解不开的纠缠情结,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是一种既迷恋又疏离、既喜爱又抗拒的矛盾姿态。正如《江湖行》中的周也壮,一次又一次地在都市空间与非都市空间徘徊游走。带着一种流浪的姿态,漂泊的心境,城市从来不是归属,却又有着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所以每一次周也壮在城市生活中感觉空虚寂寞了,便会暂时逃离都市,每一次在外面想到都市的种种繁华便又会回到都市怀抱。都市在这里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人们对于金钱、情爱、地位等等的追逐欲望。对于周也壮来说,都市是一个永远的召唤和诱惑,所以他的流浪总会以回归都市作为终结。
三、都市精神的表现
徐訏真正关注的并不是城市本身的描写,在徐訏的很多作品中,城市只是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如果承认徐訏对中国都市文学有很大贡献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对都市精神的深刻表现也许要比他对都市外在景观的表现的贡献来得更大、更珍贵。因为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到新感觉派作家再到矛盾等左翼作家,外在的城市意象和城市景观已经变得并不稀奇,但是能够像徐訏这样把都市化成一种精神写入作品的却不多。
徐訏的都市精神是指的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指一种浪漫的、自由的,甚至是带着传奇色彩的形而上的追求和指向,是指在都市繁华的物质基础上孕育的更高层次的自由精神。我们都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几乎都是处于战乱的特殊环境里,现实的世界更多的是一些灰暗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都选择了为政治服务,或者如茅盾等人一样走左翼路线,或者像萧乾等人一样直接去做战地记者,徐訏虽然也去过重庆,但是像徐訏这样的浪漫气质的作家最终还是选择把思想伸向了精神的领域,而且开辟出了一片完全不同于以往作家的文学土地,徐訏将奇幻、神秘、漂泊、流浪等因素植入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那一时代的大众需求,对处于不安定环境中的人们来说,读徐訏的小说就像在颠簸的车厢里做一个美丽幽远却又耐人深思的梦。在欣赏美的同时,也领略痛楚;在接受哲思与宗教的同时也洗涤心灵、净化灵魂,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精神之旅,最大的享受是心灵的自由。
徐訏笔下的人物大多数都迷恋于在人群中的漂泊流浪,他们不断地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可以安置灵魂的东西,或者是一种纯美的爱情,如《盲恋》中的陆梦放、《巫兰的噩梦》里的陈帼音,或者是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如《鬼恋》中的“鬼”,《江湖行》中的周也壮。这些人物身上都体现着都市精神中向往自由的一面。无论是陆梦放以一种畸形丑陋的形象追求着一个美丽如人间仙子的盲女,还是陈帼音以她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生爱上男友年过五十的父亲,都是一种看似不合理的爱情,但实际上却是通过外在形式的不和谐凸显内在的精神和谐,因为,只有超越了人间的既定法则,人性自由的一面才有延伸的空间;无论是经历了人间的背叛、虚伪、逃亡的之后的“鬼”身上那种独善其身的姿态,还是周也壮身上那个不安定的灵魂都可以视为一种都市自由精神的体现。
然而,如同徐訏小说人物对都市那种既迷恋有抗拒的矛盾态度一样,徐訏的都市精神,在自由的一面之外也有灰暗的色彩。也就是说,徐訏用他一部分作品构建他所喜爱的都市自由精神与自由人性,同时又用另一部分作品解构自己的乌托邦。这样的情绪集中体现在他的小说《盲恋》以及《巫兰的噩梦》中。《盲恋》里的都市自由精神化成了两个各自带着身体缺陷的人共同织就的一段旷世奇美的爱情,然而这种美如梦幻的爱情却因盲女复明而破碎了,因为盲女复明意味着世俗的眼光、世俗的思维、世俗的审美惯性回来了,于是,爱情消失了;《巫兰的噩梦》中年过五十的父亲和自己儿子深爱着的二十一岁的女子(陈帼音)相爱并准备结婚,走不出爱情困境的儿子学森最终选择沉谭自杀,最后,女子远走异乡。在这里,父亲与女子的自由意志被儿子学森的死亡打败了,或者说,是学森的死亡惊醒了这一对超越了世俗观念的恋人内心深处的纲常伦理。陆梦放和陈帼音的追求最后都失败了,但是追求过程中所显现的自由精神却是无比绚烂并且令人震撼的。
综上所述,徐訏小说中的都市从外在躯壳到内在精神都是双面的,徐訏在不遗余力的刻画都市外在的繁华时,也深刻挖掘都市内在精神的矛盾特性,徐訏笔下的都市是丰富深刻的,承载了作者一生的都市情结,也带给了读者永恒的都市思考。
[1]李欧梵.上海摩登[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6.
[2]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