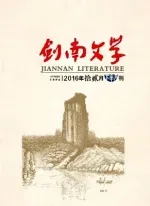人“鬼”情未了——论徐訏的 《鬼恋》与古代“人鬼恋”模式的异同
■杨 梅
上“鬼”,但是“鬼” 却一直逃避甚至拒绝“我”的爱恋,最终“鬼”离我而去、只留下“我”一个人“总是想念她、无时不在关念她的一切”。
《鬼恋》与传统“人鬼恋”模式的不同之处
《鬼恋》对传统的“人鬼恋”模式虽有借鉴,但徐訏也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流传至今的志怪传奇模式,而是在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手法和哲理思想之后,在诡谲多变的叙事技巧和气氛营造下进行了一种大胆的创新——《鬼恋》中的“人鬼恋”,实则是“人人恋”。
徐訏文章的创新之处,一则虽题为《鬼恋》,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鬼殊途”,而是具体的社会背景,使“人”不得不以“鬼”的面目生活在世间,这就在传统“鬼故事”的传奇基础上,就增加了一种讽刺的意味;二则虽为“鬼恋”,却不是一般的志怪传奇中描写的“两情相悦”,确切地说,《鬼恋》 中的恋情是一种“单相思”,是“我” 的“一厢情愿”,身为女主人公的“鬼” 一直拒绝“我” 的示爱、 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爱上“我”之后为了“逃避现实”而离开继续“过着鬼的日子”,留下病后的我独自惆怅。
《鬼恋》描写的是一个凄婉浪漫、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 从“我” 与“鬼” 在街头的最初相遇,到“我” 给“鬼” 指路、约会、交谈,然后一次偶然的大雨使“我”有机会进入“鬼” 的家中,“鬼” 扮作自己的丈夫试图回绝我,后来我在疑惑中两次故意在白天去敲“鬼”的家门而寻不到“鬼”,每次约会交谈,都是在晚上进行,即使我“故意使诈”喝多了不愿离开,“鬼”也会趁天未亮把“我”送回家。故事进行到这里,似乎所有的读者都确信“鬼”确实是行为怪异、名副其实的“鬼”了;然而作者笔锋一转,两个月后“我”在龙华寺竟然偶遇“行动似乎熟识”的尼姑,“我”追随发现,这竟然就是“鬼”,由此揭开此“鬼”绝非彼“鬼”的答案,故事也转入高潮部分——由“鬼”讲述自己“由人到鬼”的传奇身世:她是曾从事过秘密革命工作的革命者,多次参与暗杀行动,杀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后来从枪林里、车马缝里、轮船上、荒野上、牢狱中逃脱,流亡国外,回国之后发现爱人已被捕杀、继续工作也是不断地失败、被出卖,只剩下孤苦一身,在历尽人间冷暖之后,她的内心在生存的环境与精神痛苦的绝望和压抑下由人性转化为鬼性,决心做鬼,开始了昼伏夜出的生活,“冷观这人世的变化”;而面对“我”地不断示爱,多年的“非人非鬼”的生活使她早已参透世间的情爱本质,她一直坚信“恋爱是世间最幼稚的事情”而从始至终拒绝“我”的求爱,最后“鬼” 在“我” 大病初愈后留下一纸书信彻底离开“我” 的生活,留下“我”独自踌躇,“在这茫茫的人世间,我到哪里可以再会她一面呢?”,行文至此,“人人恋”画下并不圆满的句点。
一度被称作“文坛鬼才”的徐訏,在40年代常被批评家斥为“纯娱情小说家”,他的 《鬼恋》 也被批评为“追求神秘、 歪曲现实、不幸他的浪漫没有力量,没有时代与他配合”、“真正的浪漫归结于爆发和革命与强烈的对抗性,而徐訏的浪漫是逃避、麻醉、出世、宿命、投降”,然而就《鬼恋》的内容而言,这些贬斥性评论是有些求全责备的。如果一味为了迎合东南沿海市民趣味,徐訏完全可以不必讲述“鬼”的革命者身世,甚至把“人鬼恋”描写成大团圆结局似乎更符合大众审美心理。但是事实上,《鬼恋》虽没有将故事的重点放在社会现实的书写上,但却通过“鬼”的控诉对战乱年代中人性与灵魂进行了探寻与思考。如果说,《白毛女》给我们讲述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那 《鬼恋》则更为传奇地叙述了 《白毛女》的前半部分——动荡的战乱把人变成“鬼”。徐訏虽没有进行简单的政治说教和道德训导,也没有流露出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却通过“鬼”对于自己革命者身世的回忆,反映了命运和人生的无法预知和把握,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进行了发人深思的独特思考。
结论
徐訏的 《鬼恋》,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人鬼恋”的传统模式,又结合具体的战乱时势进行故事情节和环境的大胆创新,构思出独特的“人人恋”,在对爱情故事的讲述中也渗透出作者对于人性、命运、灵魂等超凡脱俗的拷问与热烈深邃的思考,是现当代文学史中一抹不可忽视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