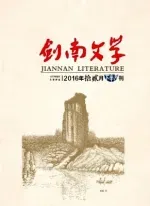东北记忆
■柴六一
我出生的较晚,与祖上未曾谋面,他们就匆匆离去了,或者说,他们在尚不知会有我这样一个乐于用文字记载他们的后人的情况下,就离我而去了。那时的 “我”还根本谈不上我这样一个概念,微小到连尘埃都不是,连产生的苗头都没有,甚至打卦都预测不出来,所以我不怪他们。
我见到的最高祖上就是我爷爷,那也仅仅是一张满洲国时期的照片,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狗毛领的棉大衣,绑腿,脚蹬一圈褶子的牛皮靰鞡鞋。方脸,皱纹如刀痕。没有蓄须。身边坐着一成年妇女,眼睛有些向眼眶里凹陷,据说是我奶奶,我的眼睛也有一点这方面的遗传。身后有五个均未成年的子女环绕,女着旗袍,男戴日式军帽,其中外八字脚的是后来的我爸爸。爷爷呈现的第二张照片,是端坐木凳的老头儿,蓄不很长的山羊胡,脸显长,面目褶皱已经柔顺。
这一切就决定我是典型的东北人,但自从上学后,每每遇到填写祖籍的时候,总要写上我毫无感觉的山东二字。这让我十分苦恼,也自始纠结,幸好贪玩,才一次次的冲淡着这方面的不解。幸好生于此,
山东棒子与东北老坦
首先做一下名词解释,这是在东北人过去对这两地人的称呼和评价。
山东棒子:是指山东人性格比较鲁直,象木头棒子 (也可能是玉米棒子)似的粗硬直筒,硬邦邦,倔烘烘。
河北老坦儿:查证费了一番工夫,多数的解释大意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比较土,东北话叫 “屯”。村子为屯儿,最小的乡下聚集单位,见大的市面自然小么。我的理解也有语言歧视的一方面因素,河北人说话垮垮的。
东北地区基本是由流民迁徙发展起来的,而来此地的人又大多数是山东人和河北人。东北的原住民是满、蒙、赫哲等少数民族。基本以游牧为主。中国的流民史,我不曾研究,大体知道南部沿海地区有客家人一说,就是由内地迁徙到那的一族人群。我臆想,人类迁徙,除生计外,可能就是对 “外面”的理想化。再则,就是人在腹地呆久了,会很闷,向南向北都是海洋的方向,对广阔的探究,走向大海,大概是人类的理想。
不知从何时起,发现了东北广柔的土地,丰富的矿藏。 “闯关东”成了时尚。我祖上,就是在这个大潮中,撇下山东济南府长青县柴家庄喜鹊窝,来东北的。是清朝中晚期,主要是到桦甸金矿淘金。那时有位 “韩边外”,很有名,跟他在一起采金。这个韩边外大概后来受皇封,边外应该是一种官职或者是封号,总之有金矿的开采权,还有一定的地方武装。他这一封号世袭,考古查证说,他家族的墓地就在现今的松花湖底,有高耸的汉白玉墓碑,日被人来了以后,建造了丰满水电站,给淹没了。我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父亲,一度也很富裕,鼎盛时期,刀鞘马鞍都是镶金的。后因常年在深山中,就不愿干了,下山进城开了一些生意,那时的富裕阶层吸大烟是时尚,以至于惰于经营,家道中落,到我爷爷这一辈只能给有土地的人做雇工了。后来凭着他老人家的精明,渐渐有了些小产业,但从而也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所有子女子都送到学校,最高学历达到伪满高中。他不懂什么奴化教育,觉得读书就是知礼的最好途径。在哪个朝代都有用。共产党来了,因父亲这一代都上过学,很快的,都成了国家干部。进一步验证了读书有用这一人类基本共识。
等到了我们这一代,除了早先有部分人管妈叫娘外,已没有任何山东人痕迹,生活习惯也与山东人也有天壤之别。甚至骨子里还有点瞧不上山东人苦瓜瓜的口音,和粗矿的饮食。山东老家,只能是上上代人心中的念想,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山东,就是个外地。
河北人是闯关东人中的一部分,没有山东人多。小时侯有个同学,叫杨么哈,大家都叫他 “老坦儿”,也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除他爷爷口音和别人有点不同外,没什么区别。生活条件都差不多,甚至还强一点。证明河北人并不是传说的那样不开化。去他家玩耍,叫他老坦儿,他爷爷呵呵的笑起来,并不脑。想来这种俚语也并无多少贬意,反而是一种亲近。相反南方的 “客家人”似乎倒有一点蔬离,有外地来做客的意味,在当地人眼里,你,永远是外地人。看来少数民族的包容性反倒很强。一直以来,这些山东棒子跟河北老坦儿们,主人样大刺刺地占据着社会主流,好象天生就是地产。
靰鞡草
旧话的一个说法,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人参跟貂皮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本地特产嘛,也算是上好的东西,但把草于人参貂皮等同,还是有其特殊性的。
我不知道是因有这种草,才产生了这种鞋,还是因有这种鞋才把这种草叫成靰鞡草。谁先谁后我没有做深层的考究,总之,人们把名贵的东西称作宝的同时,也常常把看似不值钱,却随时取之用之的自然之物,视为天赐,而感天感地,再比如水。
靰鞡草细密柔软且韧性极好,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冬季良好的保暖材料,特别是垫到鞋里,暖和耐磨。山坡塘口,到处生长,好用又丰富。那么靰鞡鞋呢,就是指专门蓄这种草的土制棉鞋,只在冬季穿的。鞋是用整快牛皮做的,从鞋底向上拉起定型,鞋脸抽一圈圆褶,有一鞋舌,大体有鞋的行状而已。鞋面用牛皮绳网状穿拉,鞋帮及脚踝,号码不是很准,以塞草多少决定。这种鞋不蓄草大概也没法穿,又大又硬又滑,很硌脚。当然,袜子的兴起还很晚,穿鞋时 (特别是冬天)用一块破布包脚,包脚布的优劣,也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
靰鞡鞋的缝制,是最为原始的梳皮处理,有极强的防水性和姣好的柔韧性,这大概就应是皮鞋的初级阶段吧?!当年的劳动者, 穿着这种 “皮鞋”, 而且是 “皮棉鞋”,穿冰踏雪,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像担着重物的扁担的颤威声,回荡在山谷小径,白桦林间,屯头巷口,有着极强的乐感。靰鞡草透析干爽暖和,又能随时更换,恰好是普通百姓必备的上等品。
靰鞡是满语发音,可以理解为鞋子的意思,乡下在从前也叫棉水靰鞡,就足以验证它的防水性,起源与哪朝哪代我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起源于满族或东北原著民的其他少数民族,我爷爷以上肯定穿过,我认为绝迹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我儿时还偶尔见到有穿的。小说 《林海雪原》中,李勇奇们就穿的那种鞋。当然,乌拉鞋似乎只限成年男子穿用,穿时必须打绑腿才配套。目前,大概也只有到民俗博物馆才能见到了。
土烟筒
烟囱,东北叫烟筒。
现代城里居民住的楼房,集中供热和电气化,基本没什么烟气排放,也就不存在烟筒了。排烟机排出的一点点烟气,在窗口打个孔就出去了。
我所说的土烟筒,是几十年前乡村土房时代的产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家从城里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父亲的名字叫 “五七战士”。 “五七”是指毛主席在某一年五月七日发出的指示,大体是号召城市里的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幸好父母也是农村家庭出身,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
第二年春天,生产队专门给我家建了一处新房子,用黄泥掺上切碎的稻草,再用叉子一层层堆起四墙,里边房间的间隔,用木杆立桩,中间用树条编织,再用稀泥抹上两边就是墙。房顶用木头钉几个三脚架,再钉上板条,外面用稻草一层层扇房,象蓑衣那样。内棚用高粱杆儿吊棚,有条件买一点花棚纸糊顶,买些旧报纸糊墙。
最突出的要数房子侧面的大烟筒,直径有房山墙三分之一,高度过房顶,可以说是巨大,象工厂的烟筒。也是用木杆立桩,树条编织,或用稻草拧成粗绳,沾稀泥编织成形后里外套泥。它用同样粗大卧地的脖子,连接屋内的土炕,土炕连接厨房大大的锅灶。
燃料基本是玉米杆和去粒后的玉米棒。那东西起不来大火,烟很大,遇上雨天淋湿,烟就更大,巨大的烟筒,黑烟滚滚,整个房子里也滚滚浓烟。
那时侯,整个村子没有一户砖房。砖房是不需要在外边建烟筒的,它直接砌到墙的夹层。傍晚,气压底,家家房顶升起炊烟,在村子上空汇聚了一层,飘飘袅袅。妇女喊着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放牧的牛、猪、羊等在幕蔼中纷纷归来。这在诗人眼中就是标准的田园生活了。
巨大的烟筒,当然也是文化生活贫乏时期,孩子的重要游乐场。比如捉迷藏,基本都是围绕着它进行。各家各户都一样,藏谁家的烟筒后是不好分辨的。那时我还小,三岁吧,几乎每天都爬到烟筒脖子上,手把着粗大的烟筒,了望和等待着哥哥姐姐们的放学归来。
那一年,我家院子里闹蛇,妈妈经常抱进屋里一捆玉米杆,在填进锅灶的时候,就窜出一条蛇来……一天,哥哥放学回来,想到房后园子里摘黄瓜吃,他正要从烟筒脖子上爬过去,我想故意吓他,拉一下他后衣襟, “有长虫!”不想,话音未落,真的就从那儿立起一条蛇来,花花绿绿的,色彩极其斑斓,当地农民叫这种蛇为 “野鸡脖子”,毒性很大的。哥哥拽起我就跑,邻里小伙子来打蛇,那家伙已不只去向。从此,我就不敢靠近那烟筒,总感到那是蛇盘踞之所,连接房前屋后的路就这样被它阻断并把我赶到了外围。多年后,我知道,蛇是怕人的,人躲蛇,蛇也躲人。而且蛇更是怕烟的,它不应盘踞于此,而仅仅是路过那里,反而是我们阻挡了它前进的方向。
轱辘井
这是俗称,学名应叫辘轳井,利用绞盘起重的原理。几时年前在乡村还较普遍,现在很少见了。这种井是供全村人用的,因此很大,也很深,下望黑咕隆咚的,有过丈。井口用木头或石头砌成方形,两平米的样子。再用木杆或粗铁管支两个架子,一个立在井边,一个立在井口,然后,横一个粗大的辘轳,辘轳边焊接一个挺长的把儿。一根长长的铁链或绳子,一头固定在辘轳上,一头固定在水桶上,摇动吱吱嘎嘎的辘轳,把水打上来,这也算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机械吧。
这水桶如果是木头的,长期泡在水里就很重,摇起来就非常吃力。如果是铁皮的,农村叫水筲,又太轻,就在桶梁上栓一块铁,易于下沉。冬天时候会很糟糕,水桶内外结上很厚的冰,费很大得力气,一次打不上多少水。而且井的四周也因长时间有水撒下,形成小山一样的大包,行走非常不便和危险。人滑倒,桶摔出,是常有的事。
摇这种井一定要有力气,一次性摇上来,如果小孩子力气小,摇到半路没劲儿了,是非常危险的件事。手一滑,吊在半空的一桶水就迅速下坠,摇把也象陀螺一样快速地反转,如躲闪不及,长长的铁把极易把人扫倒和打伤或打到井里去。我总认为,那井口实在是太宽了,似乎能下去一头牛,又极其幽深,黑幽幽象能吞噬一切的魔兽的巨口。
小时侯,听过老年人说的一则民谣:“一夜北风冷,大雪下得猛;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山是冰疙瘩,井是黑窟窿。”漫天大雪,只有井最突出。
听一回民俗专家讲 “井”的文化,咱中国人对家乡的井、水有一种天然的近乎,总会说是喝哪的水长大的。因而有 “背井离乡”一说。著名的那首 “床前明月光”,就是指坐在井床 (台),看井水倒映月亮,勾起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去外地谋生,喝不到家乡的水,内心是极其惆怅的。
从外地平安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喝上一口家乡的水,咕咚咕咚下肚,哈地喘一口气,心满意足地说, “家乡的水真甜那!”或者 “又喝到家乡的水啦!”好象必须有这么个程式,否则你回来干吗来了?
也常听有跳井的。没有高楼,也不靠海、靠江,自然就不能跳楼、跳海、跳江。好象农村里因各种原因不活的人,跳井是唯一不太费力的死法。井口又那么宽,产生死的念头,很自然就想到井。淹死了人,就污染了水。清理的办法叫淘井,组织一些壮劳力,将井水打净,再下到井底清出一些泥沙,等水再慢慢从地下溢出,水位升起,继续饮用。
当然也有意外掉下去的,救助及时,这个摇把就起到关键作用。让掉下去的大人或孩子,抓住绳索或有能力站到桶里,很容易的把他摇上来。也会有家禽等小动物不慎落下去的时候。比如一只鸭,引来一些人围观,鸭子在下面沿井壁画着圈儿,嘎嘎地叫着,上面的人哈哈地笑着,并不急着救助井中观天的鸭,让一坛井水泛起一阵涟漪。
现在乡镇饮水已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基本家家有水井,封闭的,用一根尼龙管下到井里,再接到厨房,井下装有电动水泵,只要在屋里一喝电开关, “嗡”的一声,水,就上来了。
酱缸
话说东辣西酸,南甜北咸。这咸,就和北方人的大酱有关。江南一带生活的人们,一般极不理解东北人,把黄瓜、白菜,甚至茄子、大蒜等用手抓来,沾上浓稠咸咸的酱生食大嚼的样子,常惊讶得合不拢嘴儿,无疑于食毛啖血!正像东北人不理解,他们将好端端、香喷喷的肉包子里,为什么要硬生生地塞进一块糖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叹:“那该怎么吃”?!
但,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民,对酱,乃至以此衍生的饮食图腾——酱缸,有着极其深厚的情怀。如长期漂泊在外,最念想的就剩那口爽爽的蘸酱菜了。就像古时候的人们,背井离乡,心中的那口家乡的井。坐井台,心惆怅。
住在小城或乡下,下酱,依然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城市里就不好制作了,楼房里阳光不够充分,加之酱味浓重是多有不便之处。只好在超市里买真空包装、不香不臭的酱来吃,这就有些寡淡。只有住平房,有个朝阳的院落,此时才好操作,贫民的生活才因此有了味道。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所谓平民,就是专指住平房的民众。居住于此,大家平等亲密,走东家窜西家的方便,是晚饭后的一道休闲景致和期盼。谁家的客人多,不光是他家宽敞,更体现好人缘的凝聚力,也是一种尊贵。住在盒子式的楼房就没有这份快乐,死相相,没有活力。譬如我老爹曾数次地向我探寻, “咱家右边儿这家姓啥呀”? 我说, “咱哪知道哇”?!
秋后,大豆收获上市,是制作酱的时节。 “制” 和 “下” 是有区别的, “制”是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下”是次年阳春放到缸里,加盐、水,泡制发酵的时候,也就是说,这要分两步走。
首先是要烀豆,大豆选好,拣出掺杂进的个别小石块和沙粒,洗净,放进一口大锅里,文火蒸煮起来,这个量,要视自家人口多少而定,这是全家一年的蘸头儿了。当咕噜咕噜的大锅沸腾,豆香飘散开来的时候,征询的话语也传过来。
“张嫂,你家今年烀多少斤豆子呀”?
“今年少,才四十斤。你家呢”?
“俺家整多了,娘家拿来三十斤,那死鬼又扛回三十斤,我正寻思呢,都烀上不”?
“烀上吧!大长的年”。
烀豆子不能火太旺,否则会畖底,煳了锅,直接影响酱的味道,因为这不是做酱油。待豆子熟了之后,就成了孩子们最欢快的事了,趁大人不备,把脏脏的小手伸进锅里抓上一把偷吃,烫了手也舍不得扔,左右手快速的倒腾,还用嘴呼哧呼哧地紧吹着凉气,填进嘴里,还要揪成个O型,再向外哈凉气,哈两下,再快速嚼两口,还烫,还得哈气,再嚼……吃多了,又口渴,水缸里舀一瓢凉水咕咕地灌下,与肚子里的豆子一混合,就很胀气,哏嘎地打嗝,一串串放响屁。家长此时也宽容地笑骂, “又偷吃豆儿了,看下酱不够的”!扬起巴掌,不疼不痒地在孩子后背拍一下。
煮好的豆子,要用一个光滑的木棒或一个玻璃瓶子,将豆子插碎,捣烂,使之成豆泥,再一块块的摔夯成一个个长方体的酱坯子,用铲子拍打平整,用牛皮纸包好,存放起来,这叫 “隔”,是个发酵过程,最好是放在通风的架子上,会少一些霉变。这样一放,就是一整个冬季。
待到阳春的四月初八,春暖花开之际,也是各家各户陆续下酱的时候,刷缸!刷酱坯!就在房前屋后忙碌起来。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时候?和种地一样,有个时令问题,过了这个时间再下就不好吃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超市里买回的制式包装的酱不香呢!那都是机械化生产出来,缺少灵性的。而选择这个日子,还多多少少有种仪式感。
经过一个冬天的存放,酱坯表面水份挥发殆尽,干裂板结, “隔”的差些的,还生有一层绒绒的白毛儿,中间因发酵,已由原来的金黄变成古铜色,甚至还有些发红。洗刷干净后,再将其一小块一小块地掰碎,放进加了水的缸里,水的多少,决定着酱的浓度,但原则上不宜太稀,否则蘸的不是酱而是盐水了。然后是放盐,那种大粒的洗盐,这个比例视豆子的多寡而定,也由各自口的轻重决定。当然,想吃的省些的,也会多放些盐。
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 “捣缸”了。用一个长木柄,下端平行镶一个枕头型或椭圆形的木板做的 “酱耙子”,搅弄浸泡了盐水的碎酱坯,这是个清洁过程,在搅弄的过程中,酱水翻卷,将杂质和脏的沫子卷上来,用筷子和小勺挑舀出去。这也是一项很见技巧的活儿,打高了,酱溅出来,喷到身上。打低了,水花小,杂质翻不上来。每天要捣上两回,每次要个把小时的,因此,也需要勤快。泡得差不多,家家户户呱嗒呱哒的捣缸声就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妇女们右手执酱耙子柄,动作不急不缓,匀速地捣着缸,左手拇指和食指间捏这个小勺,对应手背方向,中指的两侧还各夹支筷子,用小勺贴着缸内壁撇出翻上的脏沫子,间或用筷子夹出缸里的一个小草棍儿,一个小飞虫,或一个小蛆壳。拣出后,筷子会在缸沿外磕一下,震掉它们。捣缸的呱嗒声和筷子敲击缸沿儿的啪啪声,几乎回荡了我整个童年。
捣好的酱缸里,呈现的是透彻的鹅黄色,而不是黑漆漆的,否则,就会证明这家女人懒散埋汰。这就致使原材料一样的酱,制作出来后,每家的味道都不同。吃百鸡宴是一个味,如吃百家酱,却真真的是百家百味!
这还没完,酱是要由阳光晒的,这就是下酱要在阳光充足的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阳光的晒制,酱才能二次发酵,通常叫 “发缸”,萱萱的涨起一层,就像发好的面一样。发了缸的酱,香气才会出来,浓浓的新酱的酱香弥漫整个院落,此时才成为熟酱,方可食用。各家各户会竞相舀上一碗,交换着品尝,品评。色香味俱佳的,无疑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缸在外,就会有灰土纷扬,飞虫觊觎。因此,要用纱布罩上。先用粗铁丝围成缸外径大小,缝到纱布边沿,形成个箍。或在纱布四角包坠上重重的一个大螺丝帽,以免被风刮起。
当然,天总是要下雨,如果缸里积了雨水,就会生雨蛆虫,不光不卫生,酱还会变味儿,泻寡。缸帽子是必备的,一般情况会用洋铁皮,打制一个直径略大于缸外沿的尖顶圆锥形的酱缸盖,如草帽的形状。每当雨滴开始滴落时,人们就奔出屋来,抢在雨滴密集之前把 “帽子”盖在酱缸上,听到雨滴噼啪砸落在铁皮上时,人才会回屋,或望天儿,或卷棵旱烟点着,这时才是最安心的时候。如果出门很远,又没有预见到会下雨,眼看着瓢泼大雨,气势如虹,那将是极其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盖酱缸,是生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如被遗忘,大人要被主妇骂,孩子要被妈妈打。
前边说过,这一缸酱,是要吃到来年再次下酱的时候的,但总会有个别人家不够吃,端着个盆,去邻家借也是常事,来年新酱下来时再还,或者用豆子抵。当然,这种行为多少会在被借方心里有些不齿,会被认为是过日子少算计、没规划的行为。可借方用来年的新酱换陈酱,内心还隐隐的觉得亏欠呢!
围绕着这一缸酱,就是东北人,人人、餐餐必备的滋味了。特别是夏天蔬菜的时令时期,除了豆角、土豆之类不可生食的东西外,都可成为蘸酱之菜。从初春的柳蒿儿、猫爪子等山野菜,到黄瓜,生菜,以至于上秋儿的萝卜,白菜,大葱,大蒜,等等,等等,可谓百味归酱,百香归酱。
中国有八大菜系,东北人也在积极打造自己特色的菜系,大江南北,也都有东北特色的 “东北人家”之类的小酒馆,大酒店。其中很有名的一道菜叫 “大丰收”,就是汇聚各种各样蘸酱菜于一盘,足见能蘸酱的菜该是多么丰富。酱,又成了百味之根!
说酱,必然涉及到它的容器,酱缸。吉林舒兰所辖的一镇叫 “缸窑”,早先就是以烧制大缸的烧窑而得名,也许那里的泥土适合制陶吧,小时候,乘火车从那里经过,只见各家的院墙都是由破坛子、碎缸茬子砌成。真是与地名名副其实!几百年来 (甚至更久),那儿出产了多少缸,恐怕无法估算,但在东北,缸的用处始终如一,盛水,積菜,下酱!而酱缸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酱东西。此时的 “酱”是动词,腌制的意思。酱什么呢?太多啦!可酱黄瓜,辣椒,大头菜,香菜……蒸熟的土豆,面瓜,鸡蛋……最好是一块肉,猪肉,羊肉,兔肉……上品是牛肉,牛肉有筋性,特抗酱。酱好的牛肉是红色的,我认为,用酱酱出来的肉,才是世界上香味最浓郁的美味。这种酱香的牛肉,绝不是市面上烹调制作出来的所谓 “酱牛肉”可同日而语。
当然,被酱之物,酱之前,需熟的不要蒸煮太烂,因为在酱的过程中,有再次被酱熟的过程,否则,就成酱泥了。所有被酱之物,要用纱布包好,口扎紧,投放进缸里,最好留有一条细绳搭在缸沿儿外,便于吃的时候向外提拉。当然也有不够讲究的,把酱的东西直接扔缸里。如果缸很大,捞起来是件及其费事的事,弄不好,就会永远遗留在缸里,混为酱泥。
新酱时期是绝对不许把东西扔到缸里的,因为这会程度不同的改变酱的质地和味道。酱过的蔬菜就变成了咸菜,无疑,又丰富了餐桌上的品种。真是百味入酱,酱香百味。
台湾作家柏杨就曾阐述过中国的酱缸文化,当然,他更多的是从糟粕情况说的,他说,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中国,就会被腌制,变了味儿。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融”和 “容”呢?中国文化繁杂,自己的很多,外来的也不少, “酱”在一起,互惠互存,也没什么不好,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和民族性的体现和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