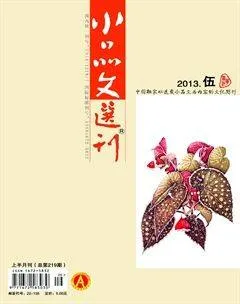劳作者
农人
夏至,农人们大规模地出现在田地里。
玉米们快速而疯狂地在短短的夜里与野草们同时飞快上窜。
播种时为确保种子发芽,他们在每个穴里都要投下四到五颗种粒。经过节气中风沙、细雨的残暴抚慰和悉心滋润后,经受考验并被恩待的种子们,便开始发芽,生根,生长,而另一些种子便永远被埋在地底,成为尸骨,化泥成土。
并不是每枚种子最终能成为成熟的庄稼。被神庇护的生物,都要经历不断拣择和考验的历程,被抛弃和恩宠,同样都是一生。为使庄稼茁壮、颗粒结实饱满,一部分长势稍差、长相不好、或者长地不适的禾苗,将与纷长的野草,被神灵派到人间的农人们掐灭在夏天的热浪里。
空气湿润,气温不断上升,田地经过雨水的浸泡和湿气的氤氲,质地越来越硬,密度越来越大。这是庄稼一生中最重要的时辰。当空间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窒息,彼此呼吸艰难,甚而快要死亡的时后,它们迎来神圣的洗礼仪式,庄稼们身边多余的同伴和草们,因为被神唾弃,而被掐灭在童年某个时刻,而新生的庄稼们,坦然地接受圣灵和恩典,从此得到新生。农人们成为庄稼的神,承接着父辈乃至先祖的习惯,抓住短暂的时间,来挑拣、修理和建造着坦荡无边的田地,主宰庄稼短暂的命运。
温河的水清澈见底,灰色的小鱼潜藏水底。杨树们叶逐日茂盛,它的树冠撑出一片又一片的阴凉。一条条牲口被闲置在树凉下,它们摇头摆尾,闲极无聊,留下大量的粪便。
村里突然变得很空。我跟禾苗站在离骡子不远的五道庙,四下里张望。石阶依旧冰凉,一群鸡颠颠地沿着石阶的边缘跑过去。对面远处,庙像一个沉默的人,蹲在那里,动也不动。
所有能动弹的男人都涌到田地里司其神职。河边,南坡,杨树沟,每块田地都陆续出现了农人的身影,他们像一些藏匿的秘者,突然现身在各处地方,戴着草帽,光着黝黑的膀子,用铲子将一蓬禾苗中的杂苗全部拔掉,只留下主株,再用明晃晃的锄头将草锄去,翻出散发着腥味和汗味的土壤,从天刚亮,一直干到黄昏。
这是庄稼人最忙碌最劳累的月份。古诗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传世名句,极准确地描绘出锄地人们劳作的情形。
当男人们起早摸黑劳作的时候,女人们也忙碌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做饭,喂牲畜,扫院,挑水,还有更多诸如搬东西一类的力气活。每到中午,家家户户的女人会提着篮子出现在街头,她们的篮子里放着烙好的饼子,撒着葱花的菜汤,她们顶着炎热的日光,去往河边,南坡,杨树沟自家男人劳作的地堰里,给他们送去饭食。
她们的篮子里同时藏着一条毛巾,一把轻巧的小锄头,当男人们吃饭的时候,会用毛巾擦去不停涌出的汗水,此时,女人们会蹲到庄稼地里,拿出小锄头,小心、灵巧有序地继续着男人们的工作。
在村里,节气成为时间的刻度,准确地将庄稼的时间囿住。一些难以言说的秘事,自然而然地被人沿用。并没有人确切地说出时间对于庄稼的具体涵义,但他们能将这段紧凑的时间利用的异常完满,而使庄稼们在有效的时间段中得到最好的护理。
这段急行军般的劳作不过十天左右光景,十天之后,禾苗将失去最佳的护理期,那些细弱的禾苗们,将贪婪地汲取着养分,邪气迷漫,所有禾苗都无法成为真正有用的庄稼,更无法结籽,成为粮食。
秋天,我们这些小孩子跟牲口们一样,喜欢吸食玉米秸杆里的甜汁,越是甜的,它的杆越粗壮,颗粒越饱满,相反,那些偷生的玉米秸杆虽然油绿好看,吃起来汁少肉寡,颇是无味。禾苗的父亲给牲口砍回桔杆,在大院子里跟禾苗大哥一起铡草,草节溅了一地。我跟禾苗吸食桔杆,把嚼干了的渣滓吐到了草节上。
禾苗说,我长大了,也要长得这么粗,这么甜。
她的名字跟她说过的话,至今想来,都是世上最好听的。
铁匠
村里的男人闲不住。
冬天,作为铁匠的六娃大爷,牺牲了给家人编扫帚,沤粪和去两里外的泉子沟挑水的时间,把铁匠铺里堆着的农具放到院子南墙跟,将尘封了一年的家什翻捣出来,扫去台面上厚后的灰尘,然后点起火,喊来他儿火火。于是,村子里响起了叮叮咚咚地砸锤声。
铁匠六娃在每年冬天里都有干不完的活计,村子好象一个硕大的仓库,需要他不断地用铁器将之填满。而村人就充当了予他职责和使命的人,来督促他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似的营生。
铁匠铺的木头风箱呼呼地将火焰吹到台面一尺高的地方,那火焰张着饥饿的嘴巴,并伸出贪婪的舌头,舔舐空气中的看不见的东西。一块铁适时地被放置其中,功夫不大,便烧到了火红,六娃大爷手疾眼快,用铁钳子将它夹出来,放在大铁墩上,左手死死地掐住钳子,右手拿一小锤,“叮”砸在铁块上。火火举着把大铁锤,见他爹小锤落下,他的大锤就紧紧跟上。一时,手起手落,大小锤声此起彼伏,看得人都痴了。锻造的过程,在一块铁来说,是疼痛的,它得不断被修正形状,火烧,锤敲,一次又一次,六娃大爷不停地翻动着左手里的铁块,眼见厚厚一块,慢慢变薄。后来变薄的铁块黑了,硬了,伤口结痂,眼看就不痛了,六娃大爺和火火也停止了敲打,却又将铁块放回火里。火火从他爹身后绕过去,蹲到地上,呼呲呼呲地拉风箱,风箱里的风在火火的拉动中,越来越大,炉里的火苗也越来越旺,火里的铁,在煎熬中,用疼痛完成了一场生命的褪变。
一块铁,要成为犁、耙、锄、镐、镰、菜刀、锅铲的过程是很复杂的。那样的锤敲有时要用一天时间,一块铁才能成为一件器物。
当一件器物打成,六娃大爷会把它快速地放到水缸中,耳听的“嘶啦”一声,像撕开一匹完整的布,一阵白烟倏然飘起,短促得让人来不及惊叹,淬火完成,一把造型好看、光滑的农具呈现眼前。
我常常站在铁匠铺门前,观望一把农具成型的过程,并看那股白烟的生成,思忖着短促的白烟瞬忽消失的原因,它们没有上天,也没有入水,更没有跳到火焰当中,眼睁睁在我面前消失。祖母来喊我回家,我有些不情愿。而那时,铁匠铺里的炉火正烧得旺盛,六娃大爷和火火像两个红人,在火下,光着膀子戴着个大围布,冒着热汗,生动而温暖。整个铁匠铺里,像火的王国,红得让人陶醉,铁屑横飞,无数星星陨落,瞬忽照明夜空,之后永陷黑暗。我的身后是冬天的北风,呼啸着从树尖掠过,枝柯断裂,砉冉掉下。
事实上,所有的危难和寒冷,在火热的铁匠铺、在被火光映红的六娃大爷和火火面前,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它)们像光,像火把,照亮了远方的记忆。
禾苗家打了犁和镰,田园家打了耙和镐,村里人都制下好农具,他们给六娃大爷送一些食物和用具作为报酬。我家没劳力,农具被扔在草房子里,跟坏了的水桶、烧火的干柴、折了的扁担放在一起,夏天流着霉水,冬天生着黑锈,我缠着祖母要打一件东西,祖母好不容易找出一块铁,并从窗台上抱了两个大南瓜,送到了铁匠铺。给我家打铁的那天,我把禾苗、田园、水草还有禾苗和水草的弟弟妹妹都叫来,我觉得那是我最值得炫耀的时刻,我想把自己观望和感受到的同她们一起分享。我把这么长时间得来的经营一一传授给他们,比如,铁该从火里拿出来砸了,小锤先落,大锤紧随,在这样叽喳的炫耀中,我更真切地看着铁的熔化,看着它在六娃大爷的小锤和火火的大锤中变薄,成型,入了水,冒起一股白烟。我们齐声欢呼。
那是一把弯月形镰刀,冷却后,六娃大爷用麻绳穿过镰把的孔,打了结,递给脸色通红的我,说,闺女,拿回家吧。
那种得到的喜悦一直延续到我见到祖母的那刻。
祖母正在烧炕火,火洞里的烟已经冒完了,柴薪呈出红色和灰白。窑洞里光线阴暗,盘腿坐在地下的祖母,被火洞的火照得通红,她的前襟透亮,脸上有种好看的光泽,像庙里的观音。
老妇
那时还小,祖母和跟前大大坐在炕上做针线。跟前大大做一会,就抽袋烟,要不就把线从针眼里拉出来,扔到地上,让我捡。有时禾苗也在,我们就一起捡。在暗色的窑洞略微潮湿的灰渣地上,那个针偶尔会闪着珍宝的光泽,但更多的时候,它并不发光,只是陷在地上的渣子中间,跟大大小小的灰渣快一起,灰白而暗淡,你必须借助光线,找一个好角度,才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它。
它是一动不动存在的,但你就是抓不住。它不像天上云,它的高度使它的存在变得高远而无法抵达。也不像河里的鱼,它飞快游走的本领让你自愧不如。
传说,能捡起针的人,是心灵手巧,心思敏慧的人。大多时候,我捡不起来,有时需要跟前大大自己下地自己捡,如果禾苗在,她捡起来的机率要大得多。跟前大大哈哈地笑话我,“你真是个笨闺女。“而后,止住笑又说,“笨人好命”。我看着她的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是冬天,温河已封冻,田地里庄稼收割后,留下大量根茬来不及收拾,长短不齐地僵立着。天冷得使人缩头缩脑,出气和说话之间嘴里就带出一股白烟,宛若有根看不见的烟袋,被含在嘴里。村里人情愿都呆在家里,围坐在炕上,男人们抽烟,编筐,拊条帚,偶尔聚在谁家里下盘棋,整个窑洞被旱烟充斥。女人们则盘坐在炕上缝补衣服,搓麻线,纳鞋底,做鞋,有时她们会糊几个毛衣掸子。村里手巧的女人会缝一个用布条拼接的坐垫、门帘。好门帘通常是这样的:各色布块齐齐整整缝成正方形或菱形或梅花形,中间却有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是用绣花针绣上去的,大红线,溜了黄边,挂在窑洞狭窄的门上,院里干枯的树、零乱的灰尘衬出一片喜色,好象春已迫在眉梢,只消撩眼,便是一派春色。
只有小孩子向往天寒地冻的外面世界。去河面上溜冰,叫喊声在河床里此起彼落,热闹非凡。
祖母和跟前大大也有做不完的针线活,祖母缝被子,补衣服,有时翻出父亲的旧衣服,比划着想做成个什么。跟前大大缝补的要比祖母多得多,她也戴着眼镜,吃烟或者看我捡针的时候,会透过眼镜框的上方向下观望,头仰得老高,眼睛却向下瞥,很可笑的样子。
更多的老女人们,要在冬天里穿针引线赶做自己的寿衣。好象冬天的寒冷,将她们的心冻小、冻怕了,又忐忑慌遽,又心怀侥幸。村里老人喜欢提前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将自己的壽衣做好,用抵抗漫长的时间来等待真正离开的那一刻。事实上,她们表面上做出来的坦然,是在掩饰骨子里的恐惧。没有人能坦然赴死,即便做好千万种准备。
她们喊来比自己更老或者关系比较好的老婆婆,将买了几十年美丽的绸缎摊开,用尺子量了,拿石灰块画好,然后裁开,戴着眼镜,就着好光线仔细地缝制。这一针一线,做起来要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精心,大到每一条边缝,每一个扣绊,小到每个针角,她们都格外细致。这袭锦衣,里面寄托了来世的祈望,是她们出行的盛装,也是她们一生最精准的展示。一般人缝寿衣不喜欢求人帮忙缝,自己的事,还是要自己了了。但最难为的,却是穿针,针关很小,线也细,穿过去要老半天。她们把线穿得长长的,像穿了一大把时间,期望老也用不完,做不完。
祖母的寿衣据说很多年前就做好了,反正我见到的时候,它们已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竖柜里了,祖母用一个白布包袱包着。她常常会解缠开包袱把它们拿出来,给一些老婆婆们看。每次我都要拿手去摸那些绸缎,酥酥麻麻的感觉。她老让我试穿,我不情愿但穿上后,就不想脱了,太像戏里的人了,我会穿着它们在炕上走上好几圈,想象一个阔大的戏台。祖母说,寿衣主贵,小孩穿了是要长命百岁的。
冬天老给人不大好的感觉,村里的老女人们在冬天慌张的样子,好象在传达着一个秘不可宣的讯息。
祖母说,人老了,最怕过冬,稍不留神,就过完了。
窗户的小块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冰花刻画着一片盛世缤纷,有河流,山峰,沟壑,有树木,鱼鸟,还有恍惚向我们走来的人,像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指尖,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出版《槛外梨花》,《花酿》、《与爱人分享的50种浪漫》。先后在《散文》、《青年文学》、《格言》、《读者》、《福建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黄河文学》、《华夏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过文章。
责任编辑 杨晓澜
(本文刊于《创作与评论》2013年5月号(上半月刊) 责编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