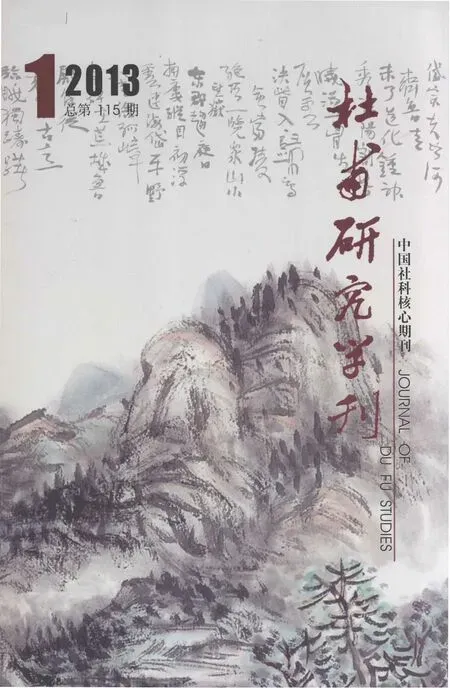杜甫的平民角色与平民情怀——兼论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问题
杨胜宽
作者: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614000。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诗人。他的伟大及深远影响,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具有历史上许多诗人所不具备的平民意识与情怀。杜甫的平民情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杜甫作为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入衰巨大转折和剧烈动荡的社会一分子,他身不由己地从社会的中层跌入社会底层,体验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流离颠沛,这种经历大大增强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感性认识;二是杜甫作为既具有丰富生活经历又具有社会良知与同情心的诗人,他用诗歌这种长于抒情的艺术形式宽视域广角度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平民的真实生活,诗人在其中对天下苍生的苦难寄予了深刻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杜诗历来被誉为“诗史”,其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和全面的记录,而且在于诗人用饱含感情的诗歌表达形式,生动反映了任何正史都不予重视和无法表现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其悲欢离合。杜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成功,为现代的文学创作和社会价值重建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郭沫若关于杜诗的“人民性”与杜甫的“地主生活”问题
杜甫其人其诗,在身后的一千多年历史里,轩轾抑扬、喜恶褒贬,几乎没有间断。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变革、中西文化交流、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起伏,对于历史人物和文学遗产的评价尺度与标准,也因不同的时代需要而不断改变。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特殊的世纪,人们对过往历史因某种需要而幡然改变已有的评价,是十分常见的事情。郭沫若对于杜甫的认识与评价的变化历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郭沫若最早是通过朗诵杜诗而知道历史上的诗人杜甫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其接触杜诗大约从五六岁就开始了。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回忆说:“读诗、学平仄四声之类,动手得尤其早,自五岁发蒙时所读的《三字经》《唐诗正文》《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作诗的)基本工作。”《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也说,十岁以前所作的诗歌和文艺方面的教育准备,除了四书五经,居于“副次”地位的,便是唐诗、《千家诗》《诗品》等。唐诗之中,郭沫若重点读了哪些诗人的作品,其诗人修养形成过程中,哪些诗人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我们从郭沫若1928年开列的《〈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提纲》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诗的修养时代”部分,首先列出的是“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韩退之(不喜欢)、白居易”。由此得知,首先,郭沫若早年诗歌修养的形成,唐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郭沫若阅读了杜甫的一些代表作,受到过杜诗的影响;第三,从郭沫若对唐代诗人的排序看,他最喜欢的是王、孟等山水田园诗,受到的影响也应最大,而李白、杜甫则排在王、孟、柳之后,表明在早年郭沫若的诗歌接受中,山水田园诗要超过李、杜诗,李、杜并提,体现了郭沫若尊重传统评价的意识;第四,郭沫若后来提及的不喜欢的唐代诗人,那时只有韩愈一人,没有表现出对李、杜的爱憎偏好。
五四运动前后,是郭沫若新诗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谈论诗歌创作的一些言论中,他也曾不止一次提及杜甫,可以看出这时郭沫若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评价态度。1920年在《论诗三札》中谈到对古代诗人的评价,体现了此时郭沫若评价古代诗人的基本标准:
至于我国古代真正的大诗人,还是屈原、陶靖节、李太白、杜甫诸人,白居易要次一等。古来的定评是不错的。因为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真正诗人的诗,不怕便是吐诉他自己的哀情、抑郁,我们读了,都足以增进我们的人格。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
这清楚表明,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完全认同传统对杜甫的评价观点,把他列为中国古代一流的大诗人。至于何以如此评价的原因,他自己给出了明确解释,因为杜甫和屈原、陶渊明、李白一样,是人格最圆满的诗人,而只有人格的圆满,才能写出最伟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足以打动读者,能够使读者完善自身的人格。郭沫若所说的“人格圆满的诗人”,指的是“个性发展得比较完全的诗人”。此时的郭沫若,信奉泛神论,张扬自我,注重诗歌的个性表达和抒情本质,是其浪漫主义艺术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时期。1924年《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一文,谈到整理古代遗产与文学创造的价值时,特别提到杜甫诗歌创造的价值:“研究莎士比亚与歌德的书车载斗量,价值抵不上一篇《罕谟列特》和一部《浮士德》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也何曾抵得上杜甫、韩愈的一诗一文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积极的创造呢?”其观点是否科学姑且不论,这表明那时的郭沫若极其重视文学创造,认为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最有创造价值。看得出,杜诗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地位是非常高的,几乎被作为古代最有价值诗歌的代名词。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因为主客观原因,进入集中研究历史人物的时期。他在《十批判书》的《后记》和《历史人物·序》等文章中,都明确提出其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是“人民本位”,并且在这个标准之下来确定郭沫若自己的“好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相关文章,郭沫若都几乎没有提及杜甫其人其诗,就跟从他的记忆中完全抹去了一般。而他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并以之为原型进行历史剧创作的,是被他称为“人民诗人”的屈原。看来,郭沫若二十年代高度评价的四位诗人,在新的评判标准之下因为研究者的主观好恶而出现了明显分化,相比对于屈原的高度重视,杜甫被郭沫若淡化,乃至“遗忘”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能够记起的是郭沫若1953年游成都杜甫草堂,为草堂题写的著名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表现了郭沫若对杜甫诗歌的高度肯定。但这种高度浓缩的题字性评价,与基于学理性研究所作的科学评价毕竟不完全相同,难免带有某些“应景”的成分。从题字内容看,中心意思依然重在肯定杜诗同情民生疾苦上,而“诗中圣哲”这种看似很高的褒扬,也似乎透露出离“人民诗人”称号犹有一间的“春秋笔法”!有力的证据是郭沫若1962年3月15日发表于《羊城晚报》的《谈诗》谈到“诗的人民性”问题,其中两处谈及杜甫及其诗歌作品,“杜甫的《三吏》《三别》,也只是同情一下人民罢了”;“至于唐代的几位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显然,此时的郭沫若对杜诗的人民性特征不突出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点成为其公开宣称不喜欢杜甫的最重要理由。
但令人不解的是,时隔三个月的1962年6月,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开幕式上致辞,后来作者把文章题目改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文章着意突出了杜诗的人民性特征,至少有三处从不同侧面谈及这一点:
他的生活就和时代的急变一样,仿佛由天上掉到了地下。从七五五年以后一直到他的逝世,十五六年间所渡过的基本上是流浪的生活,饥寒交迫的生活,忧心如捣的生活。但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他接近了人民,和人民打成了一片。
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而这忧国忧民的热情,十余年间,始终没有衰歇过。
他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既从现实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又向古代的诗人和民间的诗歌虚心学习,把古代的和民间的语言加以锻炼,而创造性地从事诗歌天地的开拓。
这些话,把杜诗人民性产生的主客观原因阐述得很透彻,不仅在诗歌思想内容上,而且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同样的评价对象,同样的评价尺度,在短短数月之间,竟有着如此截然的不同!这种迥异的评价态度,在十年后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更加走向极致。该书1971年12月出版以来,郭沫若对李、杜二人极端的抑扬态度一直饱受争议。他在《关于杜甫》部分的各章节中,全面贬低和否定了杜甫,其中一节的标题即是《杜甫的地主生活》,把杜甫归入剥削人、压迫人的统治者行列。证明的根据是杜甫自己诗中言及草堂栽种树木的种类与数量,郭沫若通过计算,认为达到一百亩的规模,拥有土地上百亩,“要说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那是很难令人首肯的”。杜甫后来漂泊到夔州,地方官柏茂琳在东屯把他安顿下来,据说还让他管理百顷公田,杜甫从这些收成中拿到了自己的一份管理“俸禄”;他在夔州还有自己的果园,养了一百只可以治风湿病的乌骨鸡!郭沫若由此判定说:“要之,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并且特意批评,那些说杜甫流浪生活很艰苦的评论者,是“人民诗人”的观念在作怪,明确否定杜甫是人民诗人,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十年前对杜诗“人民性”的评价。郭沫若认定杜甫过的是地主生活的观点,研究者普遍不能接受,认为是郭沫若机械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甚至是为了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而采取的深文周纳手法。因为郭沫若不可能不清楚,土地改革及解放后判定封建社会“地主”的性质,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自有大量土地;二是通过分租土地收取租税满足不劳而获的生活。杜甫无论在成都还是在夔州,其生活都不具备这两个特征,郭沫若硬说他过的是地主生活,的确显得牵强附会。
二、杜甫的平民角色
人们普遍相信,“安史之乱”不仅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完全改变了杜甫的人生命运。这样的观点本没有错,但它容易产生误导,使研究者和读者的目光只去关注“安史之乱”以后的杜甫,而不同程度地忽视对杜甫早期生活及诗歌创作全过程的深入了解。其实,从社会角色看,贯穿杜甫一生的都是平民化的角色,不仅跟地主生活不沾边,甚至也很少真正进入过统治阶层的行列。通观之,杜甫一生,是由以下五种角色连贯起来的:
第一种,奉儒者。这是早年杜甫的角色定位,反映了其家学渊源、家庭教育观念和未来人生的价值取向。杜甫在天宝十三载(754)所上的《进雕赋表》中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说明杜甫自其远祖杜恕、杜预,直至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以来,世世尊奉儒家思想,坚持遵照儒家的道德信条立身行事,数百年间坚持不变。言及祖父杜审言,杜甫颇有几分自得之意:“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能够在朝廷行修文之事,游藏书之府,作读书人的师表,俨然成为杜甫的职业理想和人生最大追求。他在《壮游》诗中颇为自负地回忆早年的这番经历:“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能够记起且最觉自豪的,是自幼以来的读书作文之事。他在长安希求举荐时也这样推荐自己: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杨伦《杜诗境诠》引范温评云:“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言儒冠事业。”所有这些关于早年的努力与经历及自身才能的称述,都清楚表明,杜甫是一个奉行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正宗儒生,其行为特征,完全符合传统儒家的职业追求:“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然而,笃信儒家思想的杜甫,其人生之路却总不顺畅和平坦,“安史之乱”只是造成其人生坎坷的社会原因之一;在此之前,他希望与所有读书人一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每次应考都铩羽而归,科举制度成为儒生杜甫希求入仕的最大拦路虎,因此他时常生出“儒冠多误身”的喟叹。
第二种,游观者。杜甫于20岁时南游吴越,是他成年以来第一次独自出游江南。《壮游》有云:
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
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
嵯峨闾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对于在北方中原地区长大的杜甫来说,吴越的历史名胜、自然景观、风土人情,都让他感到新鲜和奇异,他细心感受王谢风流遗韵,追忆吴、越两国的兴衰陈迹,生出无限古今盛衰、世道沧桑的感慨;甚至长洲芰荷的幽香,五月鉴湖的水凉,越女白皙的肤色——一切都让诗人感受强烈,热血沸腾。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北返,首次参加在洛阳举行的乡贡考试,自感信心满满,“气劘屈宋垒,目短曹刘墙”,相当自负,结果却是不幸“下第”,这个打击让他始料未及,心理上完全不能接受,故用“忤”字形容当时的恼怒心情。为了开解不快的心情,他旋即开始新一轮的游观之行——“放荡齐赵间”。这次被他自己称为“裘马轻狂”的游历,杜甫自述有云:“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颇有几分游侠习气,故后世评论者誉之为“游侠少年图”。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游历表现出来的侠客之风,恰在其落第失意之时,侠客被韩非定义为“以武犯禁”,自古以来就是游走于体制之外、而以为民除害为己任的社会角色,其主要作用之一便是对抗权势、为社会弱势群体打抱不平。杜甫用“放荡”“轻狂”的姿态展示一个遭遇入仕打击的侠客血气,自然含有某种对科举的不平情绪和向当权者“示威”之意。
第三种,干谒者。度过八九年的“快意”游历生活以后,杜甫于天宝五载(746)回到长安,即将开始他困居长安十年的酸辛生涯,扮演一个奔走于达官显贵之门、低声下气希求荐用的干谒者角色。杜甫有《今夕行》记录其初到长安的情形及心态: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诗中描述了诗人初到长安的一腔热血与英雄壮志,但是苦于求告无门,在客舍里无聊至极,只得以博塞为戏自寻“欢娱”。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见,当时杜甫心境是何等苦恼和烦躁,正经受着干谒权贵前的心理煎熬。经过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杜甫在除非干谒求进别无良途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下儒生的脸面及读书人的自尊,奔走求用。不消说,每一次奔走与求告都是痛苦和屈辱的,他自己对这段人生经历描述为: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按照其《进封西岳赋表》的说法:“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生活十分困难,完全没有自尊自信可言了。在困居长安期间,发生过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者诣阙应试而被李林甫以“野无遗贤”为由悉数摈斥的事件,杜甫再遭摈斥;天宝十载杜甫上《三大礼赋》而得到玄宗赏识,下令待诏集贤院,次年召试文章参列选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十四载,授甫河西尉,而他推辞不拜。为什么杜甫一直苦苦觅求的入仕机遇,真正官职到手却辞而不拜?诗人在《官定后戏赠》一诗中有所剖白: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自言不愿作河西尉,是不想为斗米折腰;接受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只是喜欢它的逍遥自由和那点微薄的俸禄,聊以解决生计而已。王嗣奭解诗的末句云:“曰‘向风飚’,知率府亦非所欲,为贫而仕,不得已也,不平之意,具在言外。”杜甫十年干谒请求,一旦得到官职却不怎么当回事,恰好体现了其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当然本色。
第四种,客居者。杜甫被任命为胄曹参军不久,他就启程前往奉先探亲,足见其确实逍遥自由。但随即“安史之乱”爆发,他在鄜州闻知肃宗李亨即位灵武,遂直奔行在,途中陷身叛军,随即侥幸逃身,麻鞋见天子于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但不久因疏救房琯,诏下三司推问。从至德二年(757)四月获职到次年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除去被三司推问,他作左拾遗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乾元二年(759),因关辅大饥,百姓纷纷逃难,48岁的杜甫也弃官加入流民队伍,开始了其后半生漂泊不定的客居生涯。《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诗人已经非常清楚,战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轨道,他将开始的漂泊不定的生涯,是自己根本无法预计和支配的,不知道何时是头,何处是归宿。由秦州经同谷,辗转进入相对安定的四川,投奔友人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在成都锦江边定居下来。关于杜甫的居所,两《唐书》本传均有“结庐”字样,但没有说明其居住的茅屋是杜甫自建还是严武援建,杜甫在秦州已是“负薪採橡栗自给”,生计已极为困难,他没有财力自建居所,应是严武施以援手。《旧唐书》本传对杜甫在草堂的生活有这样的描述:“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这一方面揭示了杜甫在成都的客居生活,由于得到严武的照顾,确实相对安定,但同时也说明,正是诗人亲自劳作,尽量自食其力,有了对普通平民生活的真切体验,有机会与田夫野老无拘无束地交往。他作为一个客居的流民,其平民角色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角色意识,在《客至》一诗中也有最贴切的体现:“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诗歌毕现杜甫客中待客之道,虽然接待客人不算丰富隆重,但其热情真诚十分到位,也许是客居的身份与感受,让他倍感睦邻友好之珍贵。
严武去世以后,杜甫失去依凭,不能继续在草堂居住,辗转顺江而下至夔州,两年间在赤甲、瀼西、东屯间迁居,其情形比成都草堂差了很远。《客堂》述及严武“累奏资薄禄”的事,说明他在成都生活可以不愁温饱,这和经严武多次奏请得到的一份检校工部员外郎的朝廷俸禄有直接关系。居夔时没有了这份皇粮,日子顿时拮据起来,加之衰病困扰,漂泊的生活更加艰难。观其“旧疾甘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别家长儿女,欲起惭筋力”的诗句,可见诗人晚境寂寥、盼北归而不能的困窘之状。
第五种,卧疾者。从大历三年(768)初出峡到五年(770)秋冬之际卒于耒阳舟中,近三年的时光,杜甫几乎都在荆湘间漂荡转徙,此时的杜甫贫病交加,境况极为凄凉。他本来身体较弱,自言“少小多病”,四十多岁开始的漂泊生涯,居无定所,衣食难保,多种疾病难以及时调养诊治,随着年龄增长日益严重。流寓夔州时,苦疾、采药、寻方治病的诗就频繁出现:“遭乱发尽白,转衰病相婴”;“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多病的悲秋客,连一向喜欢的浊酒也不能消受了。入湘以后,藩镇生乱,诗人生计落空,病情日甚,临死前所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诸友》等诗,集中反映了其人生旅程行将终结时的惨状。所谓“生涯相汩没,时物正萧森”;“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现实世界留给诗人的最后印象,竟是如此疮痍,如此无望!浦起龙评此诗云:“公诗本苦多乐少,然未有苦至此者。竟是一篇绝命词。”伟大的诗人在寂寞、贫困和绝望中告别了他为之千愁百结的世界。
三、杜诗的平民情怀
杜甫的一生,无疑是政治失败的一生。科举失败,决定他输在了仕途的起跑线上;求告无门,使他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梦想彻底破灭;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则把他完全抛入了流离失所的难民行列。然而,正是其政治上的一路失败,促成了杜甫平民角色的社会定位,及其日益深厚的平民情怀。概言之,亦有五种情怀:
第一,仁爱情怀。这是杜甫作为传统儒生从小培养和形成,并在其后来诗歌中展示最充分的一种人文关怀情怀。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者爱人”,并且主张将这种仁爱推己及人。杜甫诗歌,当天下未乱将乱之际,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作于天宝十三载,诗人眼见天子荒淫,奸佞当道,忧心乱局已成,国将破碎,民将涂炭,故有“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优”,“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等语,大声疾呼,危言耸听,其中蕴藏的是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重情怀。浦起龙评此诗有云:“顾此诗之作,犹在升平京阙间也。恐所云‘秦山破碎’‘不辨皇州’,及‘虞舜’ ‘云愁’ ‘瑶池’‘日晏’等语,比于不病而呻。故起处先着‘旷士’ ‘百忧’二语,凭空提破怀抱,以伏寓慨之根。此则匠心独苦者也。”诗人自言不是“旷士”,是对其儒生角色的清晰体认。当天下未乱之时,预忧国家动乱给百姓带来的可怕灾难,则根于其时时为国为民分忧的仁爱情怀。次年十月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是在安禄山叛乱发生的一个月前,诗人看清叛乱随时可能发生,故忧国忧民之情更显急迫,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三复致意,用心至切。王嗣奭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二语云:“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尘纳沟,孔子得之而欲立欲达,圣贤皆同此心。”对于诗人杜甫而言,想作稷契是否作得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的情怀值得感佩。
当天下乱局纷扰之际,则既忧家,更忧国;既忧己,更忧民。乾元二年,诗人自洛阳归巩县,目睹战乱之后国破家亡景象,作《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不归》诸诗,表达其对亲人的牵挂之情: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
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
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
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得舍弟消息》)
没有经过乱离之苦的人,一定难以领会诗人的矛盾心境与痛苦情怀:眼见故乡残破,故劝其弟以他乡作故乡;而彼此悬隔,不知生死存亡,只得饱尝牵挂之苦;睹家书而思亲人,可惜家人离散,早已物是人非;连家犬也感知主人的愁苦,故作垂头无趣之状!从这絮叨婉曲的思亲念亲言辞中,人们不难领会诗人对家人的那份深厚情谊。同年由洛阳返华州途中,诗人作有著名的“三吏”“三别”,王嗣奭认为,这些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没有亲身见闻,固然不能具体描写战乱的惨象,官吏的暴掠,以及百姓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有杜甫忧国忧民的仁爱情怀,即使见了这些人间惨象也写不出“三吏”“三别”,因为言其事而无其情,是根本不能令千百年的读者为之感动下泪的。后来杜甫流寓成都,有茅屋数间聊以栖身。因风破其屋,诗人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最为著名,历来对其解读亦各有不同。其实,诗人是否拥有广厦千万间来大庇天下寒士,并不重要,后人最应该致敬的,是诗人己溺己饥的仁者情怀,王嗣奭说“真有此想头,故说得出”,是直指心源的最有见地之言。诗人本是一流寓他乡的难民,自然最珍视来之不易的茅屋;而当茅屋被吹破之时,他特别能体会天下寒士没有栖身之所的愁苦,用广厦庇寒士,明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这是诗人最仁慈、最具爱心、最感动世人的美丽幻想!
第二,天地情怀。游观天下,对于唐代读书人而言,是自身成长必不可少的“功课”。李白一生好为名山游,创作出了不胜枚举的讴歌名山大川的壮美诗篇;岑参有了不止一次的西北异域生活阅历,才写出了那些奇峻瑰丽的边塞杰作。杜甫科举落第,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虽说当时带有某种“负气”之游的意味,但从诗人增长见识、丰富阅历的角度看,乃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应视为诗人的必然选择。因此,当诗人完成数年的游历作回顾时,他的最大感受是“快意”,留给诗人的回忆是十分美好和珍贵的,诗人获得的体验与感受也是极为丰富与深刻的。善游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各地的山川景物,民情风俗,更可以通过凭吊历史人物和历史遗迹,抚今追昔,感念古今盛衰之道和历史演变规律,甚至可以得自然之气,究天人之理。“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诗人在吹台之上,实现了对历史、地理的时空穿越,与古人对话,与天地一气,具备了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天地情怀;“荡胸生曾云,决眥入归鸟”,在诗人想象自由驰骋的天地里,是不是身在泰山之巅已经无关紧要,在艺术的想象中一样可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情感陶冶,其神鹜八极的艺术心灵,完全冲决了时空的视域和机械的现实。人为万物之一,天地与我同理,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对物我关系的普遍认识。欲知人世盛衰之理,必穷万物盛衰之理;欲得世道人伦之情,必得自然万物之情。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须得把扁平、静态的历史记忆与立体、鲜活的现实世界结合起来,才能洞晓事理、体察人情。杜甫具有胞民与物的仁慈之心,并且愿意担荷天下的一切苦难,与他所具备的天地情怀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酸辛情怀。困居长安的日子,对于诗人杜甫而言,最强烈的感受恐怕是生活的酸辛、求告的屈辱、世态的炎凉。天宝六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述“旅食京华”境况,扣富家之门以乞食,随肥马之尘以求进,备受达官显贵与富有之人的冷遇和白眼,让他真正感受了贫富、等级之间存在的天壤差别。没有切身的困苦经历和真实体验,就难以领略穷困饥饿的滋味,遭人歧视的屈辱。九载《进封西岳赋表》云:“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十载《进三大赋表》云:“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同年《秋述》云:“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十三载《进雕赋表》云:“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于仕进。”读这些接二连三的陈情之辞,可以想见诗人越来越艰难的生活窘况和寂寞无助的悲凉处境。这种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对于诗人正视时弊、洞察世情,是必不可少的,他能够在后来的战乱中广泛关注民生疾苦,对社会底层的民众寄予深切同情,甚至有愿意担荷天下全部痛苦的仁慈之心,与他在长安的这段不平凡心酸经历密不可分。
第四,迁徙情怀。杜甫的后半生,是在迁徙不定中度过的。虽然期间的生活境况有好有坏,但迁徙的不确定感、客居的寄寓感,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消失过的。在被迫迁徙之中,他必须考虑每到一处的生存问题、居所问题等,必须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和各种不可预测的复杂因素,必须面对未来生活不可知、不可控的严峻事实。这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而言,命运着实太残酷了。《客堂》诗所谓“死为殊方鬼”,“南雁意在北”云云,正道出了一个长期漂泊迁徙者的特殊心态与真实情怀。他乡的生活再好,环境再美,在客居者的眼里,始终都是陌生的“殊方”,他无法产生故乡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茫茫无期的漂荡生涯,愈来愈强烈地让人激起回归故土的渴望和需求。《秋兴八首》其一:“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在客居者的心中,一草一木,足以触景生悲,一朝一暮,无不倍感晚境凄凉。杜甫在迁徙时期特多感兴、遣怀之类的作品,即是这种迁徙情怀的突出反映。从杜甫的创作历程与诗风演变看,不幸的迁徙颠沛生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深化了其平民意识与情感,完善了其艺术表现风格。黄庭坚特别推崇杜甫两川和夔州诗,认为其妙处乃在于无意为文而意已至,实现了《诗经》与《离骚》的巧妙结合,则是甘苦有得之言。诗人把他的真实经历、真实感受娓娓道来,不造作、不虚饰,率意真切,诚挚感人。
第五,伤痛情怀。杜甫的伤痛情怀,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日臻老境,伴随永无休止的漂泊生活,身体越来越坏,疾病越来越多,给他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身体痛苦;二是愈到晚年,面对自己人生的穷愁末路和国家日益衰败的矛盾现实,忧国忧民的诗人由对现实和未来的深深绝望而产生的心灵痛苦。二者交互作用,加剧了杜甫晚年诗中的伤痛情怀。所谓“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就是诗人临死之前真实感情的集中表露:苦的岂止是个人的穷通悲喜,实则更主要的还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愁的也不单是身体的衰病,实则心情的悲凉与绝望更为深沉。浦起龙云:“(杜甫)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人所见所闻所感,无不令他揪心绝望。被称为杜甫绝命词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有句云:“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人间的桃花源已经无迹可寻,穷愁潦倒而一息仅存的诗人,耗尽了身体的最后能量和忧国忧民的全部情思,带着满腹的遗憾与痛苦,向亲人和世人作了最后的告别。
注释:
①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我的作诗的经过》,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②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③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提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④⑤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论诗三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235页、第235页。
⑥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⑦郭沫若:《历史人物·序》,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⑧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版1983年版,第343页。
⑨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611页。


⑭⑲㊵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8页、第1439页、第1448页。


⑰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1728页。
⑳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98页。
㉑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81页。

㉕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4-245页。

㉗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2页。

㉚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3页。
㉛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8页。
㉝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1-1693页。
㉞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66页。
㉟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8页。
㊱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
㊳王嗣奭:《杜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㊴王嗣奭:《杜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㊹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08页。
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页。
㊼华文轩编:《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

㊾浦起龙:《读杜提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