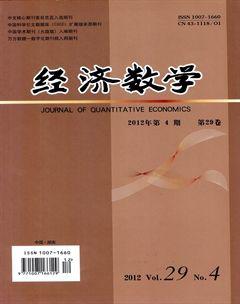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王海军 郑少华 刘国栋
摘要 在分析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母国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OFDI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企业OFDI为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中国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变量与O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表征制度质量的法律与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等四个基本因素和表征政府参与的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两个变量均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增长对OFDI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和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据此,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等来化解国家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制度变量;政府参与;OFDI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已经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占据重要地位(UNCTAD,2012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pp.4.).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流量)的份额仅为9.4%,而到2011年,这一比例已高达27%.2011年世界20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中半数为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数据来源:UNCTADWIR2012Overviewen.pdf,pp.3.,这其中尤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为迅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年流量从1990年的8.3亿美元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Annex Table 2,pp.4.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5545〈=1.发展到2011年的658.1亿美元,并呈现出流量增长快、存量规模扩大、区域和行业分布广泛的特点.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69万亿美元,以此计算,2011年中国OFDI流量占全球的比例为3.89%,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名列全球第六位数据来源:http://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2AnnexesTablesen.pdf,pp.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十年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0%数据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pp.190-192. http://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1Fullen.pdf..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这一新变化,使得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成为国际投资研究领域的热点.在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优势理论和生产折衷理论等传统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涌现出技术地方化理论(Sanjaya Lall,1994)[1]、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 T. Wells)[2]、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John A. Cantwell,1990)[3]等一批代表性的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和动机给予了不同角度的解读.但是这些理论的研究框架本质上仍然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基础上,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归结于技术外溢、比较优势、资源寻求、规模经济和市场获取等物质因素,而忽视了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内部制度环境和政府因素对OFDI所起的作用.而有些研究虽然意识到了制度和政府因素对于OFDI的重要性,但是也仅仅是从东道国吸引外资角度进行分析,而缺乏从母国角度的研究.同样,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中也缺乏母国制度和政府因素视角的研究.因此,当前的研究现状均无法深入的反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OFDI的一般特点.为此,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的OFDI为例,分析其自身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对于OFDI规模增长的影响,以其得到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经济数学第 29卷第4期
王海军等: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2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围绕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展开的,尤其是集中于对技术、资源、市场等物质条件的研究,但是对于制度和政府在FDI中的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与FDI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2.1制度因素与FDI的研究成果
制度是为了界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建立的规则和秩序(North, 1990)[4].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在经济行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而制度可以通过限定行为的可选择范围来提高经济行为的可预测性,进而减少不确定性风险(Rodrick et a.l, 2004)[5].制度约束并且限制着人们的行为,决定了商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则影响着在该国范围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也会影响跨国公司对该地区的投资行为(Delios& Henisz,2000)[6].实际上Dunning(2008)已经指出制度力量对于企业的战略选择而言有可能阻碍也有可能提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7].
制度同有形物品一样,也存在高低优劣,高质量的制度,即完备的、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的推动作用(Mishra Anil,2007)[8].而作为区位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因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必须要能够适应东道国的制度(Oxley,1999)[9],否则无法实现其预期利润目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东道国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东道国家的相对优势而扩展自身的能力.因此,如果选择的投资东道国的制度框架较为薄弱,跨国公司将负担较高的交易成本,这就阻碍了潜在交易(Meyer,2001)[10].而那些有利于增加其资源和能力的制度对FDI来说更具吸引力.因此,制度质量的好坏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制度质量优异,则能够降低FDI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减少投资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North,1990),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更快实现收益.而差的制度则可能与腐败和政治不稳定性相关,糟糕的制度效率或完全无效的制度管理(如制度执行乏力、腐败、官僚体系运行不健全、政治不稳定等)将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利润(James P. Walsh and Jiangyan Yu,2010)[11].
BenassyQuere等人(2007)认为制度质量包括私有产权的保护、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拓展以及低水平的腐败[12].而Agnès BénassyQuéré(2007)则进一步指出,东道国制度因素除了可以独立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也可以直接影响FDI的进入.包括政府效率、官僚机构、腐败因素、信息质量、金融监管以及法律制度等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好的制度的确可以吸引外资,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且制度距离可能降低双边对外直接投资[13].
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很多学者关注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制度质量与FDI的关系,例如Nauro F. Campos& Yuko Kinoshita(2008)研究了东欧和拉丁美洲的FDI决定因素归纳为金融改革、私有化、基础设施的层次和质量[14].Felix P. Meier zu Selhausen(2009)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国家(SSA)并没有因为自然资源等吸引外资的因素而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许多非SSA国家则通过制度改善吸引了更多高附加值的FDI,因此对于SSA国家而言,吸引外资的长效机制应当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和基础设施的提高[15].
此外,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母国制度因素对于OFDI的影响.如Globerman and Shapiro (1999) 就认为好的制度无论对于吸引外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都具有积极作用,因为它能够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并购创造有利条件降低不确定,提高投资回报率并促进投资的形成[16].Globerman and Shapiro (2002) 检测了政府治理指数对于FDI和OFDI的影响,他们发现好的治理能够对外资和对外投资发挥积极影响[17].
当然,对于母国制度环境与OFDI的关系也有也有相反的结论.Saime Suna Kayam(2009)认为制度环境诸如官僚体制、腐败和投资风险对于OFDI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影响.他认为政府的稳定性、投资利润和官僚体系的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OFDI的减少,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形成实际是对于本国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一种规避反映[18].而Michael A. Witt(2007)更是证明22个发达国家的OFDI增长与本国制度环境存在消极关系[19].
2.2政府作用与FDI的研究成果
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其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而企业则必须遵守.与此同时,企业则存在对政府政策的博弈行为(Boddewyn,1988) [20].根据上述理论,政府是经济活动的规制者、协调者和仲裁者,政府制定法律来规范经济运行,构建竞争环境和塑造企业所遵循的行为准则(Henisz,2000) [21].与此同时,政府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政府决策者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企业对于监管变化所做出的应对反应,如果政府未能充分抓住这样的反应可能会使那些政策不仅无效,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Kogut,1991) [22].而且,政府对于经济而言不是外生的,相反,既然企业可以将政策制定者内生到企业决策中并形成议价能力,政策环境就可以被塑造并促进企业提升国家的竞争力(Boddewyn and Brewer,1994)[23]. 随着发展中国家深入的参与到全球竞争中,这些经济体中的企业对于政府而言将变的日益重要,因为这些企业有助于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比如刺激经济增长、推动技术革新、提高国家竞争力(Luo, 2001) [24].可见政府的参与和推动不但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Yadong Luo(2009)认为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可以弥补发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劣势和不足,可以更好的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政府可以利用金融或非金融的支持帮助企业免遭后动劣势、核心优势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本国企业OFDI,既可以实现跨国公司的成长,也可以保证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对于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也有重要作用,甚至,扶植本国企业OFDI本身也是政府为经济和政治目标服务的.Yadong Luo(等人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支持本土跨国公司来实现其国际化、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其主要作用在于:1)创造OFDI的激励机制;2)简化管理程序(包括向地方政府分权);3)放松资本控制;4)提供投资信息和指导;5)降低政治和经济风险.[25]
Wang(2002)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驱动型的,其背后动因除了国内需求不振、自然资源不足等传统因素外,还包括接近和获取国外技术、专利以及维护政治关系等“中国特色”的因素.[26]
裴长洪、樊瑛(2010)进一步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既不能用垄断优势论解释,也不能用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制造等理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优势在于中国政府对内的法律制度、财政金融和巨额外汇储备等,对外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境外产业集聚区等政策和服务形成的国家特定优势.[27]
中国政府对于OFDI的作用除了大量实施的促进政策(如“走出去”战略),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有产权制度.Peter J Buckley et al(2007)认为国有产权制度是中国大型跨国公司特有优势.这种被母国政府所调控而带来的所有权优势可能促使中国企业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而且当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并得到中国政府持续提供的政治、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时,这种所有权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28]
综上所述,制度质量不仅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同样对于OFDI也有着重要作用.结合中国等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本文认为,母国制度质量对于OFDI的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1)法律制度对于产权界定和保护,有助于减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国内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OFDI本质上讲是企业国内生产经营活动的国外延伸,必然离不开国内制度环境的影响.显然,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减少企业国际化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2)市场导向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推动更加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和秩序,从规模经济角度看,有利于企业国内的充分竞争机制的形成,实现优胜劣汰,进而将刺激和鼓励部分高度市场化和规模化的企业推行国际化战略(Helpman,2004)[29],或者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本身就是这种市场导向的必然结果;3)政府的效率、政策的连续性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性,这三方面的改善将直接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预期收益.
而政府对于OFDI的作用就更为直接,其作用途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方向:第一就是上述讨论的国有产权制度.政府通过国有产权的界定和管理,能够对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流向、规模和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就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扶植政策,比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外汇政策以及投资保护国际协定政策等,能够对OFDI的收益产生影响;第三就是通过政府自身对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政府机构运行效率等的变化,间接影响OFDI的运行活动.
而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之间也存在有机联系,政府行为可以通过影响制度环境来对OFDI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比如政府通过政策实施,或政府本身运行效率及稳定性等方面来对OFDI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以中国OFDI为例,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自身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对于OFDI规模增长的影响.
3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3.1研究假说
根据现有理论分析,尽管一定程度上母国制度环境的改善可能会降低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倾向,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总体上,国内制度环境的完善,即制度质量的改善有可能为OFDI创造有利的国内环境,甚至OFDI本身就成为国内制度改善的一种标志.为此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制度质量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母国(中国)制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
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程看,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府的推动和支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投资、贸易、金融、税收以及所有权制度方面制定一系列鼓励投资政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更是明显的反映出中国政府参与和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需求.为此,提出假说2
假说 2政府参与对OFDI有直接促进促进作用,而且同样存在正向关系.
当然,除了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对OFDI的影响外,从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规律来看,母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必然会促使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而出现OFDI,母国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活动强度和规模等方面也影响OFDI,为此提出假说3:
假说 3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等宏观经济变量与OFDI也存在一定联系.
3.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计量经济学模型建立的一般规则,变量选取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被解释变量,二是解释变量,三是控制变量.其中:
被解释变量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的年增长率,该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
解释变量为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
对于制度质量的衡量,选取美国ICRG集团公布的政治风险指数中反映制度质量的四个基本指标,分别是:1)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该指标主要反映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而秩序指标主要衡量公众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分值从0~6分;2)政府稳定性(Government Stability):该指标反映政府实践其竞选承诺和连任的能力,其由政府的统一、立法强度和公众支持三个因素组成,分值0~12分;3)官僚体系质量(Bureaucratic Quality):该指标反映政府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的运行效率、政策的执行的连续性和官员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分值0~4分;4)腐败程度(Corruption.):主要是对政治体系中的腐败进行评估.腐败无疑将扭曲市场交易规则,扰乱经济和金融环境,进而威胁对外投资,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效率,分值0~6分.以上四个指标分值越大表明各自代表的制度质量相应越高.
为反映中国政府参与的影响,选取国有化程度和政府政策两个变量:
1)国有化程度(Nationalization):指中国对外直接存量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具体数据来源中商务部公布数据;2)政府政策变量(Government policy):考虑到政府宏观政策的定性性质,引入相应虚拟变量.以政府宏观政策是否积极促进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为标准,相对限制阶段取值为0,积极鼓励时期为1.
此外,根据现有研究文献,选取了三个常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1)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经济增长率越高代表这个国家经济活力越强,其市场发展发展潜力越大,也能反映出该国对外投资的潜力和实力,因此,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率越高的时期往往也是对外直接投资活跃的时期.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2)出口依存度(Ratio of Export Dependency):指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该指标既反映了一国经济开放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企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越强,对外投资的扩张能力也越强.该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3)汇率(Exchange Rate):Aliber(1970)认为持强币国的资本化率高于持弱币国,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持强币国流向持弱币国,因为,前者在购买后者的实物资产时,后者的资产价值低而使购买成本较低.因此,一国本币升值时会促进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该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
预计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共6个指标的预期符号均为正,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率与出口依存度为正,汇率的符号为负.
4计量模型构建与分析
4.1模型设定
本文的模型借鉴Buckley(2007)、Daniels and Trevino (2007)[31]以及Duanmu and Guney (2009)[32]等人的研究思路,利用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制度质量、政府参与和OFDI的动态实证分析模型,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方程(为消除异方差,以下所有变量除虚拟变量外均取对数形式):
4.2变量描述性统计检验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于各变量均为对数形式(除虚拟变量外),整体上看,各个变量的差异变化不大,但是相对而言,OFDI和虚拟变量的数值在各个时期的差异较大.
本文还计算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较低,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限于篇幅未予列示.
4.3ADF平稳性检验
由于所选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如直接应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模型,很可能导致伪回归发生.根据计量建模的原则,需要对变量((除虚拟变量外)进行迪克-弗勒检验,即ADF平稳性检验,以确认变量是否属于同阶平稳序列.经检验(见表2),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4.4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对时间序列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一种统计验证.由于已对OFDI等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且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故可进行协整检验,具体而言就是对方程(1)的拟合残差resid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4.5模型估计结果及说明
表4中所有回归结果均为最小二乘法估计所得,从模型的判定系数及联合检验水平来看,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其整体估计的拟合优度也都较高.根据以上估计方程,本文对计量模型中回归结果给予进一步说明:
模型(1)显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6个解释变量均不同程度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其中尤其是log LAW和log GOV_STA两个反映中国制度质量的指标的显著性最强,回归系数也最高,这在其他5个模型中也是一样,二者对OFDI的影响系数达到了1.186和3.334,这说明法律和秩序与政府稳定性的改善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强正向联系.此外,官僚质量的提高、腐败程度的降低、国有化程度及政府政策四个变量对OFDI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其回归系数分别为1.085、0.035、1.197和1.055.因此,基本可以判断中国制度质量的改善和政府参与的加强的确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验证了假设1.
模型(2)-模型(4),是将三个控制变量逐渐加入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log ER外,其余两个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使的OFDI存量增长率加快38.479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物质基础.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这与本文之前的假设是相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出口增长对于OFDI就没有促进作用.实际上,出口的增长一直是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进而也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资金渠道,但是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轨迹上看,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跨国经营的两种基本战略,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Robert,1957),即在一国开始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初期,出口可能居于主要地位,但是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将显著的增长,这个时候往往表现为出口依存度的稳定或降低,中国近几年的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出口依存度已经由2007年的最高值37.53%下降到了2011年25.89%.而且,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以GDP为计算基数的出口依存度进一步降低了;最后,实际汇率与OFDI呈现负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吻合.实际汇率主要影响海外资产的购买力和结算价格,人民币的相对升值将增强人民币兑换美元后购买力并有助于降低汇兑成本.
模型(5)和(6)是将变量GOV_POL与log LAW和log BURE的交叉项逐个引入到模型中的计量结果,总体上看,以交叉项作为新解释变量在上述两个模型中也都是显著的,而且交叉项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与模型(1)中相应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一致,这表明政府除了通过所有权控制和直接投资政策对OFDI发挥积极作用外,还可以通过改善国内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官僚体系运行水平来间接促进OFDI.
5结论与建议
中国企业OFDI的决定和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是从母国制度环境和政府作用角度研究OFDI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本文通过引入表征制度质量的四个指标和表征政府参与政府的两个变量,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政府参与的加强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张的重要动因,尤其中国政府的稳定性、法律秩序、所有权程度以及政府政策四个因素对于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最为显著.据此,建议:1)中国需进一步保持政治和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贯性,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提供稳定的国内环境;2)保护私有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民营和私营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分布和规模,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3)鉴于中国企业OFDI中的产权制度背景,政府必须在建立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加强风险管理和考核机制,保证资产安全和出资人权益.
参考文献
[1]Lall SanjayaIndustrial strategy and polic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995, 2(2):34-51.
[2]刘易斯、威尔斯第三世界跨国企业[M].叶刚,杨宇光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23-25.
[3]John A CANTWELL, Paz Estrella TOLENTINO.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 [M] University of Reading Discussion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1990, No.139.
[4]D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ew York:Norton,1990.
[5]D RODRIK.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9, 4:385-412.
[6]J H DUNNING, S M LUNDAN.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4):573-593.
[7]A DELIOS, W HENISZ. Japanese firms: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305-323.
[8]Anil MISHRA, Kevin DALY. Effect of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7,16 (2):231-244.
[9]Les OXLEY, David GREASLEY. A nordic convergence club[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1999,6(3):157-60.
[10]Laurence MEYER H. Payment of interest on reserves[R].Testimony before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nsumer Credit,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01:4-6.
[11]P JAMES WALSH, Jiangyan YU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ectoral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R]. IMF Working,2010,187:2-6.
[12]A Bénassy QUERE, M COUEP, T MAYER.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The World Economy, 2007:30(5):764-782.
[13]A Bénassy QUERE, Coupet MAYLIS,Mayer THIERY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The World Economy,2007,30(5):764-782.
[14]Campos NAURO, Kinoshita YUK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 reforms:panel evidence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R].IMF Working Paper,2008:4-6.
[15]P Felix MEIER ZU SELHAUSENOn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a cross countr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bsaharan african relativ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R]. Documentos de trabajo sobre cooperación y desarrollo 2009:3-5.
[16]S GLOBERMAN, D SHAPIRO.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canadian experie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3): 513-532
[17]S GLOBERMAN, D SHAPIRO.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34(1):19-39.
[18]Suna Kayam SAIME. Home market determinants of FDI outflows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R].MPRA Paper 16781,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2009:1-3.
[19]A Witt MICHAE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escape response to home country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579-94.
[20]J B BODDEWYN. Political aspects of MNE theor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19:341-363.
[21]W J HENISZ.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02,16: 334-364
[22]B KOGUT. 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border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 33-47.
[23]J BODDEWYN, T L BREWER. Internationalbusiness political behavior: New theoretical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1): 119-143.
[24]Y LUO. Toward a cooperative view of MNChost government relations: Building blocks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1,32(2): 401-420.
[25]Yadong LUO, Qiuzhi XUE, Binjie HAN.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Experi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9,45(1):68-79.
[26]M Y WANG. The motivations behind China governmentinitiated industrial investments overseas[J].Pacific Affairs ,2002,75(2):187.
[27]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7):45-54.
[28]P J BUCKLEY, L J CLEGG, A R CROSS,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38(4): 499-518.
[29]E HELPMAN, M MELITZ, S YEAPLE. Export versus FD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2004,94(1):300-316.
[30]Danie KAUFMANN, Aart l Kraay, I Massimo MASTRUZZ. Governance mattersV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1996-2006[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280, 2007:2.
[31]J L DUANMU, Y GUNEY.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and India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Asia Business Studies,2009,3(2):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