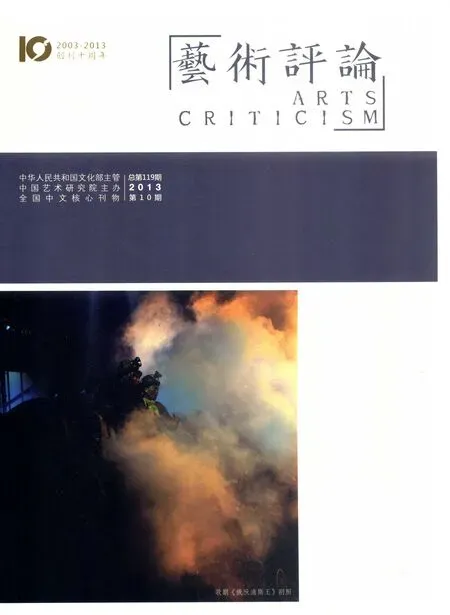音乐只表达音乐自身
——歌剧《俄狄浦斯王》导演易立明访谈录
2013-06-01 09:26唐凌
艺术评论 2013年10期
唐 凌
音乐只表达音乐自身——歌剧《俄狄浦斯王》导演易立明访谈录
唐 凌
今年七月,易立明导演了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时隔两个月,他又导演了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俄狄浦斯王》,这两部现代歌剧在天津大剧院的连续上演,一时成为歌剧界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为此,我们与易立明导演有了如下对话:
唐凌:
目前在中国上演的歌剧还是以《图兰朵》、《茶花女》、《蝴蝶夫人》等古典歌剧居多,人们相对较为熟知,而现代歌剧几乎是一个空白,但您近期排演的这两部作品均属于现代歌剧,这对于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缘由?易立明:
做古典歌剧是非常好的事情,我本人也很喜欢听古典歌剧,但那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我选择现代歌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本人对音乐的喜好,听音乐听到一定的时候,对音乐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古典作品听得太多,慢慢会觉得思考的东西在减少,更多是一种享受的愉悦,而我想,音乐其实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它可以表达的东西更多,我选择现代歌剧就是基于这个理解。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确实很少有人做现代歌剧,我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分享。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唐凌:
说到现代歌剧、现代音乐,通常人们总会说不好听,听不懂。郭文景:
现代音乐有其独到的不可替代的表现力,但由于传统的审美习惯,大多数听众会觉得现代音乐很陌生,不好听。但如果借助文学和视觉的帮助,就不会觉得现代音乐不可理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电影中有很多的场景为了渲染气氛而创作的音乐,所使用的大都是很现代的手法,但是与电影情节和画面配在一起,就没有了审美上的障碍。而且,现在是21世纪了,斯特拉文斯基也成古典作曲家了,巴托克更不用说了,现在也是古典音乐了。
导演:易立明
易立明:
就是我们的民国初期。杨乾武:
对,20年代。唐凌:
关于这部剧的呈现方式,是那天演出后的热议话题,反应不一,有热烈的,有疑惑的,也有些惴惴不安的。大幕拉开是火车满载着黑黢黢的煤矿工人的合唱,许多人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郭文景:
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搞创作的人最难回答的问题。易立明:
是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火车?为什么是煤矿工人?郭文景: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应该被提出来,只要和音乐的精神和灵魂契合,煤矿工人或者是炼钢工人,我以为就都可以。易立明:
对我来说,古希腊是一个遥远而又美好的想象,但是当我听到《俄狄浦斯王》的音乐的时候,完全是一种我们熟知的重工业的感觉,它的质感绝对不是现代的电子工厂,也不是早期农业时代的田园图景,它属于工业革命时代,它让我想到了我们所经历的大炼钢铁。我最早也曾设想,一列火车停在了荒原,音乐就在这列停滞不前的火车上展开,结尾是火车重新启动,从在枕木上爬行的俄狄浦斯的身上压过去,特别的残酷。但最终我还是手软了,没有这么做。唐凌:
尽管你手软了,但现在这个舞台仍然充满了力量和刚健之美,当下中国舞台上很少这样的气质,太多的声嘶力竭和所谓的恢弘大气很多时候只是假阳刚。易立明:
其实当我把那个火车头想好以后,舞台的气质就已经确立了。杨乾武:
很干净很精炼,直接抛出来,不叙述过程,所以特别有力量。易立明:
《俄狄浦斯王》的音乐很特别,没有序曲和前奏,乐队奏响的第一个音符就是合唱,有一种拉响警报的意味,我之所以用一列满载工人的火车直接冲到台上,就是因为它很强烈,直接而有力量,符合这段音乐的气质。郭文景:
我特别喜欢易立明的这个处理,他让观众对音乐获得了突破性的感受。易立明:
就是禅宗的棒喝的方式,就是这一下子。杨乾武:
这个《俄狄浦斯王》相当有剧场的形式感,我很吃惊,因为此前知道这是一部清唱剧,但这次舞台上完全是戏剧化的歌剧。易立明:
现在这个舞台也是用写实的方法,只是场景转换了一下而已。唐凌:
这个舞台看上去是写实的,其实是超现实的。在剧场中,观众多少有点难以名状的兴奋,被音乐和舞台的气势征服,但是我在感受震撼的同时,残存的那一点理性也在逼迫我思考一个问题,即我激动莫名却又若有所失,似乎没能感到内心深层的触动。为什么会是这样?会是什么问题?
徐瑛:
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戏剧文学被作曲家和导演联手灭掉了。在这部歌剧中,戏剧文学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唐凌:
有同感。好像是不是俄狄浦斯,已经不重要了。徐瑛:
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是极具震撼力的,但歌剧《俄狄浦斯王》的音乐和导演的手法在视听上给观众带来的冲击力太强烈,以至于观众已经不再关心人物的命运。杨乾武:
我的感受跟你们不一样。戏剧性不是故事,讲故事是电视剧,是好莱坞电影,不是戏剧的精华。从戏剧的角度,杀父娶母都只是背景,重要的是英雄末路,是精神上的东西。在音乐里,高级的音乐都蕴含戏剧性,我看这个戏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他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淡化了,淡化到高度浓缩到音乐上去了。现场是很震撼的音乐性和戏剧性高度的融合,但是最后是通过音乐体现出来的,恰恰是戏剧文学成为血液融入到音乐里,从音乐体现出来的,听着就很来劲!易立明:
有人说我把戏改得支离破碎了。郭文景:
你告诉他,科克托的《俄狄浦斯王》剧本就是这样的,这是二十世纪的《俄狄浦斯王》!易立明:
斯特拉文斯基一开始就没想用音乐再来讲一遍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他不想承担再给你复述一遍故事的义务,他借用了人们对这个故事的熟知,而只选取了最适合表达他的音乐的那些片段。郭文景:
斯特拉文斯基认为,为了歌剧的音乐不受影响,最好是用观众不懂的语言。如果你听歌剧,你不懂他唱什么,每一个音节就都是纯粹音乐的意义,没有文学的意义,他特别想放大和强调这个东西,所以他专门找人把这个剧本译成了大多数人都不懂的拉丁文,他觉得音乐本身是最重要的。常常是这样,即作曲家越是纯粹地追求音乐,后人处理他的歌剧的空间会更大,因为音乐是很抽象的。如果他特别具体地向文学上靠拢,这种空间反倒会缩小。杨乾武:
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为了摆脱叙事给他的音乐创作带来的麻烦,为了让音乐的表达挣脱语言的束缚,他就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并在剧本上尽可能地简化,同时选择了一门大家根本不能懂的语言,让音乐处在了主导地位。徐瑛:
我有一个想法,即音乐全然不动,重新编一个跟俄狄浦斯王没有关系但能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的故事。不知道这个想法怎样?易立明:
如果重新编一个故事,当然很好,但那就变成原创歌剧了,就是我们借用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但不能叫《俄狄浦斯王》了。徐瑛:
这部歌剧的音乐和舞台呈现都具有超强的力量,如果戏剧文学的力量也足够强大,并能做到与音乐和导演的手法浑然一体,观众的感受就会大不一样,对音乐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总之不管怎么说,我对戏剧文学的被否定还是耿耿于怀,多少有一点遗憾。易立明:
我是文学爱好者,但是为了忠实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为什么不可以否定一次戏剧文学呢?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俄狄浦斯已经不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了。他已经把最悲剧的东西消解了。作为导演,面对这样一部歌剧,我所能做的只是在结构上处理,在视觉上呈现,仅此而已。唐凌:
这与你对现代歌剧的理解,对斯特拉文斯基这部作品的理解有关。易立明:
现代歌剧更强调音乐自身的表现,音乐不再是讲述故事的工具,音乐所表现的就是音乐本身。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新古典主义音乐宣言里写得很清楚:音乐什么都不能表达,既不能讲述故事,也不能表达情感,音乐所能做的只是表达音乐本身。这是他的原话。这也是他借用巴洛克时期音乐的缘由。唐凌:
在你对这个作品的诠释中,音乐被置于的是首要位置。易立明:
音乐只表达音乐自身,这个很关键,这是现代主义最根本的审美特征。从戏剧的角度,因为根本不再有那么多的篇幅给你展开戏剧,所以你必须要找到相应的手段,非常直接地跟音乐连接。
唐凌:
能做到这么纯粹吗?易立明:还
没有,比如说原剧中俄狄浦斯刺瞎双眼,本应是全剧中最强烈的一个动作,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根本就没提供给你任何东西,你都找不到那个点,为了戏剧的呈现,我让刺瞎了双眼的俄狄浦斯在渐渐弱化的音乐中顺着铁轨爬向远方,这对音乐来说其实已经属于画蛇添足。唐凌:
您之前很重视地谈到过关于这部戏与当代人的关系,您希望这不仅仅是几千年前古希腊的故事而已,而是与当代人有一种关联。易立明:
之所以《俄狄浦斯王》戏剧能流传到今天,一定是在精神上与今天的人有深刻的关联。唐凌:
那么,这部剧中当下性究竟何在?比如说,今年拜罗伊特艺术节上演的《指环》中,原剧中对黄金的追逐变成了对黑色黄金——石油的追逐,剧中最后的世界末日则终结于纽约华尔街的股市,这种与当代的连接方式,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对应,但是有一种内在联系。每个时代的“黄金”不一样,但人性中的贪婪是永远的。当然这样的改编思维并不鲜见,这版《指环》也受到许多批评,所以我又怀疑如果这样做其实是重落俗套。但是,目前戏剧与音乐完全忠实原作,仅仅在舞台上呈现当代的场景和当代人的造型、服装,这就足以构成一种当代性,就足以显示和支撑这部剧与当代的关联吗?徐瑛:
我感觉是没有的。这个戏的舞台呈现其实是易立明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他听到这个音乐想象出来的场景画面,就是这样的一种质感。是否与当下关联其实并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他在意的是表达音乐本身,将观众带入一个审美的层面,进而给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郭文景:
我不赞成与当下的直接联系,我认为导演是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间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唐凌:
当然不是刻意的生硬的联系,在我们谈一部经典作品或历史题材的作品的当代性时,一定不是在要求与当下的直接对应。易立明: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一定会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这是我一定要想的。西方人有原罪的观念,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民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英雄和民众的关系。在这个剧中,当灾难发生以后,民众希望有一个人来拯救他们。他们祈求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挺身而出,承担英雄的责任。但人们逐渐发现,俄狄浦斯才是灾难的根源。这时民众是什么态度呢?斯特拉文斯基写民众叙述伊俄卡斯塔自杀的那一段,民众边喝酒狂欢边兴高采烈地聊着俄狄浦斯的痛苦,这样的场景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音乐的尾声我以想象加了一段戏,就是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后自我放逐,沿着铁轨往前走,回头寻求别人的搀扶,但所有人都往后退缩着说“你快走吧,你走了就是救我们,我们爱你。”俄狄浦斯是在极度痛苦与绝望中沿着铁轨爬出去的。唐凌:
这个古老故事的当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完成。从导演的角度,排演歌剧既可以忠实于歌剧情节发生的年代,也可以是时空置换的方式,您这次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方式?易立明:
以这部剧为例,如果还是拘泥地去忠实故事发生的时空,让演员穿上古希腊的服装,在舞台上盖一个神庙,我觉得会很虚假,我们做的是二十世纪斯特拉文斯基的《俄狄浦斯王》,而不是两千多年前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其实,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俄狄浦斯王》中,你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古希腊的元素了。所以我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处理,是否还能表达作曲家音乐的气质。唐凌:
即使你想还原,也已经是不可能了。易立明
:那种东西已经不是真的了。徐瑛:
易立明这样的处理,充分展示了他在创作中“蛮横不讲理”的霸道。他今年排的两部歌剧我都看了,《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排得中规中距,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式,没有超越观众的想象。《俄狄浦斯王》就有点肆无忌惮了,他完全不在乎他对作品的诠释与大众的理解是否契合,但恰恰是他的这种肆无忌惮让我们看得热血沸腾。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作品:自我表达。但这种对自我表达的强调同时也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即个性化的创作有可能偏执地走向极端。易立明:
你说“横蛮不讲理”,我是这样理解,如果有很多艺术家不讲理,创作就讲理了。正因为现在的艺术家太讲理,都想让人觉得有道理,所以我们创作才没有活力,没有个性。我希望有十个有个性的俄狄浦斯出来才好,你就可以有选择。唐凌:
可要是真的不讲理到疯狂的程度,那就自己毁灭了。易立明:
但是如果不讲理,却还能跟一些人交流,获得一些的认同,同时有继续创作的可能性,这就是最好的创作生态。唐凌:
歌剧是音乐和戏剧结合的艺术,导演和指挥分别是戏剧和音乐的主导者,往往有合作有冲突,这是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之后您与指挥家汤沐海二度合作,你们的合作怎样?易立明:
做歌剧,必须有一个跟你想法一致、有共同艺术追求的指挥,他的品位、审美的眼光非常重要。我有幸遇到汤沐海,他充满了激情,手上有魔术般的能量,而且他非常懂戏剧,我们彼此理解。唐凌:
这两部歌剧的推出均是在天津大剧院首演,天津大剧院的总经理钱程,他对普及交响乐做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现在对歌剧又情有独钟,他提出“有歌剧的城市”,其实,做歌剧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易立明:
你知道演这种戏很难有票房,天津大剧院的钱总却与我们一拍即合。他美术专业出身,艺术家气质浓厚,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他引进的剧目、乐团都非常有眼光。他是一个有艺术抱负的人。他明明知道没有票房,但是他说这事我们应该做。郭文景:
还有就是这个乐团和合唱,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去之前,本来对音乐的呈现没有抱什么希望,主要是想看易立明怎么处理这个戏。但是这次我真的很震惊,天津交响乐团和河南的两个合唱团,竟然能演奏演唱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而且还演得像模像样,让我一下子对中国的歌剧有了信心。唐凌:
总体而言,现代歌剧在当代中国还是一种缺失,不要说普通观众,就是艺术界的专业人士,对这两部歌剧也多是只闻其名未闻其声。易立明:
作为我个人,我是有一些不满足。我经历过造型专业艺术的训练,发现视觉艺术上我们走得很远,现代文学,比如说乔伊斯的作品、意识流等等,我们也多少有所了解。但在现代音乐和当代戏剧的推介上还相对比较保守。唐凌:
美术以及文学的创作,因为其个人化色彩更强,自我表达相对自由度更大。
天津大剧院总经理 钱程
易立明:
但是经历现代艺术的洗礼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文化系统不断自我再生的过程。在中国,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进入了当代,但我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甚至是上上个世纪。不了解现代艺术,谈创新谈文化的发展就有点空中楼阁。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很重要。对于现代音乐,尤其是现代歌剧,我们还处于相对陌生的阶段,即使我们的专业歌剧演员也缺乏现代音乐技巧的学习和实践。《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我勉强还排出了中国组,这次排《俄狄浦斯王》,中国组就没建立起来。中国的大部分歌剧演员,从学习到登台,唱的都还是威尔第、普契尼的意大利古典歌剧,对他们来说,掌握现代歌剧里面频繁的转调、无调性和节奏变化非常困难,他们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唐凌:
对于现代艺术的了解和学习对我们有着推动,乃至某些方面开启的作用。易立明:
是的。还有,我认为我们要理解斯特拉文斯基,一定要跟另一个人结合起来,就是毕加索。理解了斯特拉文斯基你就理解了毕加索,理解了斯特拉文斯基和毕加索你就理解了现代主义,你就掌握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命脉,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现在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优雅的、优美的、追求真理的层面上,没有看到那种文化的强大侵略性。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就有这么强大,你听懂没听懂都觉得强大,这就是力量,这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精髓所在。唐凌:
你对现代艺术有着某种亲近感。易立明: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现代主义是一个过程,我们的审美系统里必须有这个环节,那些有趣的东西会熔化到今天的创作手法当中。唐凌:
谢谢你!但这种开始的阶段总是格外艰难,这两部现代歌剧的排演,实在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尝试和努力。易立明:
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最大的价值的就是“已在”。易立明:歌剧《俄狄浦斯王》导演
郭文景:作曲家
徐 瑛:剧作家
杨乾武:北京市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唐 凌:《艺术评论》主编
猜你喜欢
南风窗(2020年12期)2020-06-12
读者欣赏(2020年4期)2020-04-19
发明与创新·大科技(2019年5期)2019-07-31
家长(2018年8期)2018-09-10
歌剧(2017年11期)2018-01-23
歌剧(2017年6期)2017-07-06
歌剧(2017年4期)2017-05-17
校园英语·下旬(2016年7期)2016-07-28
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16年6期)2016-07-02
上海文化(新批评)(2014年6期)201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