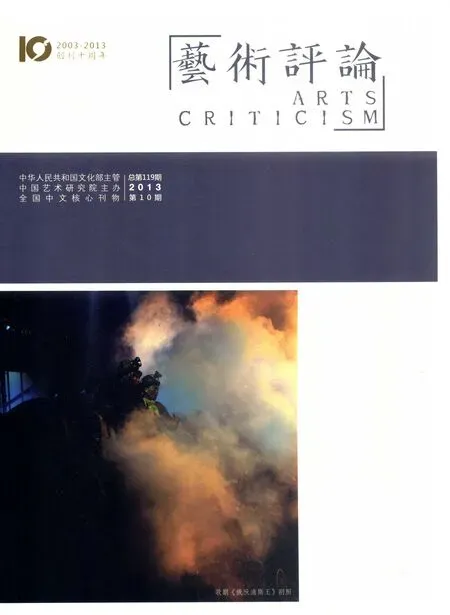传统的滋养与创造性转化
——王仁杰梨园戏剧作二题
单跃进
传统的滋养与创造性转化——王仁杰梨园戏剧作二题
单跃进
王仁杰之所以伫立在中国戏剧界,为人景仰,是他为中国剧坛剧作提供了难得的剧作。特别是《节妇吟》与《董生与李氏》等梨园戏新作,激活了沉寂东南一隅千百年的戏曲“活化石”——梨园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梨园戏不再为古城泉州一方所有,而是当下中国戏剧最为鲜活的演出形态之一,影响至全国。这也与王仁杰的剧作被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院龚万里、曾静萍等一班演员的精彩演绎直接相关,铸就了中国当代戏剧史极为显赫的篇章。
古典诗韵与当代意识
因为关注梨园戏,关注王仁杰的作品,也关注王评章对王仁杰及其梨园戏的研究。我很欣赏王评章关于王仁杰是“最后一位优雅的古典诗人”的说法。之所以这么说,是它能够反映出王仁杰及其剧作的某些审美特征,但是这种说法也让我产生些许末世之感。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最后一位优雅的古典诗人的地步了?内心不免有些惆怅。
就审美感受而言,王仁杰剧作确有古典诗韵品格,这对当下萧瑟与迷乱的
戏曲界,实属难得和幸运。在现当代剧作家中,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将语言锤炼得如此精粹、妙趣,且诗意盎然的人了。以我管见,五四以来,至少是半个世纪以来,能够真正秉承古典诗韵的剧作家凤毛麟角,而王仁杰便是其中一位。但王仁杰剧作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以及表达的人文意识,在我看来并不古旧,恰恰相反,其中包含着一种很顽强的创作力量,极具现代性和时代感。他的作品充满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符号,但是这些符号与千百年前人们的理解是不同的,他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运用这些符号,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呼唤,又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开创。这与他深厚的传统学养息息相关,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碍于学识和对传统认知有限,往往做不到。我由此想到林毓生先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说过,人的生命本身天赋就有一种原创力,但这种原创的力量需要得到生动完整且具丰富性的传统的滋养。如果没有这种滋养,这种生命的原创力很有可能导向一种混乱。由此,我们应该建立这么一种理念:艺术的创造力必须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束缚。王仁杰剧作所呈现出的这种创造力正来源于其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尊重。记得王仁杰曾对我说,他是福建泉州地区的封建头子。当然,这是一种自我调侃。如果王仁杰真是一位封建卫道士的话,那末绝对写不出《节妇吟》、《董生与李氏》、《陈仲子》这样的作品。《陈仲子》尽管用的都是大家熟悉的经典故事,但是王仁杰对这些故事的解释是充满调侃和隐喻的。这种调侃和隐喻不是站在迂腐的角度,而是他用一种貌似迂腐的眼光在看待迂腐。这类的作品表面看上去是比较含混,不清晰的,但如果静下来看,我觉得是有王仁杰的独特理解和创造的。
王仁杰剧作无疑是有当代意识的,并且很是深刻。就说《董生与李氏》吧,那绝不仅仅是在讲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也绝不仅是一种调侃和幽默,而是有一种隐喻在其中。即,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很难摆脱的精神枷锁之中;甚至今天的我们,既是这种精神枷锁的被束缚者,也是这种精神枷锁的忠实执行者,乃至帮凶。那个接受彭员外“临终托付”的董生,便是这么一个具有“帮凶”、“被束缚者”和“解脱者”几重身份的人物。戏是沿着董生的心路历程构建起来的,而李氏是不断赋予董生行动的源泉,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作为编剧,王仁杰的好处就在于他从来不善做这么理性抽象的思考,他只是以诗人的情怀去感悟两个生命体触碰后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涟漪。所谓涟漪,即是人物内心的微澜与感应,这往往是伦理与历史等视角容易忽略的东西,恰恰是诗人最为敏锐与在意的东西。如果王仁杰也直扑理念,刻意图解董生与李氏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所构建的所谓深刻性,那么他营造的舞台,也将索然无味。王仁杰则以一个风花雪月般故事框架,温润地塑造了董生与李氏两个让人反复咀嚼的人物形象,且富喜剧的滑稽幽默。特别是“监守自盗”,这是一种非常智慧的喜剧结构方式。其间,我们不难看出梨园戏独特的舞台表演手段和丰富的剧目资源,对王仁杰的滋润与影响。

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剧照

王仁杰近照
人性探幽与舞台行动
纵观王仁杰作品,无论成功或不太成功,都不着眼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恢宏与深刻,叙事以儿女情长居多,主题亦不够宏大。凡此种种,堪为“缺憾”,自然会有人责难与不屑。总之,王仁杰不善“宏大叙事”却精于“人性探幽”,是不争的事实。
此种情形,让我想起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和以法国卢梭为代表的“积极自由”两种思潮和两种路径的差异。“自然法”崇尚传统和经验,通过自发的演变实现社会的转型;“积极自由”的思想与后来的激进主义思想有渊源,崇尚“宏大叙事”,具有现实批判性,却难免自身的异化。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对立与制衡,却都在那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发挥着影响和作用。这两种思潮并存的现象,对我们还是有启迪的。我们今天貌似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方式,显然与我们经历的文化历史和现实有关,但是否就一定是当今文艺表达的唯一方式,则不宜主观武断。从个体生命感受出发,自然地发掘一些看似并不宏大的主题,却不失对人性的探索,就艺术表达而言,“终极”的审美判断来自审美主体的感知与感悟,来自作品带给剧场的魅力。王仁杰剧作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更趋于人情世故的自然流淌,也承袭了梨园戏在讲述众多小人物故事时一以贯之的“口吻”(讲述方式),就好比王仁杰无法改变他浓重的泉州口音一样。
与此关联的是,王仁杰剧作的舞台行动性很值得关注。很多人以为他的剧本虽然文辞典雅,但情节寡淡,没戏可看。是的,王仁杰的剧作极少惊天地泣鬼雄的大跌大宕,更没峰回路转的惊奇突变,极少生拉硬扯勉为其难地编戏做戏。但他的剧本立在舞台上,人物不失舞台动作,还吊足观众的胃口。那么王仁杰是怎么规定和铺设舞台动作?怎样引导台上演员的行动和控制节奏?其实王仁杰的剧作是极其讲究舞台行动性的。以我浅识,王仁杰首先是制造戏剧情境,其次是懂得适时“纰露”人物心理,再次是锤炼角色语言的性格化。剧中人物俱都沿着他“规定”的情境和“纰露”的心理态势在开展自己的行动。由此,人物的外在的行动可能并不彰显,但内在的心理动作却格外坚实可信,能说服观众。《董生与李氏》第一场通过“临终嘱托”彭员外极为荒诞的“嘱托”,一下子将董生与李氏两个本不太相干的人纽结起来了。董生将怎样去践行他对彭员外的承诺?李氏会如何承受董生对她的关照?两个巨大的问号,悄然推向观众。在这样“规定”的情境下,观众再不关心台上人物的命运,实在是不能够了。戏是随着王仁杰对董生心理的“纰露”而渐次推进的。总共五场戏,从“临终嘱托”到“每日功课”、“登墙夜窥”、“监守自盗”、“坟前舌争”每场戏的动作主施者皆为董生。尤其是“登墙夜窥”到“监守自盗”,董生的动作始于他的尽忠尽职,从监视到窥视,从攀墙而望到越墙入室,一步一步,直至赢得李氏的“你行他不行……”,每每关键处,层层“纰露”董生内心的纠结,让董生在几近酸腐的自我心理拷问与应答中,为人物找到行动的理由。即便是一个蚊虫的叮咬,也生发出对己的责难与怀疑,转而又获得鼓励与慰藉,成为他下一步行动的契机。这一番又一番的心理刻画时常是辗转磨矶的,却恰是董生的性格使然。即便在紧张的监视中,他听到李氏“东邻多病萧娘,西邻清瘦刘郎”的呻吟,便脱口而出“是元人小令”,“又是元人小令”,教书匠好掉书袋的酸溜劲儿袒露无遗。而李氏虽然不是外在行动的主导者,却是一个充满魅惑的生命体,不断赋予董生行动的力量源泉。李氏的生命状态表面静如止水,实则暗流涌动。俩人间没有隔空喊话,但有贯穿的心灵呼应。这一切都依赖于王仁杰从容不迫地设计人物的心理波动,通过细节对人物心理进行“纰露”,使之延宕浸润在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王仁杰剧作对人物行动的设计以及对舞台行动的铺排具有与众不同处,他不企求通过外部的强烈动作来设置戏剧情节,而是更多地考量人物心理动机,让人物的舞台动作自然地发生,让人物自然地行动。他的舞台行动往往是静谧与沉闷的,但往往与人物心理发展态势呈现高度的同步与共振。这也解释了王仁杰塑造的人物形象何以感人可信,我以为这感人可信的基础是人物情感与心理的细腻真实。中国戏曲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局中,呼唤艺术创造与呼唤艺术固守往往被认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王仁杰的创作实践却告诉我们,创造与固守不是绝对的,两者间彼此的滋养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单跃进:上海京剧院院长、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