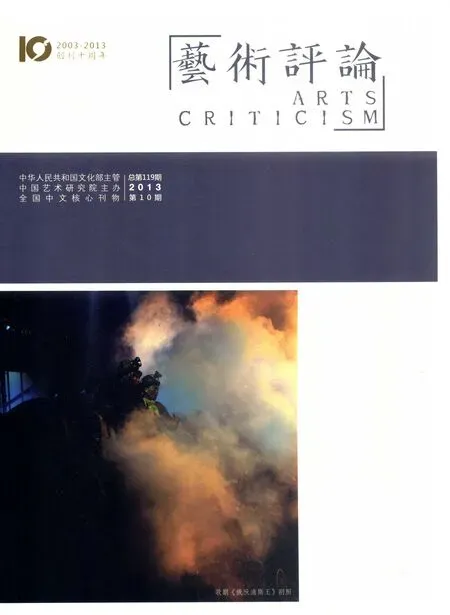“伟大作家”能“呼唤”吗?
阎 纲
“伟大作家”能“呼唤”吗?
阎 纲
有人问:“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是一个迫切的命题,怎么呼唤才好呢?
多年来,我们“呼唤”艺术大师和“伟大的作品”,说了不知多少偏离美学原则的话!我自己早在28年前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写过一篇文章:《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孙犁看后大不以为然,批评我说:“史诗是‘呼唤’出来的吗?”
吴冠中,标志性的艺术家,时代的骄子,民族的骄傲,人们纪念他,也是想借重他“呼唤伟大的作品”。
吴冠中与我毗邻而居,公园散步时亲口对我说,“文学就是借文字表现感情的内涵,我自己一辈子笔墨丹青,步入老年后,发现绘画造型毕竟是用眼睛看的,没有声音,情节出不来,恐为后人责骂,亲手烧毁了200多幅画,丹青负我啊!我本来不想学画画,一心想学鲁迅,这是我一生的心愿。固然,形象能够表现内涵,但文字表现得更生动。以文字抒难抒之情,是艺术的灵魂,更深刻、更有蕴藉,诗,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越到晚年,越觉得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是数千年千姿百态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孙后代肃然起敬的民族壮景。我还敢狂妄地说:‘100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则不然。他称鲁迅是精神上的父亲,自己要做一个有脊梁的中国文人,说:“我坚信,离世之后,我的散文读者要超过我绘画的赏者。”
一位愧怍“我负丹青”的画家,在文学面前却敢言“丹青负我”,他把精神看得比笔墨更高,其目的是艺术与诗意的完美结合。吴冠中所继承的,正是代表“忧愤深广”的“民族魂”以及中国新文化方向的鲁迅精神。
所以,吴冠中逝世后,中央领导同志参观画展时表彰他“高尚的人品风范,深邃的艺术思想,不懈的艺术追求,高远的艺术境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且说他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关键词是:人格!艺术!
现时文坛,人心浮躁,名缰利锁。一次,和作家韩小蕙交换看法,问何者是我目睹文坛之怪现状,我说,四句打油,恕我不恭:“作家要表现,领导要宣传,大众要好看,书商要赚钱。”消息传出,朋友们哈哈大笑,俱皆认同。孙犁早在1979年给我的《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写道:“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作品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昙花一现。”警惕艺术的商品化,为钱袋和评奖而写作注定与伟大无缘。

吴冠中作品:《山村图》
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环境里,空头文艺家泛滥、流氓文艺家很多,好的艺术当然出不来了。
文艺多元化,各人心里一杆秤,但多年来,我们偏离文学谈文学,偏离艺术论艺术,偏离恩格斯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发议论。恩格斯认为这两个“观点”的统一是评判文艺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又说:“……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坦率的。”
文学就是文学,艺术首先是艺术,是声容笑貌、喜怒哀乐,是情欲、世道人心,是美,作家必须具备美学资质。
可见,呼唤伟大的作品出世,是憧憬,是激励,是期待,是文学梦也是中国梦,好梦成真,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文坛是非多,是非之大莫过于对于“创作自由”和“自由度”的理解。党中央多次倡导“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发文件指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政策界限是明确的,只要我们在行业自身的实施中加以细化,具体操作起来才不至于遇到难障,优秀的、伟大的作品才能应时而生。
研讨会该开还得开,但求名心切,太滥,有钱就能开;能开就是精品力作,登发言、发消息,形容词高耸入云,要能拿个什么奖的,分田分地真忙,立马改换门庭。研讨会的学术质量亟待提高。文艺“除草”、“扫黄”在即,但什么是草是毒是黄祸、黄色描写,缺乏法理的依据,致使有的作品昨天禁、今天印,禁有说法,再印却什么也不说,只能被认为禁是对的,开禁也没有错。“以人为本”的文艺立法刻不容缓。
话又说回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恨铁不成钢,该“呼唤”还得“呼唤”,只要尊重艺术规律,不吹牛说大话就好。我常常引用恩格斯这样一段话:“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热情呼唤:“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今之中国,社会大转型,历史大变革,“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出大文豪、艺术巨擘的时候。中国文学,什么时候会给我们新的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呢?
需要榜样的力量,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美学的精微,需要精神的压力。试想,没有鲁迅的脊梁,能出孙犁、吴冠中吗?没有《保卫延安》的出世,《创业史》的诞生会不会推迟?没有《创业史》脱颖而出,能否带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青年作家“走出潼关”?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压力,《白鹿原》的笔者能破釜沉舟,自将磨励,以超越历史为己任?
阎 纲:文艺理论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