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之夭夭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张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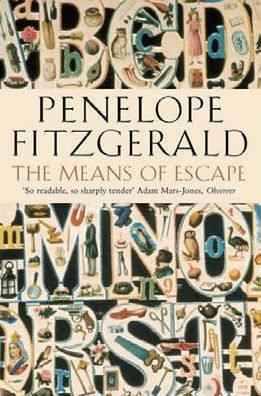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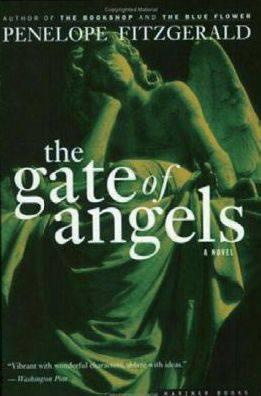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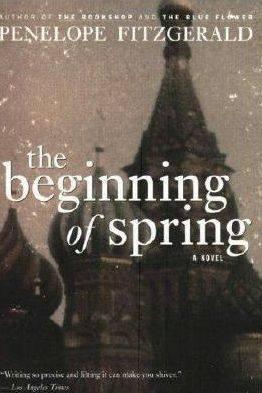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1916—2000)
英国女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20世纪60年代,曾和英国小说家A. S. 拜厄特共同执教于威斯敏斯特辅导学校,197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金孩》后,1979年《离岸》获布克奖,另有三部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蓝花》于1997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批评家协会奖,使她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非美国公民。
圣乔治教堂位于霍巴特② ,高耸于巴特里角区和港口间。教堂里面看起来很怪,很可能一直就那么怪;虽然那个时候教堂里并没有你现在能看到的蓝粉黄三色相间的玻璃——这玻璃是1875年才从一家德国公司订购的,但教堂石棺形的窗户却古来如此,想必建筑师当时想到了埃及,并认为埃及风格的窗户与教堂主题相配(据说圣乔治是一位埃及圣人)。这些石棺形的窗户给你一种怪异的印象,使你跨过教堂门槛时感觉像是走进一座古墓。
1852年,教堂面朝东,那时还没管风琴,伴奏乐是用一种叫塞若芬的乐器弹奏的。那架塞若芬是由艾勒德先生装上的,事实上,也是他发明的。艾勒德先生来自都柏林,现在是霍巴特的居民。虽然由艾勒德先生指挥的合唱团成员大部分是男人:总验船师、海军牧师、港务长和他的员工,但他仍打算组建一支天使合唱团。谁会弹塞若芬呢?刚开始只有艾勒德先生的女儿洛根女士会,她因此似乎能拿到20英镑的年薪,和教堂司事以及办事员的酬劳一样。因为塞若芬演奏时得连续不断地打气,所以当洛根女士觉得这活儿她干不了时,她教会了教区长的女儿爱丽斯·戈德利。
霍巴特地处“没有北方的南部”,位于白雪皑皑的威灵顿山和德文特河之间。德文特河一路顺势而下,穿过海岬汇入冰冷的港口。你要是在霍巴特,四面八方吹来的风都不会错过,霍巴特再往南就是南极流冰了。每次爱丽斯要练习圣歌伴奏,她都得先打开外面的泪柏③防风门,然后再打开里面的防风门,最后再使劲把这两道门关上。
那架塞若芬放在教堂一角一块方形羊毛织花地毯上。那是一个下午,圣乔治教堂外阳光灿烂(我是指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教堂内明暗交汇,让人感觉有东西要从暗处爬出来,很难判断不远处刷得漆黑的靠背长椅上会不会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从座位上立起来。爱丽斯爱读神秘故事,这会儿她想起了故事里的某个情节:一个人形的东西在阴影里前行。
如果爱丽斯仍是十年前那个女学生,碰到这种情况,肯定就尖叫起来了,但这次她没有。据说十年前到处都有从阿瑟港跑出来的逃犯,警察却没向公众提供那些逃犯的信息。现在,政府当局公告牌上也仅有大约20个逃犯的名字。
“我不知道这儿还有人,”她说,“教堂一直是锁着的。我是这儿弹琴的,也许我可以帮你?”
一股恶臭从教堂过道里向她袭来,这不像是想参观教堂的人身上发出的味道。那人的样子看起来怪怪的,也许是因为那人的头被麻袋罩着的缘故吧,像要被拉出去屠宰的牲口。麻袋上有两个窟窿眼,于是这人看上去又像将被绞死的死刑犯。
“好极了,”他说,“你可以帮我点忙。”
“现在我可帮不了你,”她边说边拾起乐谱盒,“不许再走近!”她毫不含糊地补充道。
他站着不动了,“我们应该对彼此多点了解,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你要愿意,可以考考我,拉丁文或希腊语都行。我从阿瑟港来。我给人下毒了。”
“我还真没料到你都结婚了。”
“我可没说我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他叫道。
“那你是无辜的了?”
“你们女人觉得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不,我有罪,但我被定错了罪。我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他们告我做假证。”
“我不懂什么叫‘一根指头都没动过?”她说,“你刚才还说你给人下毒了。”
“我那么说是想吓唬你,”他说,“但这不是我现在的目的了。”
她本来打算径直走出教堂,尽快把门锁上,绝不回头看他;她相信一个禀性坏的人正如一匹马,是容不得对他有丝毫同情或其他什么的。然而他,在那些靠背长椅中穿来穿去,似乎想要堵住她出教堂的路。
他告诉她,他现在用的“萨维奇”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他是从莫德尔监狱逃出来的,身上带着刀。开始他是想割了她的喉咙,但立刻就发现这位年轻女士脾气不坏。他是从砖砌的教堂塔楼(修好了一半,但现在没有工人在那儿干活了)缝里进来的。他还没找她要吃的,她就很果断地说她弄不到吃的。她父亲是在职教区长,这儿最慷慨的人,但在他的管区,每一样东西都得严格登记。每周二、周四傍晚有慈善布道,她也许能给他弄点喝过的茶叶,那东西总是留着的;如果他能弄点热水,可以把茶叶再捣碎。
“承蒙好意!”他说,“喝过的茶叶!”
“我现在只能做到这点,我有个朋友——过两天也许我能多帮帮你,可你最多只能待到明天。”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三,11月12号。”
“这么说‘不屈号还泊在港口。”
“你怎么知道的?”
监狱里的囚犯都知道。他们之间闭口不提但却心照不宣,航行单在识字的囚犯间秘密传阅,不识字的则默默记在心里。
“‘不屈号是运煤船改装的,能装货还能载150人,现泊在富兰克林港。我把我的秘密计划告诉你:我打算偷偷登船,随它一起抵达朴次茅斯,或者最近也得到开普敦。”
他穿着重罪犯的囚服,说到这,他把头上的罩子取了下来,拿在手里绞来绞去,好像正在洗它一样。
爱丽斯第一次正眼看他。
“夫人,我还得换一身衣服。”
“你可以叫我‘爱丽斯小姐,”她说。
一听到点儿声音,或者也许是假想的声音,他便躲起来,消失在黑暗中,顺着台阶躲回了塔楼。头上那个罩子蜷成一团落在了椅凳上。爱丽斯捡了起来,放进她的乐谱盒,把盒口的带子拉紧。
注释
① 本文选译自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 菲茨杰拉德的同名短篇小说集《逃之夭夭》(The Means of Escape )。该集2001 年由英国红鹳出版社(Flamingo)出版,共十个短篇;本文为该集第一篇。本译文的翻译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② 又译“ 荷巴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和港口,位于塔斯马尼亚岛东南部德温特河河口,塔斯曼海的海湾旁。1804 年作为罪犯的充军地建立,是澳大利亚仅次于悉尼的第二个古老城市。
③ 澳洲塔斯马尼亚产,其木材多用来造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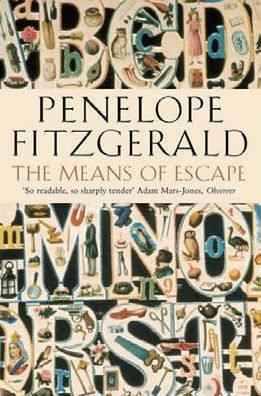
爱丽斯很幸运,她有个心心相印的朋友爱姬,全名爱姬·夏克伯格。爱姬的父母经营着夏克伯格旅店。
“你想过吗,他很可能就割了你的喉咙?”
“他这么想过,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爱丽斯说。
“有一点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爸,或警局的约翰逊局长?你不用马上回答我;因为若是马上回答我,你不一定告诉我实情。但你先告诉我,若是一个女人躲在教堂里,你会以相同的方式应对吗?”爱丽斯沉默了。爱姬接着说:“你们之间是不是突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是。”
那就没辙了,爱姬想。“恐怕他在那儿不好过,塔楼里没水,除非最后一拨工人留了一桶,并且那儿也没厕所。”但爱丽斯觉得他有可能会在夜里溜出去。“我要是他,我就会那么做。”爱丽斯接着解释说萨维奇是个聪明人,他计划偷偷登上“不屈号”离开此地。
“亲爱的,你不会想着跟他一起走吧?”
“我可没那么想过,”爱丽斯说道。
她们在旅店清点那些干净的亚麻布。那么多桌布、围裙、餐具、枕套,她俩说话时从不停下手中的活,她们知道自己对家庭应尽的义务。
夏克伯格旅馆有自己的仓库和商店,就在港口前。虽然弄不到港口进口过来的洋货,爱姬总能找到机会拿出点茶叶和熏肉,然后她俩再找机会送到教堂里去。
“爱丽斯,只要你不想跟他走!”
爱丽斯挽着她的胳膊:“45!”
她们决定在45岁时变得不可理喻地怪异。现在她们已经开始想象着那个情景了。这个教区,事实上,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俩已经有点怪了,因为她们还没有成家,尤其是爱姬,尽管旅店生意让她有很多这方面的机会。
“他把这个落下了,”爱丽斯边说边打开她的乐谱盒,盒里飘出一股恶臭味。她把麻袋似的头罩拉平整,罩子上狭长的窟窿眼犹如服丧的丑角所戴的。
“囚犯必须得戴这个吗?”
“我常听父亲说到这事儿。每次他们走出牢房门时都得戴着。这是新制度的一部分,是证明它们价值的有效方法。因为戴着头罩,没人能看明白另一个人长什么样,也不会知道别人的身份。并且,犯人之间也不许交谈,这样他们只能和自己的内心交流;也因此,只有上帝是他们的倾诉对象,这样他们就忍不住会回想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并悔过自新。当然了,在这事儿发生前,我可从未真正见过这东西。”
“它上面还有号码,”爱姬说,但并不想碰它,“我猜他们得自己洗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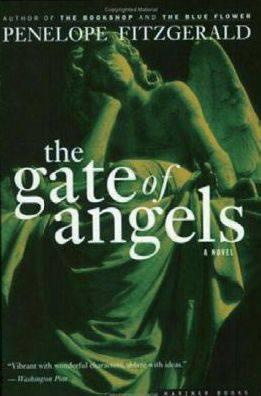
教区长家四点钟的晚餐桌旁已经坐着五个人了:爱丽斯的父亲、挨着她父亲的是一位客人——来访教士、紧挨着来访教士的是沃森夫人,然后是卢克夫妇。沃森夫人是这栋房子的管家,她是带着七年的刑期来范迪门斯地①的,现已获得离开此地的许可。发配来的仆人一般在后房用膳,但在教区长家,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份子。卢克夫妇是身无分文的移民(移民文件上说卢克先生是场景画师,遗憾的是霍巴特没有剧院),卢克先生和他妻子在这儿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
爱丽斯请大伙原谅,她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一上去,她就点亮一支蜡烛,把头罩上的虱子都捉着烧了。她戴上头罩。头罩并没弄乱她的头发。教区长女儿的头发整洁光亮,出得了任何场面。头罩上的眼洞太低了,爱丽斯戴上后啥也看不见,她站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问自己:“我怎么就犯了罪呢?”
爱丽斯的父亲从未大着嗓门说话,这时从楼下叫道:“女儿,我们都等着你呢。”爱丽斯取下头罩,叠好,放在她装羊毛袜的篮子里。
感恩祈祷后,他们吃了红鳍笛鲷、煮羊肉和面包布丁,没吃蔬菜。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戈德利教区长有一个不错的菜园子;但在这儿,在巴特里角区周围贫瘠的土地上,韭葱、卷心菜都长不好。
卢克先生说希望爱丽斯小姐下午练琴愉快。
“我没怎么练,”爱丽斯回答,“练琴时被打断了。”
“啊,演奏中途被打断挺让人难过的,这样专注力就没了。‘当灯碎了②……”
“我倒没觉得,”爱丽斯说。
“您太谦虚了,不愿意承认。”
“爸爸,我一直在想,”爱丽斯接着说,“既然卢克先生那么喜欢音乐,让他来弹弹塞若芬应该是件好事。这样,万一我要离开这儿,也能有个接替我的人。”
“您这么说就好像我们夫妻俩要永远待在这儿了,”卢克先生叫道。
没人对此做出回应——卢克夫人不会,她的日子过得稀里糊涂,让人唏嘘。她怎么会坐在离克莱肯威尔12000英里远的地方吃着面包布丁,并在此度过余生呢?教区长的注意力此时被来访教士给吸引了过去,教士拿着一份《霍巴特每日快报》大声念着其中的一段,是关于他从墨尔本抵达此地的报道。“热烈欢迎您的到来,”教区长大声说,“很高兴《快报》关注此事。”“哦,他们大可不必,”来访教士说,“但我无论去哪,都会登门拜访一下当地主要报社,聊上几句混个脸熟。那样,要是编辑没什么重要的内容登——情况往往如此,他就会把我的事写上一两句。”他来此地是要祈祷范迪门斯永远别发现金子,内陆地区已经发现,给人们带去了新的诱惑。
盘子都撤走后,爱丽斯说她得再去爱姬那儿,当然,一定会在天黑前回家。卢克夫人半闭着眼坐着,卢克先生走到后厨,问洗碗池旁的沃森夫人要不要帮忙抽点水上来,这样好歹他还有点用。
“不用,”沃森夫人说。
卢克先生硬要把谈话继续下去,“我相信你有相当多的生活经历。我发现爱丽斯小姐人不错,但似乎不太好让人理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她?”
“不能。”
注释
① 塔斯马尼亚的旧称。
②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1822 年创作的一首诗歌,诗的第一节如下:“当灯碎了,它的光亮灭于灰尘;当天空的云散了,彩虹不再灿烂辉煌;当琵琶弦断,美妙的音乐不再回响;当嘴把话说完,爱语即刻被遗忘。”
③ 始于17 世纪的英国传统木偶戏,主要角色为驼背丑角庞奇及其妻子朱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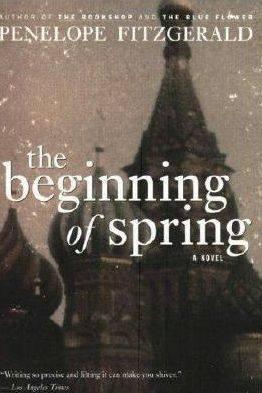
沃森夫人这辈子挺不幸的,即便在她情绪最好的时候,也是少言寡语。被送到这儿前,她失去了三个孩子,现在她也记不得这三个孩子的名字了。爱丽斯不信,因为她碰到的其他女人都认为叫出死去孩子的名字不吉利。沃森夫人的第三个孩子非常不幸。邻居十岁的小姑娘照看它,沃森夫人每周付她四便士。那天房子怎么着火的谁也不知道。突然起的大火。沃森夫人当时在别处干活,和她生活的那个男人倒是在家,但那时他已醉得不成样子,并且他也做了——在沃森夫人想来——在当时紧急状况下他能做的:把小姑娘和婴儿从窗户那儿扔了出去。验尸官说不妨看作一出《庞奇和朱迪》木偶戏③。爱丽斯劝沃森夫人,“尽量别再想这事。”不巧的是,一个星期后,沃森夫人因偷窃被拘。她想投河,偏偏带子又把她给绊住了。
抵达霍巴特后,她被送到女子劳教所,一年后,因表现稳定,被分到雇佣培训部,在那儿雇主可以挑一个有用工证明的人,沃森夫人就是这样在几年前来到教区长家的。爱丽斯教她读写并且送给她一本《圣经》——这是要求雇主一定要做的。爱丽斯在书上印了一个吻;衬页上,她抄下了《何西阿②书》上的一句:“告诉你的姊妹,她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
沃森夫人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自己的年龄,她苍白的脸上也没有因岁月的虐待和不公留下过多皱纹;很显然,只是时间或机遇给了她随意一击,又或许她一直看起来就那样。虽然那时候,她没有说感谢的话,但很明显几个月后,她就把自己未能倾注出的爱全给了爱丽斯:她常会抓住爱丽斯的手握上一会儿,也会无意识中奇怪地模仿爱丽斯——模仿她快步走,模仿她打理家务的方式,这些都清楚地表达出了沃森夫人对爱丽斯的爱。心中有爱而无处倾注,这是女人最大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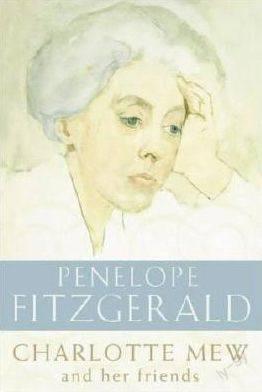
爱姬弄到了茶叶、熏肉、李子酱,她还主动加了一卷雪茄。只有雪茄是从店里弄的,也许不应该带过去,但两个女孩从未见或听说过男人有机会抽烟而不抽,有机会嚼雪茄而不嚼的。并且她们还知道在诺福克岛和阿瑟港,常有犯人为了雪茄而杀人。
她们记下了所拿的这些东西的现金价。爱丽斯过后会把这笔钱付给夏克伯格旅店,她会从上音乐课挣的钱里掏。(在圣乔治教堂弹奏塞若芬的工钱,她一直都没要。)但是要讲实话的要求怎么办?要诚实的要求怎么办?嗯,爱丽斯会等上120天,等“不屈号”抵达朴次茅斯再说。那个时候,她会向她爸老实交代。
“你跟他说什么呢?”爱姬问。
“我会告诉他我偷东西了,我撒谎了;并且也让我的朋友偷东西、撒谎了。”
“不错,但你这样做是出于怜悯啊,你可怜这个男的,这个囚犯,孤零零地在这个宽广的世界。”
“我不敢肯定我这么做是出于怜悯。”
去教堂的路上,肯定有人从刚修葺的房子的明亮前窗看到她俩了。她俩的小推车也有人看见了,只是人们以为小推车是和教区杂志或某种打算预订的杂志有关;因此,即便有人从窗户里看到了这些,他们也很快就从窗边走开了。爱姬很想看看爱丽斯的囚犯,但走到小山顶部时,她说:“我就不跟你一起进去了。”
“可你帮了这么多忙,你一定是想看看他长什么样的。”
“我确实想看看他长什么样,但是我要控制住自己,一个人的性格就是这么形成的,有些时候,你得控制住自己。”
“爱姬,你的性格已经形成了。”
“天,爱丽斯,你真想让我跟你一起进去吗?”
“不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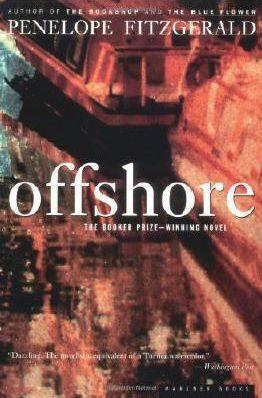
“萨维奇先生,”爱丽斯果断地喊道。
“我就在你身后。”
爱丽斯没有转身,她把用白色包装纸裹得紧的东西一一拿出。他没有接那些东西,雪茄也没接,却说道:“我一直从塔楼看着你和另外那个年轻女士。”
“你不能一直这样,”爱丽斯说,“这教堂每周五都有祈祷会。”
“我明晚就打算跑掉的,”萨维奇说,“但我需要一套女人穿的衣服。我块头不大。无论从哪方面看,我在阿瑟港都瘦了。你能帮我弄套衣服吗?”
“我没法把一套女人穿的衣服拿到教堂来,”爱丽斯说,“圣保罗禁止这么做。”虽然她常常觉得自己对圣保罗已经受够了。
“如果他不让你到我这儿来,那我可以到你那儿去。”萨维奇说。
“你是说到我爸的房子那儿去?”
“爱丽斯小姐,告诉我怎么走,你的房间在哪儿。待时机合适,我会在你的窗户上敲两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