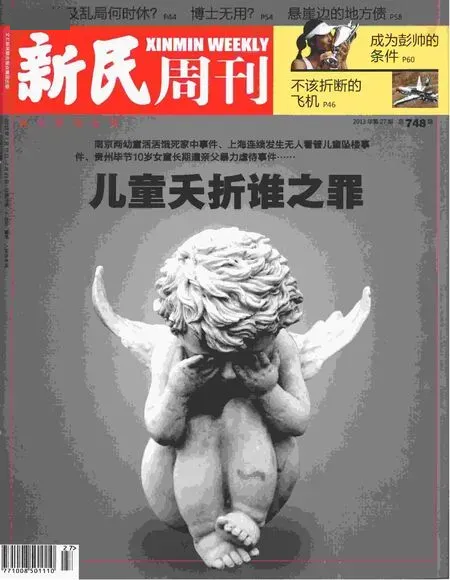铁轨上
崔骥
无名的铁轨,不知将要抵达何方,即便抵达了那个想要的尽头,还是要有一段日子慢慢度过,还会遭遇不幸,或许还会有新的旅程,未来还可能被它送回到原地,送回来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还有随身携带的梦想、悲伤与收获。
19世纪德国诗人海涅说过,空间被火车杀死了。而那枚彪炳的利器就是铁轨。
实际上,世上第一部电影、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逼真地呈现了一个钢铁巨物沿着两排铁轨,汹涌前行的气势。有的观众惊慌失措,四散而逃。
俄国作家高尔基观后感叹:“这也只不过是一列幻影罢了。”
台湾导演杨德昌处女作《浮萍》中,一个年轻的、对社会抱有美好幻想的女孩,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她乘坐的是火车,电影画面中一片空蒙的铁轨,孤独地躺在野外,犹如即将生活在大城市的女孩,那不可名状的形态,也隐藏着更多的陷阱。因为它通向一个未知的异乡。
无名的铁轨,不知将要抵达何方,即便抵达了那个想要的尽头,还是要有一段日子慢慢度过,还会遭遇不幸,或许还会有新的旅程,未来还可能被它送回到原地,送回来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还有随身携带的梦想、悲伤与收获。
《黑暗中的舞者》的塞尔玛,一名贫寒的捷克移民,她有先天性眼疾,这个病症也遗传给了她的儿子,她要赶在失明之前,加班多赚钱,以期给儿子积攒足够多的医药费。但她眼疾尚未恶化时,她还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而当看不见路时,她选择顺着铁轨走回家,长长的铁轨成了塞尔玛内心的归宿。火车隆隆开过时,幻化成了音乐节奏,如同一曲挽歌。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丑陋世界,她不见了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通透的现在与未来。
韩国导演李沧东的《薄荷糖》里,也有一段段铁轨,看似寂寥、荒凉,其实布满了生活的斑斑痕迹,那是主人公命运的写照。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里那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两三点人影拾阶而上,伸向远方的斑驳铁轨,少男少女踯躅慢行,像是一首哀而不伤的民谣。
铁轨就是那个直指未来的线性时间。《盗梦空间》里柯布进入了多重梦境,开篇是一次失败的盗梦旅行,而在现实世界,他在日本新干线上,计划在下一站京都站下车。第一层梦境里,大雨倾盆,柯布团队遭到一列突然冲上街道的火车的袭击,这是他潜意识中的已故妻子——罗伯特·费雪的干扰。火车是她的投影。这列冲上街道的火车与现实中平稳运行的火车构成一组对比,那是一个时空对另一个时空的扭转。
《盗梦空间》中“脱轨”的梦侵扰了“正轨”的人生。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安娜与沃伦斯基初次在火车站相遇,当时一个人被火车压死了。这一幕预示了后来安娜的卧轨事件,她的卧轨更是整本小说与所有改编的影视版本中,最决绝震撼的一幕。她醒悟了她在爱情中的处境,“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接紧挨着开过来火车的地方,停了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契诃夫评论道。
《观音山》中放纵青春的青年,也是躺在铁轨上,不同的是他们在最后一刻起身了,火车擦肩而过。回到了生命的正轨。
我也喜欢听火车的声音,但我年少的家距离铁路很远,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听到火车声音时的欢快与兴奋。那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因为火车经过我家附近时通常不会鸣笛——但有那么几次,火车鸣笛了,还恰逢整个空间处于最寂静的时刻,比如一场暴风雪或雷阵雨过后,那天外之音,虽然是来自几公里的地方,却俨然也像另一个国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