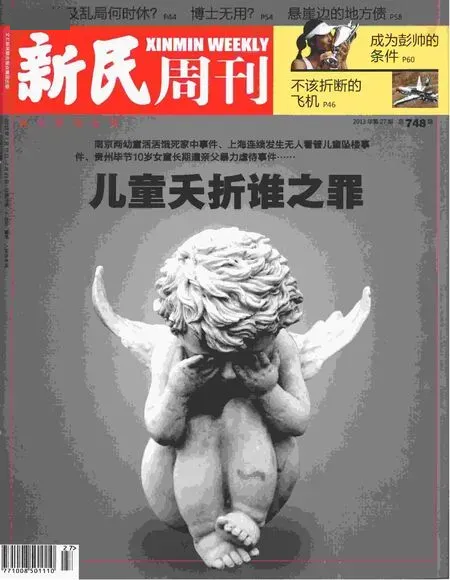中国特殊吗?
顾文豪
在《高尔吉亚篇》里,苏格拉底驳斥现实主义者:“你在人群中宣扬伯里克利这些人的善行,宣扬他们为同胞服务,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但却不告诉同胞什么是善和诚实。雅典人谈他们使国家强大,但雅典人不知道这一强大不过是一种夸张,一块充满腐败的肿瘤。”
“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但却不告诉同胞什么是善和诚实”,若是苏格拉底活转来,我料想他将为遍地皆是这等“现实主义者”而瞠目结舌,同时他将惊讶地发现,今日的知识分子不仅试图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甚至更乐意满足欲望中尤为粗鄙的那部分。如果说,过往的时代,被定义为世界牧师的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职责是,反对时代精神的被侵袭,由此民众需要他们。如今知识分子更多扮演的是媒体明星和段子批发商,妄想成为眼球中心的他们其实更渴望民众,准确点说,是渴望听众。而一旦言论沦为表演和牟利的工具,也就谈不上言论的品质了,一如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慨叹的那样,“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而恰恰因为这样的时代困局,我尤为歆服刘擎老师的议论。在我有过交往的知识人里,刘擎无疑始终葆有对超验真理的信仰。每次听他声如洪钟般的谈学论理,都不自觉地在我面前展开一幅知识的图景。这位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大政治学教授,似乎从未让自己拘囿在任何太过形而下的琐细问题中,相反总能在最幽微曲折的凡俗问题里洞见时代的褶皱,并以他一贯的高亢、快速、华丽乃至激情的表达将这份褶皱撸平给我们看。
在新著《中国有多特殊》里,此前多年的政治哲学的学术训练赋予了刘擎发言论议的整体视野,他关心的是正当“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汇入了正在浮现的新的地平线”的历史时刻,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又有多特殊?而当中国式的特殊遭遇世界,中国又该如何自处?
秉持这样的视角,他提醒我们关于一个全面西化的中国的所谓的种种“中国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却完全忽视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而一如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异化劳动”的富士康事件,刘擎直指事件背后的“反科学”发展观,诘问“中国奇迹”究竟埋藏着多少可耻的秘密;至于火爆一时的“虎妈教育”,在那些卫道者正为中国式应试教育沾沾自喜之际,刘擎冷言,虎妈的战歌是唱给美国人听的,“而在应试教育已经处于暴政地位的中国,若要套用虎妈妈的秘诀药方,可能无异于自服‘毒药”。
但我们似乎也不必将此书理解为一份关于“中国特殊性”的对照记,事实上,这是一本“自我书”。就大者言,刘擎追问的是长久困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和世界是怎样的关系,中国崛起是否能够建立一套“中国范式”;就小者言,刘擎在探寻一种知识分子如何经由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进而介入时代的方式,在今天深水激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不仅是一种对话和互动,我以为更多是在找寻知识人合适的时代位置,容我唐突,从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在究问“知识分子有多特殊”。
这让我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歌德在《诗与真》里写:“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我们既不关心报纸,也无意传播消息,我们的工作就是认识人。”以我和刘擎老师的有限交往,他兼具演说家的煽动力与学者条分缕析之功,我每每循着他回环绵密的话语去“认识人”。实话说,我所见的学者多有学问而少洞见,而刘擎仿若一台思想的永动机。在他这里,思想不是一个浮夸虚空的名词,而是扎实牢靠充满力量的动词,一如他发言时稍稍涨红的脸、有力的手势。我其实不很关心他思考了哪些现实问题,他吸引我的永远是他切入的角度与那或许承袭于早年写诗所形成的独特语言,这才是刘擎特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