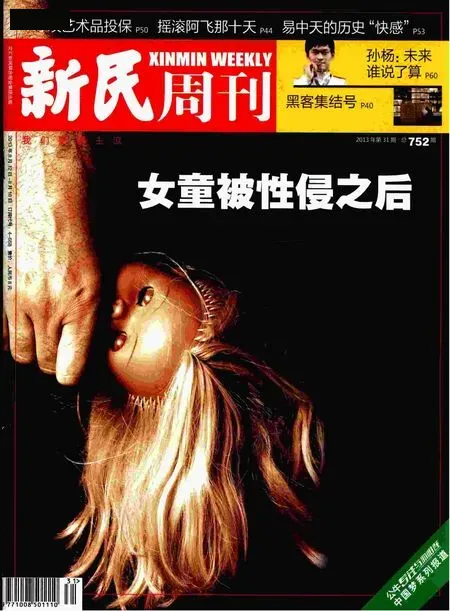大家一起吃
苗炜
我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课本上有一篇童话,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篇课文的开头,然后叫我起来接着往下念,我拿起课本,皱着眉头,确认课本上没有我不认识的字,慢吞吞地念着:“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我停下来,不念了,老师说,继续念啊。我还是不出声,老师让我坐下,换一个同学念课文,我还是站着,心里默念课文,桌子、台布、盘子、碗、苹果、梅子,最重要的是烧鹅,还有刀叉,在我周围飞舞。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西餐,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是西餐,有桌布才是西餐,用刀子和叉子吃饭才是西餐。
一张铺好桌布的餐桌,上面全是好吃的食物,有卡慕干邑,有烤乳猪,小猪“眼睛紧闭着,睫毛还清晰可见”。波黑作家戈兰萨马尔季奇接着描述,“最丰盛的食物,最昂贵的东西,都放在我面前,恨不得每分每秒都在给我上新的菜。我解开衬衫的扣子,松了松百慕大短裤,让胃可以松快些。我的下颚和进化尖利的犬齿,不停地、单调地咀嚼着。它们甚至嚼碎了肉骨头。在我那两排用牙线清理干净的齿间,所有的东西都被俘虏了,粉碎了,击破了,就好像在咀嚼的时候,我再次杀死了那头猪。”这是小说《凡尼水》中的一段描述,显然,主人公处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境地。如今我读小说,还会注意那些描写到食物的场景,但很少会流口水了,大多数食物我们已经吃过见过了。即便我没吃过,也见过别人吃过,见过朋友吃过,食物的照片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简直把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餐桌。Instagram统计,上一年的感恩节,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午饭时间,每秒钟有200万张照片发布,其中有100万张照片都是食物。我们这里没有相关数据,但我相信,我们食物的照片更多,分享的热情更高。
如今我们有机会看到各种描述食物记述吃饭的文章,不管吃得好还是吃得超凡脱俗,都有那么点儿“自我陶醉”的意思。“菜单写在羊皮纸卷轴上,有前言,有两个章节,有尾声,这不是瓦格纳的歌剧或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是我的一顿晚餐。”《哲学杂志》的编辑到斯德哥尔摩一家米其林餐厅去吃饭,他打算写一篇“食物与哲学”的文章,因此将要度过“生命中最奢侈的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中,他将品尝十九道菜,一顿晚餐的价钱是350欧元,他说,世界上还有十亿人饿着肚子,我却要吃这么贵的一顿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道德上的挑战。看得出来,这位哲学编辑也不富裕,人均三千元的一顿饭在中国并不罕见,可在欧洲,却是非常贵的餐厅了。
餐厅主厨接受了哲学编辑的采访,他说他喜欢吃香肠,还喜欢吃麦当劳,他说,到这里来就餐要放松一些,我们饿了就要来吃饭,就这么简单。餐厅的布置、菜品的讲究、上菜的时机、餐具的选择,都很不简单,哲学编辑吃下贝类、肉汤、青菜。他说,到这样的餐厅来吃饭,肯定不是饿了要吃饱这么简单。吃这顿饭是罕见的生命体验,当然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体验而已。艺术总让我们忘却我们平凡的肉身,忽然间有了些神圣感,忽然间有了神性,但烹饪这种艺术,总是让我们想到,我们就是凡夫俗子,烹饪是内在的审美,而不是超验的。
我觉得这位哲学编辑的文章很有意思,虽然我看不太懂他要说什么。我知道,吃得太好会有罪恶感,吃饭也不像做礼拜那样能升华自己,很可能还会因为发现自己的动物属性而自惭形秽,但我觉得,吃到好吃的,分享照片是美德,这位老兄面临的道德挑战是,你该不该拍下那些菜,让我们这些没机会去斯德哥尔摩品尝那家餐厅的人也先有机会看看,那里的菜到底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