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扎尔辞典》:一本奇书的传说
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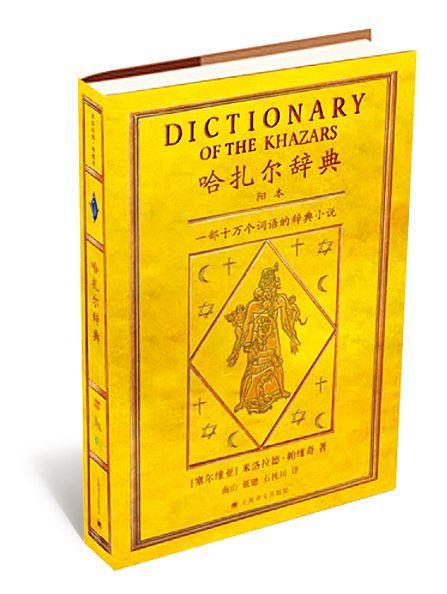
在文学史上,1984年是个被预告过的年份。奥威尔式的梦魇固然未能成真,恐惧却挥之不去。1984年之于文学史还有另外的意义,“21世纪的第一部小说”在这一年诞生。
从世界到中国
《哈扎尔辞典》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学者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处女作,假托1691年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以百科全书的体例,叙述哈扎尔人的历史和传说。小说于1984年以塞语出版,赢得本国评论界嘉许,第一篇书评出自诗人拉沙·利维达之手,他盛赞这部未来之书:“惊奇之处在于,它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集、历史专著,加上神秘主义的手册,同时集于一身,总而言之,这是十足的文学。”
该书的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均在1988年出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巴黎竞赛》画报称之为“21世纪的第一本小说”,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观察家报》撰文,冠之以“魔物”和“致命武器”的头衔。而罗伯特·库弗在《纽约时报书评》所刊文章的标题是《他用我们做梦的方式思考》。
在中国,《哈扎尔辞典》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人所知。1996年底,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刊文,指控韩少功的小说新作《马桥词典》“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另一位评论家王干也在该报上说:“《马桥词典》模仿一位外国作家,虽然惟妙惟肖,但终归不入流品。”不甘受辱的韩少功最终选择起诉张王二人和相关媒体。“马桥事件”成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大陆最为轰动的文坛公案之一。
然而笔仗打得不开可交之时,《哈扎尔辞典》其实仍未在中国完整亮相,仅在1994年第二期的《外国文艺》杂志上发表过节译。1998年12月,南山、戴骢、石枕川三人合译的全书,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读者将它拿来与《马桥词典》对照,便发现两本书其实完全没有可比性。
官司打了两年多,直到1999年3月,法院才做出终审判决,裁定韩少功胜诉。此前史铁生、汪曾祺、李锐、迟子建和余华等人曾公开呼吁,由作协机构聘请专家组成《马桥词典》评审委员会,就韩少功是否“抄袭”“剽窃”“完全照搬”做出鉴定,似乎更为合理,也能为日后的类似公案立下范例。
“右眼当叉,左眼当刀,去他的”
《哈扎尔辞典》讲述的是哈扎尔人的故事。在历史上,哈扎尔人确有其族,操突厥语,公元2世纪时来历不明地出现,游牧于里海和黑海之间,6世纪建立起强盛的商业帝国,10世纪忽然衰落,继而神秘消失,一如当年神秘地出现。
小说融合了历史、哲学和神学,但从故事到结构,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中心事件即所谓的哈扎尔大论辩:可汗请来三位哲人释梦,并承诺,哪位哲人在辩论中获胜,他便带领臣民皈依该哲人所属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或犹太教。关于论辩的过程和结果众说纷纭,三大宗教都认为本方获得了胜利。17世纪的后人收集了已存的所有史料,编成一部百科全书。
帕维奇在卷首语中煞有介事地宣布:“本书现在的作者保证读者诸君读罢本书后绝不会招来杀身之祸,而此种不幸命运曾于1691年《哈扎尔辞典》初版面世后,降临在当时的读者身上。”
《哈扎尔辞典》分为三部分:基督徒的红书,穆斯林的绿书和犹太人的黄书,各列词条,各做解读,并以代表三种宗教的十字架、新月或大卫星符号建立起联系,互相证实或证伪。根据叙述者视角、时间、信仰或身份的不同,叙述往往也是不同且不可靠的,甚至经常相互冲突。借助这种形式,帕维奇打乱了传统叙事的时序,以俄国套娃般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创造出了一种迷宫式的布局,穿插着罗生门式的讲述。凡此种种,注定了《哈扎尔辞典》必将成为一部少有争议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
他的第二部小说《茶绘风景》(1988)犹如填字游戏,横章与竖章交替,横章按年代叙述,竖章则旁敲侧击。横读还是竖看,读者可任选其一。另一部《风的内侧》(1991)是对希腊神话中海洛和利安德故事的重述,而《君士坦丁堡最后的爱》(1994)则犹如一副塔罗牌,读者可以将书中21章自行打乱重组。
经由上述作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哈扎尔辞典》,帕维奇一跃成为后现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常被人拿来与博尔赫斯、艾柯、卡尔维诺和科塔萨尔等人相提并论。
无中心,不确定,零散化,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最明显的特征。它们往往是开放的、扩散的和相互脱节的,以此反对任何确定性、系统性和集体性的认知。在开始阅读时,读者也许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最好的办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当你不知不觉参与到情节的构建和因果的结合,快感逼退了不适,喜乐的时刻也就来到了。
最不济的话,我们也可以采用《哈扎尔辞典》中写到的吃读法:“像饕餮之徒那样狼吞虎咽:把右眼当叉,左眼当刀,把骨头抛到身背后——去他的!”

捕梦者
很难在中国找到帕维奇这样博学的小说家,更难的是在中国的小说家中发现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
1929年10月15日,米洛拉德·帕维奇生于贝尔格莱德,2009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80岁。
帕维奇的母语是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但从小就通晓法语和德语,非常年轻的时候又学会了俄语和英语。他先后入读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萨格勒布大学,亦曾在巴黎大学和维也纳大学访学,并在国内的诺维萨德大学和贝尔格莱德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和雷根斯堡大学任教,专治哲学和文学史,出版有《塞尔维亚巴洛克文学史》《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的塞尔维亚文学史》,以及《现代塞尔维亚文学的诞生》等专著,另外出版了26本诗集、剧本、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翻译过普希金和拜伦的作品。
帕维奇是博尔赫斯的信徒,迷宫、梦境和图书馆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最爱。正像他自己笔下的职业捕梦人那样:“捕梦者能释读别人的梦,能在梦里日行千里选择住所,能在梦里捕获指定的猎物——人和物或者野兽。”
关于《哈扎尔辞典》,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该书历来分阴阳两版(或男版与女版)印行,不过差异极其微小,不同之处其实只有一段,或所谓神秘的17行。知道秘密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公开泄密,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剧透地剥夺了更多新读者的参与之乐和发现之趣。这一切都使得《哈扎尔辞典》愈发成为传奇。
博尔赫斯说过:“在人类浩繁的工具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书,其余的皆是人类身体的延伸,诸如显微镜、望远镜是视力的延伸;电话则是语言的延伸;犁耙和刀剑则是手臂的延长。而书则完全不同,它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整整30年前,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的后记里写道:“今天的人也不具足够的孤独去阅读书籍和辞典了。”想想那个时候,真可以称得上史前时代,人类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网络。如果人的孤独在那时便已不够,那么今天,被鼎沸的喧嚣淹没的我们,又该怎样为阅读找到逃生的出口?
《哈扎尔辞典》已有大约70种译本问世。帕维奇去世后,其作品的出版和再版出现了一个小高峰,两年内便有大约20种新译本在世界各地上市。《哈扎尔辞典》的中译本再版在即。不过,在帕维奇的众多作品中,这仍是身处中文世界的我们拥有的唯一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