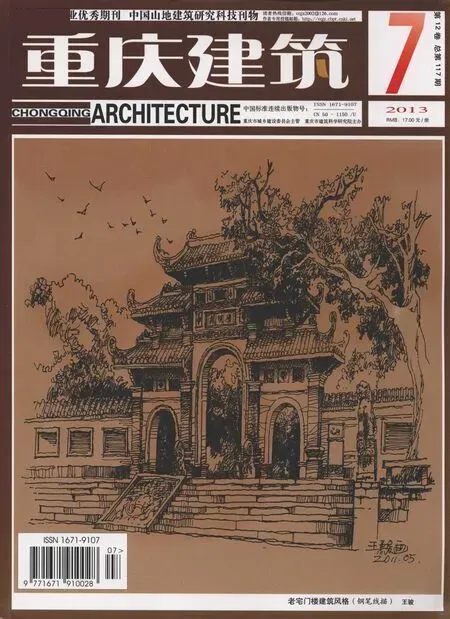世界眼光 哲学头脑 中国心——学习吴冠中先生的艺术哲学
顾孟潮
吴冠中先生(1919年7月5日-2010年6月25日)是当代罕见的德才艺绝佳的大家,值得为他编撰画语录供人们学习借鉴。吴冠中先生也是我十分尊重和喜欢的当代艺术大师,读他的画作与文章有一种鲜有的眼亮心明、酣畅淋漓、促人行动的感受。
但是,鉴于吴先生画作和文章之多让人目不暇接,我一直想找一本供建筑界人士学习借鉴吴先生艺术哲学思想的书而不可得。
近日,好友德侬教授赠我《看日出——吴冠中66封信中的世界》。初翻阅这本巨作时我还有些疑惑:如此厚厚的450多页洋洋洒洒58万字、514幅图的大书,让我担心,书桌上积压着好几本待读的书,何时能读完此书?而当我拿起来时就放不下了,一口气全部读完之后,觉得“看日出”基本上满足了我上述愿望。应当说,读此书真是极大的艺术享受。特别是,读吴冠中先生的画论颇有读《罗丹艺术论》的感觉。“看日出”出色地整理了吴冠中先生留给建筑艺术界的丰厚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熟读精思、珍藏实践。
从何读起呢?
书中提到吴先生论绘画时多次提示:“统帅是大色块、主调和结构,其他都是小兵”。我想作画如此读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于是,我从66封信切入开始读起。为了研读的方便,我还专门制成吴冠中先生致邹德侬等人66封信索引。结果一读就放不下了,连续三天夜以继日地读完全书。深深感觉到:这66封信恰恰是书的灵魂,是书的“大色块、主调和结构”。信如其人,信如其心,信是该书的魂!
吴冠中论建筑艺术
吴先生70多年前自中外艺术院校毕业后,曾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多年,因此他对建筑艺术、建筑教学、建筑师的了解洞若观火。邹德侬又是吴先生中年变法后的高足,曾亲聆吴先生言传身教,听德侬解读吴先生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画作,有声情并茂、体会入微之感。
吴先生关于建筑教育与建筑师实践的许多评论切中要害,如:
1、建筑系不缺画建筑图的人,缺的是艺术家!
2、建筑系的学生总是追求技法,虽然技法基本掌握了,可是画面总是不耐看,没有感染力。你要问问自己,艺术在那里?不是技法,是艺术,技术为艺术服务。
3、写生不是到此一游的游记,而是要去发现美,要把美抓出来,放大,重新安排,让没有发现美的人感受到,这就是创作,写生就是创作!
4、从技巧讲……你及你的同窗看到,也许会赞扬其渲染效果,但你立刻会悟到:你以前一味追求的道路的终点原来就在这里——无聊的坟墓。
5、实用、经济、美观,美观是形式问题,排行老三,在我们今天贫穷的条件下,我赞同这样的提法。形式之所以只能被内容决定,因为它被认为是次要的,是装点装点而已,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首先要办完年货,有余钱再买年画。
6、构图不是孤立的,构图就是构思,是艺术思想的物化。
7、有效果就是技法,技法为创作服务,在创作中形成技法,不是练好技法再上阵。
吴冠中的艺术哲学
吴先生把哲学真理视为“种子”。
他说:“真理好比种子,种子是坚实的,一遇水土便可生长。唐代的莲子,就曾在京郊的植物园再度开花,小小莲子,越世近千年,心脏不坏。”这大概是他特别重视艺术哲学探索的思想根源,他是从年轻时便重视艺术理论学习的。
当回忆到自身成长过程时,吴先生满怀深情地说:“朱光潜先生早年写的《文艺心理学》是我艺术思想成长过程中第一个奶妈,我学艺的童年是吃他的奶长大的,对他永远崇敬,愿他尽量长寿!”
认真学习《文艺心理学》等中外艺术前辈理论著作,和勤奋的艺术实践使他能有艺术哲学的高起点,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美术界提出“形式美”、“抽象美”的问题,对中国绘画的现代化和油画民族化做出极大的贡献。
“形式美”、“抽象美”的问题,同样也是长期困扰建筑师的老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一直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也未理出头绪。
吴冠中的艺术哲学思想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建筑师朋友学习、领会:
1、艺术的灵魂是美。
他强调,要“美”不要“漂亮”。艺术没有职业,没有价值。美是本质的,漂亮是表面的;美是永恒的,漂亮是暂时的。如果有人夸我的画“漂亮”,我就很不开心!老乡说我的画“很美”,我就十分高兴。漂亮不等于美,好料子,宝石、玳瑁这都是漂亮的东西,但不一定就美。应该抓住美的本质,这时候,石头和泥巴都可以是美的。
2、中国的“美盲”多于“文盲”。
这是中国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和背景,也正是开创中国绘画的现代化和油画民族化之路十分艰难的根源。
3、思想比技巧更重要,思想领先,题材、内容、境界全新,笔墨等于零。
他笃信德拉克罗瓦的绘画经验:用扫帚落笔,用绣花针收拾,这样可以做到“大笔不失空洞,小笔不至于琐碎”。后来他把此上升为“色块、主调与结构”理论,他强调“统帅是大色块、主调和结构、其他都是小兵”。仔细想想,这不正是“图底理论”的吴氏说法吗?大色块、主调和结构是绘画的“底”,其他都是“图”是“小兵”。而现在许多人做画或做事常犯的大忌,便是忙于作“图”,忘了“底”这个帅。
4、创新的思路与路径。
从66封信的索引也可以看出吴先生思路与路径的一点眉目。
如:第2封信:形象、形式是画家的生命线,不愧见洋鬼子,试作水墨;第23封信:去日本之画已在东京展出;第26封信:形式美问题被提到空前高度;第34封信:谈及抽象美问题;第43封信:组织批我的“抽象美”;第50封信:“一见钟情”在形式美中的永恒价值;第55封信:开始反刍动物新草;第63封信:香港“吴冠中回顾展”20天,作品的力量将征服一切;第66封信:回顾展振撼香港艺术界。吴先生的创新思路和路径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而且也经历了“出口转内销”的过程,先要得到境外人的认可,然后才在国内逐渐热起来。
记得1978年5月出版的 《罗丹艺术论》,开篇的 “出版说明”,就为罗丹扣上“唯心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不可知论”等几顶大帽子。而且还感到力度不够,在这本154页的小书最后又加了20多页的“后记”,深入地批判所谓罗丹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书中的“糟粕部分”,甚至,把罗丹和胡风联系起来,说是在散布“反动文艺理论”云云。

山城(国画) 吴冠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理解在艺术观念、思想、艺术手法上与罗丹“英雄所见略同”的吴冠中先生,此刻提出抽象美、形式美的学术勇气和艰难处境,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必然性。况且罗丹的许多观点在吴冠中先生这里得到深化和发展呢?
吴冠中先生认为,要正确对待东西方——东方与西方只是从不同的方向攀登艺术高峰,路径不同,方向一致,殊途同归。
现代化与民族化——只是一体的两面,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所谓两个观众——指西方的艺术大师和中国的老百姓是吴先生的服务对象。
意境——乃是吴先生每一次创作的艺术追求。
吴冠中先生说:民族化的核心,我觉得主要还是意境问题。我没有对数十年来的摸索作过理论分析和总结,但回忆一下,粗粗地归纳,我似乎不断在追求四个方面:人民的感情、泥土的气息、传统的特色和现代西方绘画的形式法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有意境。形式呢,吸收西方现代手法必须将之化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身家性命画图中
吴冠中先生视艺术为生命,为艺术创新献出了他的一切,其精神是我们的榜样。学生问他创作的“成功率”时,他回答说:
我作画的“成功率”大约也就是10或20分之一吧。失败当然比成功多得多,不过,我是“宁可玉碎”。和你们一起画画我也怕,因为我总是搞可能失败的东西,我已经掌握的东西,就不愿再重复,重复不会有什么新的提高。要搞自己没有把握的东西,就有可能失败;我宁可失败,也不愿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
关于成功笔者想到一句话:“别关注正确,关注成功”,这句话难道错了吗?
我觉得不怕失败和关注成功恰恰是一体的两面。过去我们往往把关注成功等同于追求名利加以批判,这值得我们反思。
“别关注正确,关注成功”,这句话是乔布斯的座右铭之一,它提示人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太把人们司空见惯的“正确”当回事,结果既不敢想更不敢为,那还活什么劲啊!
还有个主流和非主流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吴冠中先生写自传时说过,他自归国后,就处于三大派(延安派、亲苏派和写实派)之外的非主流位置,得不到重视和重用。谁成想“因祸得福”思想上禁锢少一些,探索的空间自由宽广一些,才有了后来的吴冠中。无独有偶的是,今年获普列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师王澍,也是非主流建筑师,他的事务所也是业余建筑设计事务所。这两个历史事实应当给我们更深的启示吧?